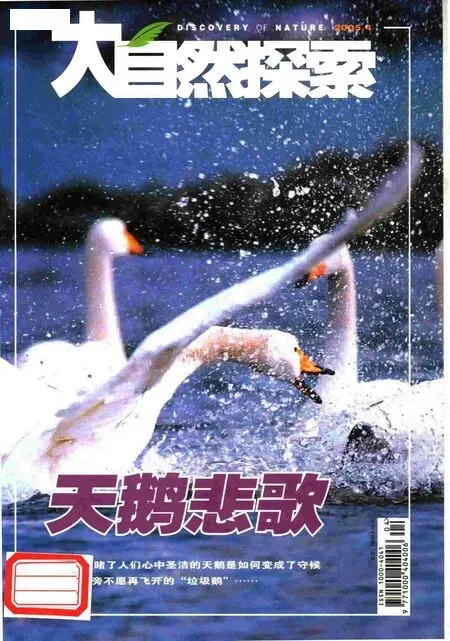馬王堆漢墓發掘記
熊傳薪
馬王堆漢墓發掘是我國20世紀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因一號墓中出土了兩千多件珍貴文物和一具保存了2100多年而未腐爛的女尸而令中外震驚。在事隔3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特約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考古專家和我們一起重溫這一重大考古發掘歷史,相信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千百年來,一個形似馬鞍的土堆兀立于空曠的原野上;一個關于漢景帝的兩位妃子和她們的兒子的傳奇故事廣為流傳。
馬王堆位于長沙市郊的東屯城附近。遠眺馬王堆,它是一處高出周圍平地20多米的橢圓形土堆,方圓不到1公里。實際上,它是由東西兩個并列土堆組成,土堆上各有一個四五米高的小山包。由于周圍是一片空曠的原野,從而使馬王堆顯得高突兀立。
馬王堆上的兩個小山包并列而立,其形狀似馬鞍,故在明清以前,馬王堆被稱為“馬鞍堆”。隨著時代的變遷,因“鞍”字在長沙地方口音中與“王”的發音相近,馬鞍堆就逐漸演變成了“馬王堆”。馬鞍堆變成馬王堆,除了地方口音之外,還有一個原因,與史書記載有關。據史載,公元923年,后唐取代梁,一個名叫馬殷的人被冊封為楚王,并以潭州(今長沙)為統治中心,管轄今湖南全省、江西西部、貴州東部和湖北南部地區。公元930年,馬殷去世,其子馬希范繼位。至北宋,楚國滅亡,馬殷家族統治湖南達數十年之久,迄今長沙市內仍保留了一些以“馬王”為名的遺址,馬王堆就是其中之一。在楚王馬殷家族消失數百年后,清人認為馬殷及其家族死后葬于馬王堆,但由于史料記載不足,故只好以馬殷家族的疑冢稱之。
還有人認為,馬王堆是西漢時期長沙定王劉發的母親程、唐二姬之墓。據史載:在長沙縣側十里,有西漢長沙王(劉發)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雙女墳”,墳高7丈。史書中還有一個有趣的記載:長沙王劉發的母親唐姬原是漢景帝的寵妃程姬之侍女。一天,漢景帝傳喚程姬侍寢,但程姬正遇經期,皇上的旨意不可違抗,程姬便想出一個辦法,從她的侍女中挑選了身高相當、容貌相似的侍女唐兒,裝扮一番,代替自己與景帝同房。那晚景帝宴罷歸房,醉眼朦朧,在昏黃的燈光下不及細看,就與唐兒同床共寢,唐兒因此懷上龍種,為景帝生了個兒子,取名劉發。劉發因為是侍女所生,所以他長大成人后,景帝將他封為“乃人口一萬五千戶耳”的長沙國之王,封號定王,并讓其遠離長安。后來劉發知其身世,對唐、程二姬十分孝順,在臨湘(今長沙)城內高筑土臺(即今長沙市的定王臺),時常登高遠眺長安城,思念其母。在唐、程二姬相繼去世后,劉發將她們的尸體由長安運至臨湘,安葬在城東幾里之外的土堆中,并在土堆上豎立起一根高大的旗桿,桿上吊掛一只紅燈籠,每當劉發站在定王臺上遠眺大紅燈籠,就仿佛看見了自己的母親。
馬王堆究竟是五代楚王馬殷家族的墓地,還是漢代的“雙女墳”?從史書上難以確定。1952年,我國考古學家對馬王堆進行了實地考古調查,從馬王堆的地貌、地層堆積和土質等情況分析作出結論:馬王堆不是一處自然的高大土堆,而是由原有的一座僅高六七米的橢圓形自然土堆,后經人工培土逐漸升高、加大而形成的,是一處漢代貴族的墓葬群,但墓主人究竟是誰?一直未有定論。
防空洞施工現場,一個民工將鋼釬插入土中,無意間的動作拉開了震驚世界的考古大發現的序幕。
1971年,馬王堆已是湖南軍區所屬的一所醫院的所在地。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該醫院為“戰備”需要,在該地修建防空洞,正在施工當中。當時兩條防空洞分別由東向西和由南向北向土堆中部挖去。在由東向西的防空洞挖進20多米時,洞內的土質發生了變化,由原生土變成了松土,洞頂和洞壁也經常出現塌方。更為奇怪的是,防空洞底部的土質也很松軟,有民工休息時將鋼釬插進土層,拔出來后發現土層上形成一個小洞,洞內有一股涼氣冒出,還有淤水從洞內沖出來。民工雖覺奇怪,但沒太在意。后來,又有民工休息時無意中將點燃的火柴蒂碰到了從洞內冒出的涼氣,結果涼氣一下就燃起來,火焰呈藍色。這時民工中間一片嘩然,有人就說這是地下的“鬼火”。消息傳開,民工們再也不敢繼續往下挖,有人干脆就卷起鋪蓋回家了。這樣一來,工程面臨停工的威脅。怎么辦?醫院方面將此情況上報,有關方面旋即電告湖南省博物館,要求派人前往調查。
筆者當時正是湖南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接到任務后,博物館的領導、幾位挖墓老師傅和筆者一行數人于3天后趕赴現場進行考古調查。
我們首先進入由東向西的防空洞。當走進洞內20多米時,發現防空洞的洞壁、頂部以及底部的土質有所變化,不僅土質松軟,而且從土中還發現了已炭化的顆粒,土質有經過夯打的痕跡。我們又查看了鋼釬在防空洞底部留下的小洞,并劃燃一根火柴,將燃著的明火與洞內冒出的氣體接觸,結果氣體燃燒,火焰呈藍色。挖墓老師傅根據經驗判斷,防空洞下面可能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這段防空洞所經過的地方可能是墓葬中的填土部位。防空洞底下冒出來的氣體可能是墓內埋葬物腐爛之后產生的沼氣。
隨后,我們又轉入由南向北的防空洞進行調查。我們剛從洞口走進四五米就發現洞壁上有一團呈橢圓形狀的白色膏泥,非常顯眼。大家都覺得奇怪這里怎么會有白膏泥呢?我們用手去摳白膏泥,感到它像磁土一樣,不僅柔軟,還有黏性,就像搗碎了的糯米粑。
當整塊白膏泥被挖去之后,里面又現出了木炭,木炭有大有小,直往洞外掉落。一位老師傅用手向垮塌出來的炭洞中摸去,發現里面有兩塊橫豎搭放的大木塊。他將手縮回來,說:里面可能是一個大木槨的一部分。我們立刻意識到:這里果然有一座墓!
為了保密,我們將落到洞外的木炭重新塞回洞內,再將白膏泥填在外面,保持原樣不動。走出防空洞,我們又爬上土堆頂部觀察,發現其中由東向西的防空洞底下的古墓正好處于東邊土堆的正下方,而由南向北的防空洞底下的古墓則位于土堆南邊,據此我們估計,西邊土堆下還應該有一座古墓。
這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陸續發掘出土的馬王堆一號、二號和三號墓,震驚世界的長沙馬王堆漢墓考古大發現也由此拉開了序幕。
這是一次極為艱辛的發掘工作,規模巨大,困難重重,令人至今難忘。
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工作是從一號墓的封土堆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封土堆上曾建過一個涼亭,后來涼亭雖不在了,但水泥基腳仍牢牢地扎在封土堆之中。我們用推土機推掉水泥基腳,然后人工往下深挖,進行了三四天的緊張施工,很快就將封土堆的土挖走。在接近墓口的上方,出現了一層平鋪的白膏泥,厚約10厘米,長約20米,寬近18米。在清理完白膏泥層后,又出現一層含有沙粒的黃色黏土。挖完黃土后,幾個老師傅找出了墓邊,確定了墓口。墓口南北長19.5米,東西寬17.8米,近乎一正方形。
接著,我們開始發掘墓坑內的填土。挖掘工作工程浩大,困難重重,先后有1500多人次到現場參加發掘,每天參加的人數就有一兩百人。
在70多天的發掘過程中,不知有多少人磨破了多少件衣服,穿破了多少雙鞋,挑斷了多少根扁擔和多少條繩索,損壞的撮箕都堆成了一座小山。到4月上旬,墓坑內的最
后一擔填土終于被運走。我們對墓坑進行了測量。從封土堆到基坑底,整個深度達13米,從墓坑內挖出的土方約2萬立方米。馬王堆一號墓的發掘,堪稱我國最為艱辛的一次考古發掘工作。
在墓坑的底部有一層白膏泥,猶如一張白色的地毯,人站在上面感覺軟綿綿的。白膏泥是古人為保護槨室不腐爛而采用的一種防腐措施,一般只對有一定身份的死者使用。在長江流域的墓葬中,這一措施從春秋時期開始使用,沿襲到兩漢前期。白膏泥的學名叫“微日高嶺土”,它的化學成分為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鋁、氧化鐵和硫、鈣、鎂、鈉、鉀等,礦物成分主要是石英、白云母和高嶺石。它具有一定的黏性和可塑性。含水分多,分子結構緊密,滲透性極低。由于這些特性,把白膏泥埋放在墓室內的槨室上下和四周,既可避免槨室內的氧氣與填土中的氧氣接觸,又可防止填土中的氧和水滲透到槨室中去。
要想將墓室內的白膏泥取走,也很不容易。白膏泥不宜用鋤頭挖,因為鋤頭挖下去就拔不出來。那怎么挖呢?只能用沾了水的鐵鍬一鍬一鍬地鏟。由于白膏泥有黏性,比重又大,如果把它放在竹箢箕里,它就會粘在竹箢箕上,挑起來很重,搬運起來很不方便。最后我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用鐵鍬將白膏泥鏟成一方塊一方塊的,然后讓人排成長隊,隊伍從墓室底部一直排到墓坑口,采取傳遞的方式,將白膏泥運送到坑外。我們用了近兩個整天的時間,才將槨室頂部和四周的白膏泥運走。經估算,槨室上層的白膏泥厚約60厘米,四周的白膏泥厚約1.3米。
我們以為挖完白膏泥層后就能見到槨室,可是白膏泥層下面還有一層木炭,整整齊齊地覆蓋在槨室頂上,就像一層黑色的絨毯,在槨室的四周也填塞了厚厚的木炭。木炭是具有很多細孔的無定形炭,吸水、防潮的性能良好,能起到防潮的作用。在大型的古代貴族墓葬中,木炭一般與白膏泥同時使用。清理木炭比清理白膏泥容易一些。我們用鐵鍬將木炭鏟在竹箢箕里,一擔一擔地運出坑外。經測量,槨室上層的木炭厚約40厘米,槨室四周填塞的木炭厚約56厘米,總共有5D00多公斤。在墓中發現的木炭和現在的木炭相比沒有什么區別,放在爐火中燃燒,仍具有很強的火力。
到了4月10日,槨室上面及四周的白膏泥和木炭全部清理完畢。基室四周向四壁內凹,形成一個南北長7.6米、東西寬6.7米、高3.2米的基室。
三個盜洞赫然出現,令考古專家感到隱隱不安:難道這座古墓早已被人盜過?
前面已提到,我們發現從防空洞底下的槨室中冒出來的氣體能燃燒。據老師傅說,這是一座“火坑墓”。這種墓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保存完好,從未被人盜掘過,墓坑內的槨室用白膏泥和木炭密封,槨室和隨葬物都完好無損;另一種情況是被人盜挖過,雖然槨室仍保存完好,但墓中的隨葬物已至少有一部分被盜走。為什么在被盜挖后洞中還能繼續冒出氣體,而且氣體也能燃燒呢?老師傅告訴我們:基原本筑得相當嚴實,從上往下挖的盜洞通常挖得很小,僅能容納一人上下;當盜墓人從洞中進入槨室后,常常會因為難以忍受墓中有機物腐敗后產生的氣體,只好匆匆忙忙地從墓室中取走部分器物,然后立即爬上地面;由于盜洞不成形,洞內的填土和白膏泥很快垮塌,重新將盜洞嚴實地封住,這樣一來,槨室中的絕大部分氣體便保存下來,如果以后無人再挖洞。該墓仍然是一座“火坑墓”。
聽老師傅這么一講,我們的心懸了起來:這座墓會不會屬于第二種情況呢?在挖填土時,我們特意安排了兩位有經驗的老師傅,請他們注意填土中是否有盜洞。當墓口的填土往下挖到1米左右時,老師傅果然發現了三個盜洞:一個為圓形,另兩個為長方形。老師傅估計長方形盜洞為近代所挖,圓形盜洞則為古代所挖。
經過幾天的淤泥清理,兩個長方形的盜洞現出了底部,我們在其中一個盜洞內發現了一只“回力牌”男鞋的鞋底,可見這兩個盜洞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挖的。
在清理圓形盜洞的淤土時發現了兩枚“開元通寶”銅錢,從銅錢分析,此盜洞為唐代時所挖。隨著挖掘的進行,我們的擔心也越來越大:這座墓難道真的已被盜過嗎?順著盜洞往下挖,盜洞越來越小。到9米深處時,洞壁上出現了煙熏過的痕跡;到19米深處時,盜洞痕跡不見了。老師傅說:“盜洞挖斜了,沒有挖到墓室。”聞此言,我們忐忑不安的心才算平定了下來。為什么盜洞沒有挖到底呢?老師傅分析說:因墓坑太深,當時盜墓人的技術也不怎么樣,所以將盜洞挖斜了,但畢竟還是挖了十幾米深,盜墓人用來照明的火在盜洞內點燃了從墓室中滲透出來的沼氣,燃燒產生的煙霧將盜洞壁熏黑,盜墓人也可能被燒死在洞內,盜墓因此停止。
揭去遮蓋,一座宏大的槨室出現在人們面前。大量陪葬物歷兩千年至今依然艷麗如初,仿佛剛剛被人放入墓室。
在打掃完槨室上面的木炭后,我們發現在槨室蓋板上還鋪滿了一層竹席。經過半天。多時間的努力,竹席全都露了出來。竹席剛見天日時呈黃色,猶如新的一樣,但僅過了半小時,因為與空氣中的氧氣接觸,竹席就逐漸變黑了。這些竹席的編織方法與現代差不多。在槨室上一共鋪了26張竹席。在其中一些竹席的一角上還墨書有“家”字。又經過半天多的時間,我們將覆蓋在槨室蓋板上的竹席全部取了上來。現在,一個完整無損的大槨室終于顯現出來了,它呈黃色,保存得也相當完好。經測,這座槨室長6.72米、寬4.88米、高2.8米,顯然算得上塊頭巨大。
我們原打算在4月13日上午就掀開槨蓋板,但由于消息傳出后到工地上來看熱鬧者人山人海,白天無法工作,只好改在晚上進行。晚上九點,電燈、碘鎢燈齊亮,把整個工地照得猶如白晝。20余人一齊下到了墓坑內。
木槨的構造,是沿襲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的棺槨結構形式,史書上稱之為“井槨”,意思是說它的形狀像一口井。八塊巨大的木板拼成四個邊箱,正中是一個較大的棺室。四個邊箱主要用來放置隨葬物,中間的槨室用以放置重重套棺。
木槨全部用粗大的木料制成,上下嚴密、平整,全槨70塊木板之間未用一根金屬嵌釘,而用扣件、套榫與栓釘結合而成。木槨所有的木板全是整塊木料,最大的一塊槨板長4.88米,寬1.52米,厚0.26米,重1500多公斤,估計它所取自的原木直徑起碼在2米以上。據估算,一號墓的木槨現有板材即達50多立方米,當初所耗費的原木至少在200立方米以上。
經過兩個晚上的緊張施工,蓋板被一塊一塊地掀開,木槨的四個邊箱被打開,里面擺放著滿滿的隨葬物,看起來保存狀況都很好,就像不久前才放進去的一樣。
從四個邊箱的大小和存放在邊箱內的隨葬品分析,北邊箱空間較大,應是象征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地方,其他三個邊箱則象征墓主人生前存放物品的地方。因此我們首先選擇北邊箱開始清理。
最先取出的是一件漆案。案上存放有耳環、卮、盤等器物,有的盤上放一雙竹筷,有的盤上則盛有牛排骨。這些漆器既光亮又完整,色澤鮮艷,紋飾流暢,猶如新制作的一樣。接著,一個繡枕被取了出來,保存得也相當完整,這還是在我國第一次發現古代繡枕。然后,又從邊箱內陸續取出了五人一
組的鼓瑟、吹箏木俑、歌俑、舞俑、著衣女侍俑、彩繪立俑,以及漆鈁、漆勺、竹熏罩、木杖、陶壺、陶熏爐、絲履、繡花夾袍、繡花毛巾、繡花夾袱、五子漆圓奩、繡花香蓑、九子漆圓奩、漆風、漆屏風、竹席等70多件隨葬品。
在后來的幾個晚上,發掘人員繼續清理其他幾個邊箱內的隨葬品。東邊箱內分層堆滿了隨葬品,其中有一捆竹簡,堆放在漆器上面,有的竹簡因編繩已腐斷,部分竹簡散落在漆器旁。除竹簡外,東邊箱的隨葬品主要是木俑和漆器。彩繪木俑不下45個,其中有一個戴冠的男俑,它形體高大,身著絲綢長袍,鞋底刻著“冠人”二字。漆器數量近230件,保存完好,制作精良,色顏鮮艷,紋飾優美。有的漆器尤其值得一提,如一具杯盒,在一盒內存放有七件耳杯,其中六件順放,另一件與這六件反扣在一起,其設計堪稱匠心獨具。又如一件漆鼎,內盛清水,水面上漂浮著幾片成形的藕片。然而,當老師傅將鼎從邊箱底部輕輕地捧上來時,鼎內的藕片卻在頃刻間散架。當時我們雖然對此覺得奇怪,但也沒太在意。沒想到,后來這件漆鼎竟成了地震部門研究長沙地區地震史的寶貴資料,證明長沙兩干多年來從未發生過強烈的地震,這一推斷與史書的記載完全吻合。藕片跟地震有什么關系?藕片在鼎里泡了兩千多年,早已化成粉,卻能保持原形,但鼎在老師傅手中輕輕一晃,藕片卻融化在了水中,這不正好說明當地在過去兩千多年中晃都沒晃過一下嗎?
南邊箱的上層也堆放有大量的彩繪木俑,此外也有一件高大的戴冠男俑,與東邊箱出土的那件高大男俑相同。在木俑下面主要是陶器,包括陶瓿、硬陶罐、彩繪陶豆、彩繪陶鈁、彩繪熏爐、陶釜、陶甑等,最底層還放有竹笥和竹莢等。在清理這批陶器時,我們發現每件陶罐的口部都被書有“轪侯家丞”字樣的封泥封住。正是這些封泥,為我們徹底解開馬王堆墓主人身份之謎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
西邊箱的上層擺放著一把長柄扇,一把短柄扇,一件用錦袋盛裝的木瑟和一件竽。在這些器物下面,擺放了三層竹笥。竹笥剛出土時,竹蔑呈黃色,但時間稍長一點,就逐漸變成了黑色。上層的竹笥質地保存較好,每個竹笥都用麻繩捆扎,在繩的交叉處有的還保留有一木牌,木牌上標明笥內所盛的實物。如329號竹笥吊掛的木牌上墨書有“衣笥”字樣,后來在打開竹笥蓋后,發現笥內果然裝滿了各種服飾,如單衣、袍、裙、襪、手套等,這也是我國發現年代最早的服飾。它們的顏色非常鮮艷,保存也十分完好,但由于長期浸泡在水中,質地受到了影響,如果用手去摸,就會感覺它們像豆腐一樣。在專家的精心處理下,這些衣物最終完整地保存了下來。竹笥內還出土了46件單幅的絲織物,如紗、絹、綺、羅、錦、繡,它們充分反映了我國古代紡織技術的高超水平,證明了當時的我國不愧為“絲綢之國”。在西邊箱,總共出土了50多個竹笥,其中每個竹笥內部盛滿了實物,里面還殘存有各種飛禽走獸的骸骨和大量的中草藥等。
最后一具棺木終于被打開,在棕黃色的液體中究竟隱藏著什么?人們屏住呼吸,等待著揭開謎底的重大時刻的來臨。
當四個邊箱內的隨葬器物清理完后,清理人員開始清理槨室中的棺室。棺室內有幾層棺?當時不得而知,只能一層層地揭開才能知道答案。
先拆開內槨板,現出了一個長方形的黑漆棺,素面無紋飾,這是該墓的第一層棺,長2.95米,寬1.5米,通高1.44米,棺的外表面遍涂棕黑色油漆。我們用刀片將棺蓋與棺身的縫隙中的粘合劑刮掉,再將一個木塞塞到縫隙中,使棺蓋和棺身分開。抬開蓋板,然后將棺身的四邊壁板拆開,就現出了第二層棺。
第二層棺為黑底彩繪棺,長2.56米,寬1.18米,通高1.14米,棺的外表以黑漆為底,彩繪了復雜多變的云氣紋,以及穿插其間、形態生動的各種神怪和禽獸。這么豪華的漆棺,此前大家從未見到過。為了打開它,同時還不能損壞它,當時真是費了一番功夫。
棺蓋蓋在棺身后,為了密封,在蓋和身的合口縫隙中還用了一種粘合漆,但合口縫隙仍存在一條縫。于是,我們從縫隙下手,在棺的四周分別站幾個人,每個人手中拿一塊薄薄的刀片,將刀片伸入縫隙中,慢慢地將縫隙中的粘合漆刮掉。刮了兩個多小時,漆棺四周縫隙中的粘合漆全被刮掉。然后,在四周的縫隙中分別打入木塞,使蓋和身脹開,直至手指能伸進的程度。再叫幾個身強力壯的人站在棺的四周,將雙手伸進縫隙中,一齊用勁,終于將棺蓋揭開了。
將棺蓋抬開以后,只見里面還有一層棺。這是第三層棺,為朱地彩繪棺,保存狀況也很好。棺蓋紅紅的,在紅底上繪有二龍二虎相斗圖案。二龍的龍首相向,居于畫面中部的上方,龍身各自向兩側盤繞,尾伸至左右兩下角。二虎相背于二龍之間,分別攀在龍首之下,口嚙龍身。龍為粉褐色,用赭色勾邊,身披鱗甲而有三角弧形斑紋,斑紋內填以綠色。虎為赤褐色,頭部加飾流云。
在這層棺里面還有一層棺,其蓋板與外面三層棺的裝飾風格完全不同,它中間為菱形勾連紋的羽毛貼錦,周邊飾以鋪絨銹錦,中間又橫貼一道,成一“日”字形,在它上面還反鋪有一幅帛畫。
帛畫的畫幅很大,如何揭取它呢?一位專家用手摸了一下帛畫,發現帛畫質地較好。經過研究,決定在帛畫上鋪一張質地較好的宣紙,然后用一個紙筒作軸心,將帛畫輕輕地卷在軸上。
用了一個多小時,終于將帛畫卷在了軸心上,然后清理人員將軸心放在鋪有宣紙的三合板上,從正面將帛畫展開,只見帛畫色彩非常鮮艷,采用了朱砂、土紅、青黛、藤黃以及銀粉、蜃粉等顏料,用淡墨起稿,再放各種色彩,最后勾畫墨線。以平漆為主。有些地方還采用了濃淡渲染的畫法,畫面上線條流暢,線條變化和色彩調配也很合理。畫的內容豐富,大致分為天上、人間、地獄三大部分。
費了好大的功夫,帛畫終于取了出來,但事情還沒有完,用絲織物包住的棺還擺在那里。我們猜測,那應該是最后一層棺了。但究竟是不是最后一層棺,還得等棺蓋打開之后才能知道。我們將貼在棺蓋上的羽毛錦和鋪絨繡一塊一塊地揭取下來后,看到棺蓋的兩端各橫纏了兩道寬12厘米的帛束,它們被用來捆綁這層棺。如何將這層棺蓋揭開呢?我們仍采用上述的辦法,將棺蓋和棺身的縫隙中的粘合漆刮開,割開纏繞棺身的兩道帛束,然后幾人用手將棺蓋移動一點,將手指伸入縫隙中,用力將棺蓋抬起,再塞進木塞,最后大家一齊用勁,終于將棺蓋打開。
棺蓋打開了,人們的目光一齊聚集到了這層棺里,里面果然沒有棺了,就是說這的確是最后一層棺。棺內滿滿的一棺絲織物,浸泡在棕黃色的棺液里。這棺里究竟裝著什么?
在經過了那么長時間、克服了那么多困難之后,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會是什么?謎底就要揭開了!也許當時在場的人中沒有一個意識到,他們將成為20世紀一次震驚世界的考古大發現的直接見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