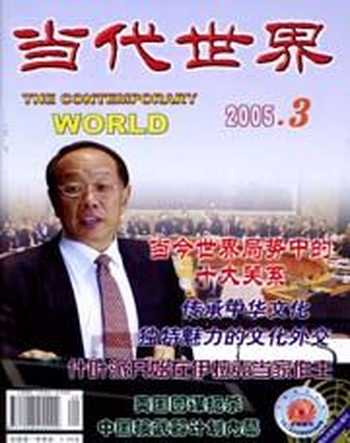誰來幫助非洲減貧?
杜小林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擁有豐富的礦藏和資源,但長期以來卻為貧困所擾,經濟發展遲緩。提高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其減少貧困,既是非洲國家自身的義務,也是當今世界共同的責任。
非洲到底有多窮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當每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時就可稱為貧困,當收入不足1美元時,稱為極度貧困或赤貧。目前世界上有28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11億處于赤貧狀態,亞太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別約占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即各有7億多和3億多赤貧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總共只有7億,也就是說,這一地區的貧困率將近50%,無疑是全球最高的。另外從經濟發展水平、人類發展指數等來看,非洲也遠落后于其他地區。21世紀初,非洲國家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450美元,其中約一半國家低于300美元;非洲GDP僅占全球總量的1%,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僅占1.5%;人均壽命只有53歲,40%的人口得不到醫療衛生服務;小學入學率約70%,中學入學率只有33%;每百人僅擁有3部電話和0.9臺計算機。在48個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就占了33個,世界銀行又將其中的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塞拉利昂和布隆迪五國列為世界最窮國,其人均收入在100美元上下。
更讓人不安的是,當世界其他地區的貧困人口在減少時,非洲的卻在增加。世界銀行統計顯示,1981年到2001年,發展中國家的赤貧人口從15億減少到11億,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從40%降至21%。相應地,東亞地區的貧困率從58%降到16%,南亞地區從 41%降到31%,惟獨非洲從
42%升到47%,赤貧人數從1.64億增加到了3.14億。
造成非洲貧困的諸多原因
籠統地說,貧困是非洲大陸發展階段滯后、生產力水平低下導致的必然現象,既是歷史造成的,也有現實原因,既有人為成份,也是客觀使然,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具體說來,可將造成非洲貧困的原因歸納為十個方面:一,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使非洲喪失了大量寶貴資源;二、殖民統治使非洲形成初級產品單一經濟和城鄉二元結構,現行的國際分工使非洲國家無力改變現狀,對外依賴性強,抵御外界風險能力差;三,現行貿易秩序使非洲國家受到新殖民主義及不平等交換的剝削,非洲產品在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面前競爭乏力,在世界總出口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80年為5.9%,1990年3%,2000年2%;四、多數非洲國家不能獨立自主地堅持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盲目照抄照搬外來模式,戰略和政策有誤,喪失發展良機;五、民族、部族、宗教和地區等各種矛盾處于多發階段,各方對利益協調機制的探索剛剛開始,沖突、政變、戰亂頻仍,社會長期動蕩;六、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失衡,人口增長往往快于經濟增長,使經濟增長的好處消于無形;七、人口素質亟待提高,窮人缺乏改變自身命運的知識和技能,許多國家成人識字率低于40%;八、艾滋病、瘧疾和結核病等奪去大量青壯勞動力,留下了1300萬艾滋病孤兒,感染艾滋病毒總人數達2500多萬,占全球五分之三;九、20世紀90年代民主化浪潮導致非洲國家政局動蕩,經濟受到沖擊;十、經濟全球化使非洲國家日益邊緣化,得到的援助、投資減少,外債負擔在發展中國家最為沉重,一些國家如蘇丹和津巴布韋還受到西方制裁。
聯合國搭起全球減貧平臺
貧困不僅導致非洲國家內部沖突、貧富差距和動蕩,也是國際沖突、戰爭和恐怖主義的根源,威脅到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實現。為了戰勝這一人類的宿敵,在2000年9月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世界各國領導人確定了“千年發展目標”,作為全球反貧困的核心議程。“千年發展目標”是對減貧及相關努力進行監測、評估和督促的一套機制,包括8項大目標和48項小指標,8項大目標是,以1990年的數據為基數,到2015年時要達到:將赤貧和饑餓人數減半;普及初級教育;提高婦女權力并促進男女平等;減少兒童死亡率,將五歲以下幼兒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提高母親的健康水平,將產婦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遏制疾病特別是艾滋病和瘧疾的傳播勢頭;確保環境可持續性;建立以援助、貿易和減免債務為指標的全球發展合作關系。
與“千年發展目標”比較,非洲的情況不容樂觀。在各項指標中,多數非洲國家現狀與當前應達到的水平都有不小距離,照此趨勢,到2015年,只能實現其中的一兩項目標,赤貧人數不但不能減半,只要不增加就不錯了。
非洲自身視
減貧為重中之重
盡管非洲反貧任務十分艱巨,非洲國家并未聽天由命,而是積極與貧困作斗爭,不少國家已積累了一定經驗并取得明顯成效,莫桑比克、烏干達和埃塞俄比亞三國較有代表性。莫桑比克執政黨和政府結合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從教育、衛生、農業與農村發展、基礎設施、良政和完善宏觀經濟管理等六個方面制定減貧行動計劃,實施十多年,使貧困率從1997年的69%降到2003年的54%,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成任務,莫執政黨也因此連續兩次贏得大選勝利。烏干達1990年時貧困率為56%,艾滋病感染率超過20%,真可謂貧病交加,烏政府將防治艾滋病作為反貧的重要環節。烏首先是正視現實,向全國公開艾滋病的嚴重程度,讓人們搞清楚艾滋病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通過立法成立專門委員會來整合資源,協調各方。再就是政府分階段制定計劃和目標并監督落實,同時爭取外援。結果,到2004年時艾滋病感染率已降至6%,貧困率也減少到
38%。埃塞重點通過加大教育投入和能力建設來扶貧。除了給更多青少年提供正規教育機會外,還以職業教育、技能培訓等方式增強成年人的脫貧能力,使小學入學率和成人識字率分別從1990年的33%和28%增加到2004年的69%和43%,貧困率則從64%降到44%。
上述三國減貧成功的背后,有許多共同經驗。如三國都是歷經了多年戰亂后,維持了政治穩定,以市場經濟手段調動生產積極性,從國情出發,以己為主,主動改革,并爭取外援。三國也是非洲近年來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非洲其他國家也很重視減貧并投入了大量精力,更讓人感到鼓舞的是,非洲國家的集體組織——非洲聯盟,已將減貧作為整個大陸的重點工作之一。非盟將減貧目標寫進指導大陸經濟發展的藍圖“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通過內外兩種渠道來行動。一是聯合自強,建立起“同行評審”等相應機制,對各國實施良政、發展經濟、反腐、減貧等進行監督和協調,并擬建立全非維和部隊,以便需要時強行實現、維護和平與穩定。二是與外界建立伙伴關系,爭取人、財、物等各方面幫助,共同解決非洲的問題。
西方大國對
非洲減貧半心半意
早于1970年,國際社會就要求富國為窮國提供幫助,發達國家也允將GDP的0.7%作為官方發展援助(ODA)。但時至今日,除一些北歐國家能做到外,美國等西方大國的ODA 遠低于0.7%限額。自1980年以來,由西方大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發展經濟”的名義壓非洲國家實行“結構調整計劃”,而結果表明,這一計劃是失敗的,幾乎沒有非洲國家因此而得到發展,告別貧窮。因為其實質是強迫非洲國家接受以 “華盛頓共識”為表現的新自由主義,使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外圍的國家更好地為中心服務,而不是以幫助非洲為初衷。90年代,非洲從西方得到的ODA進一步減少,2000年比1990年少了100億美元。“9·11”事件后,西方意識到發展中國家的貧窮直接威脅發達國家的安全,表示要重視幫助非洲減貧。2002年八國首腦會議將援助非洲作為一項重要議題,通過了“對非行動計劃”來支持“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但至今未確定任何具體援助項目。美國響應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拋出了“千年挑戰帳戶”,允諾2004-2006年間向“在民主和資本主義進程中”取得進展的窮國多援助100億美元。美國表示關注非洲艾滋病問題,布什總統2003年宣布五年提供150億美元來幫助非洲、加勒比國家防治艾滋病。但評論認為,近年美國經濟不振,屆時不可能完全兌現承諾,美國政府對外宣傳成份大于實際行動。
中國真心誠意
幫助非洲減貧
與非洲有過類似歷史遭遇的中國對非洲國家的貧困一向感同身受,從1956年起就開始援助非洲。至今,共完成800來個成套項目,涉及農林牧漁、水電交通、廣播電視和教科文衛等各個領域。學校、醫院等項目直接有助減貧,鐵路、農場等項目對當地經濟發展影響深遠。中國還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物資、技術和人力援助,曾向近40個非洲國家派出醫療隊,為1.6萬非洲學子提供了政府獎學金,派遣專業教師500多名。正如胡錦濤主席2004年在加蓬議會演講中所說:“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向非洲國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是中國對非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
中國政府注意隨形勢變化給對非援助注入新的內容。2001-2002年間,中國免除了31個非洲窮國的約105億人民幣的債務,占這些國家對中國到期債務的
60%。2003年底,溫家寶總理在第二屆中非合作論壇會議上宣布,中國將減免非洲國家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關稅,加大對非人力資源培訓的投入,今后三年為非洲培養、培訓一萬名人才。中國還在WTO坎昆會議上與非洲國家合作,抵制了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2004年,中國與聯合國共同舉辦“上海全球減貧會議”,同國際社會交流、分享減貧經驗。減債、擴大貿易、開發人力資源和借鑒經驗,對非洲減貧都是急需的,中國一系列的新舉措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歡迎。
2005年是聯合國60華誕,距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期限只剩10年。未來10年,沒有國際社會的幫助,非洲自身難以實現目標。南非總統姆貝基說:“一個多數人貧窮、少數人繁榮的全球社會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我們沒有理由不對非洲減貧伸出援助之手。
(本文責任編輯: 季仰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