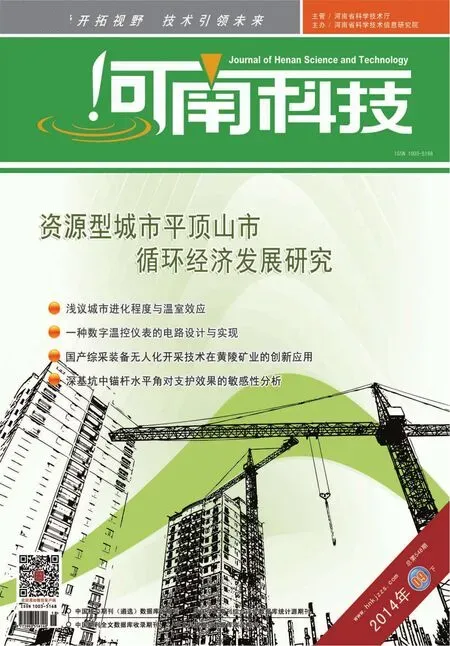獨立學院學習型教學管理隊伍建設實證研究——以桂林理工大學博文管理學院為例
2014-02-27 14:15:17劉穎,朱嵐濤,江曉云
河南科技 2014年18期


猜你喜歡
大學(2021年2期)2021-06-11 01:13:24
甘肅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 09:01:24
甘肅教育(2020年4期)2020-09-11 07:41:24
中國外匯(2019年18期)2019-11-25 01:41:56
電子制作(2018年14期)2018-08-21 01:38:28
人大建設(2017年10期)2018-01-23 03:10:17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10:29:03
體育師友(2011年2期)2011-03-20 15:29:29
數學大世界·小學低年級輔導版(2010年2期)2010-03-03 09:39:48
中國火炬(2009年2期)2009-07-24 14: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