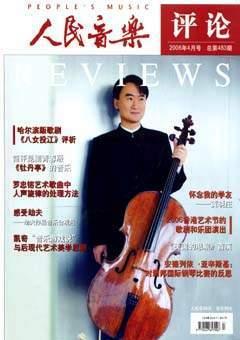勞山的光榮兒子——黃曉莊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延安機場接王若飛同志重慶談判后歸延。前排:(從右至左)王若飛夫人李培之、王若飛、曉莊爺爺黃齊生、奶奶王守瑜。后排:黃曉莊、大妹黃曉芬、陳復君、劉伯承侄女劉僉泰。
1946年4月8日,天氣陰沉,雨雪交加。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附近隱隱聽見了稀有的飛機轟鳴聲。突然一聲巨響,機聲消失……17位可貴的生命就在這巨響中驟然消逝了。他們當中有我們老一輩的革命家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有我黨的老朋友、貴州知名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有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也有婦孺兒童,其中還有我的同學、戰友、親人、結婚才一月余的丈夫——青年音樂家黃曉莊同志。
曉莊是黃齊生先生的侄孫、王若飛同志的表侄。他從小在祖父身邊長大,1937年11月曾隨祖父母到延安參觀訪問了半年多。由于當時延安條件比較困難,沒有合適的學校可以就讀,他不得不于1938年4月又隨祖父母返回西南。延安短暫的逗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他后來堅決走上革命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曉莊從小喜愛音樂,立志要做個音樂家。小小年紀的時候,他就唱過黃自的歌曲,并在日記本上天真地寫道:“黃自、黃自,將來有一個姓黃的要比你的歌還作得好。”到重慶后他考入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學習鋼琴、大提琴,成績都很優異,兩門課的教師都曾希望他以各自教授的課目為主科,但曉莊自己卻更喜愛作曲。不久,校方了解到他到過延安,他的親屬中還有共產黨人,更有不少同情共產黨的人,便以莫須有的罪名令他退學了。黃老先生與我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是多年至交,得知陶先生為少年兒童辦了一所育才學校,于是把曉莊轉送到育才學校。
這是一所在我黨的直接關懷下由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學校。學生大多來自戰時兒童保育院,少數是我黨的干部子弟或進步知名人士的子弟。這些孩子小的八九歲,大的也只有十三四歲。這是一所從入學起就開始進行專業學習的學校,設有音樂、戲劇、文學、繪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6個組,后來又增設了舞蹈組。在這里工作任教的有許多共產黨人和知名進步人士。音樂組有賀綠汀、常學鏞(貴州音樂家、現名任虹),戲劇組有章泯、水華、舒強,文學組有鄒綠芷、陸維特、力揚,繪畫組有陳煙橋、劉峴,舞蹈組有吳曉邦、盛婕、戴愛蓮等,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的是一些老共產黨員,如王洞若、孫銘勛、方與嚴、帥昌書(又名丁華)、程今吾等。我們在這個學校里既學習又勞動,既搞社會調查又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及演出活動。
曉莊是1941年下半年來到學校的。他來的時候,正是“皖南事變”之后,學校處在極端困難的時期。許多老師在惡劣的政治空氣下被迫轉移解放區,我們的學業因缺乏老師幾乎陷入停頓,只好按照陶行知先生創導的“小先生制”思想,自己教自己,同學互相當老師。說到生活更是清苦,常常是三餐稀粥幾顆胡豆度日。但是曉莊和我們一樣,在這大后方少有的民主、自由、和諧的天地里,生活得十分愉快。
我們這些從保育院來的窮孩子,入校時在音樂方面幾乎都是白丁,不要說彈鋼琴、識五線譜,許多人連鋼琴都沒見過。而這個個子不高、面目清秀的少年,不僅鋼琴彈得好,大提琴拉得也不錯,而且還能作曲,這真使我們感到驚訝。曉莊是個感情豐富但性格內向的人,在同學們的驚嘆聲中,他并未有任何高傲的表示。有位今日在創作上有相當建樹的老同學曾對我說:“我真佩服曉莊,他真聰明,他來學校的時候未受過系統的作曲訓練,但他卻不僅能寫優美動聽的旋律,而且還能寫樂曲。”說到這里,他十分感嘆地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假如黃曉莊在,可能沒有我?菖?菖?菖了。”這話說得太過謙遜,但也足見曉莊在同學中的確是比較突出的,他的天賦的確是比較高的。是的,他仿佛是為音樂而生的,每當聽到好的音樂時,往往激動得流淚。記得1943年我們音樂組為了求教的方便,從草街子搬到重慶江北觀音橋,與中華交響樂團是近鄰。我們常常去聽他們的排練。一次在聽他們排練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愴交響樂時,曉莊激動得哭起來。平時,他更是有感就寫,寫得也快,音樂仿佛從心中流淌出來似的。由于他受過革命的熏陶,作為一個有一定政治頭腦的熱血青年,他對那動蕩不安時代所發生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見解,這更促長了他的創作欲。不過,當時他常常苦于沒有合意的詞,于是就自己動手。他的作品大多具有鮮明的時代感,政治氣息很濃。他的合唱《重慶頌》,痛斥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詛咒了國民黨的貪官污吏。獨唱曲《花》描寫一個癡情的姑娘,動員她的心上人上戰場去抗日,當她的戀人要把一朵鮮花插到她的頭上時,她唱道:“快去當兵把敵殺,得勝回來我再接你的花!”合唱《往哪里逃》寫于1944年湘桂戰爭時期,當他看到人們東奔西逃,惶惶不可終日時,他寫道:“你也逃,他也逃,大家拼命地逃,逃難逃了7年多,哪里才是我們的安樂窩?”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之后,他又用勸導的口吻寫道:“逃難的日子多難過呀,打游擊要比逃難強得多!你看許多游擊區,敵人去都不敢去。”最后他疾呼:“只要團結一條心,不怕打不走鬼子兵,同胞們呀!同胞們,再不能逃,還是掉轉身來把家鄉保。”這首十分親切動人富有激情的歌,后來曾發表在1945年5月13日的延安《解放日報》上。
曉莊也很注意向民間學習,向傳統學習,向先輩革命音樂家學習,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具有很強的民族風格。他的鋼琴小品《新年》《小花鼓》就很富有民間氣息。我們的老同學杜鳴心曾告訴我,當年他留蘇入學考試時,主考教師曾讓他彈奏一首中國作品,他當時彈奏的就是曉莊的《小花鼓》,得到了老師的好評,當然,蘇聯教師不會想到這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創作的。至今鳴心還能流暢地彈出這首作品來。
在重慶時,我們音樂組經常在社會上舉行音樂會,曉莊除參加演奏外(因我們音樂組人很少,男同學更少,因而每個人都參加合唱),幾乎每次音樂會都有他的新作,作為一個十幾歲的青年作曲者,真是難能可貴。
1944年5月,曉莊的表伯父王若飛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由延安來到重慶,參加國共兩黨的談判。這時曉莊已經成人,他向往延安,向往早日投身到火熱的斗爭中去,于是他向若飛同志提出了再次去延安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表伯父的應允。一天,他帶著興奮的心情悄悄對我說;“表伯也同意你一起去哩!”延安是我們育才學生日思暮想的地方,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我感到幸運極了。
1944年底,我們來到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爾后便隨著他的祖父母和80多位同志,分乘4輛大卡車向延安奔去。
曉莊是帶著一顆赤誠火熱的心二次來到延安的。在我珍藏的他留下的一本延安日記的扉頁上,他寫下了這樣的字句:
莫回顧你往日的美麗
莫依戀你從前的幸福
既然為革命來到這里
就該勇敢地戰斗到底!
——送給自己
1945年3月20日
他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他雖然酷愛音樂,但也做好了為革命而改行的準備。他說,如果革命需要,他可以去做任何工作。到那時,可以把音樂作為副科。在延安等待分配工作考慮選擇哪個單位時,他最初選擇的是賀綠汀老師所在的聯防司令部政治部宣傳隊。他在日記中寫道:“參加聯政宣傳隊,我想在工作中去鍛煉。有一天反攻了,就有能力到前線,我不單干音樂工作,而且還要拿槍,干政治工作。”
延安是尊重人才、愛惜人才的地方。黨為了培養我們,用革命的理論武裝我們的頭腦,使我們樹立正確的革命人生觀,先送我們到中央黨校三部(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學習了一個短時期,然后分配我們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曉莊便在那兒邊教書,邊搞創作,我則到魯藝文工團工作。
在延安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曉莊總想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筆為人民創作。他熱愛延安,到后不久就寫了歌頌延安的抒情歌曲《當我漫步在延河邊》。他熱愛延安的軍民,醞釀著用民歌風格寫一首大型的解放區軍民大合唱。延安開展防旱備荒運動,他除了積極參加生產外,寫了《防旱備荒小調》。蘇聯紅軍攻入柏林,他興高采烈地寫了《紅軍打進了柏林城》。抗日尚未結束,蔣介石已經準備發動內戰,他寫了反對內戰的小曲……他還準備寫一部以陜北民歌為主題的《和平交響樂》,他還有不少創作設想,可惜,這一切都未能完成,他就離開了人間。
曉莊只活了20歲,人生本來就來去匆匆,而20年更是太短促了!但是他的短暫一生卻是戰斗的、充實的一生,是可以引以為自豪的青春的禮贊!曉莊去世以后,我們敬愛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校長曾寫了一首詩悼念他:
挽黃曉莊小朋友
勞山的光榮的兒子!
你沒有想到你會死。
你的爺爺也沒有想到,
他會帶你一同去死!
死者不可復生,
但是你的音樂不會死。
我將培養一百位人民的音樂幼苗,
努力一輩子,
補償這不可補償的犧牲,
一直到我死,
你也永遠不會死!
陶校長還在這首詩的注中寫道:“黃曉莊是黃齊生先生的愛侄孫,生于南京老山(后改名勞山)之小莊,有音樂之才,出口成歌,在育才學校肄業一學期中作曲48首。他作曲抱定一個宗旨:要為人民而唱,唱出人民心里的呼聲,還要達到人民自己歡喜唱。4月8日隨其叔祖父一同殉難,系新音樂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35年4月”
陶校長的詩和注是對黃曉莊同志短暫一生最好的總結,陶校長充滿感情的崇高評價,對曉莊來說也是最大的安慰!
(原載《中華英烈》1988年第二期)
陳復君 翻譯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