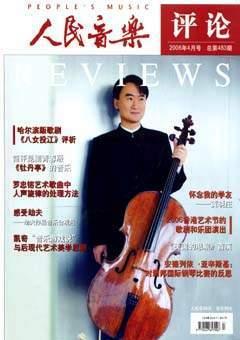懷念黃曉莊同志
今天我們已經作為世界的大國名列世界樂壇,但是,在解放前,由于統治當局的腐敗、政局的長期動蕩、經濟的落后,我國的音樂界一直處于艱難困苦的境地。許多才能突出甚或成就卓著的音樂家,常常因為種種客觀的因素而過早地離開人世。蕭友梅、劉天華、黃自、譚小麟、鄭志聲等均因疾病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而逝世。冼星海、張寒暉、董源等則因長期顛沛流離,積勞成疾而不治。張曙死于日寇的狂轟濫炸,任光、麥新遭到反動派的伏擊而壯烈犧牲,聶耳則是在流亡中溺水而亡。而其中年齡最小的黃曉莊,則在他剛剛流露其過人的音樂才華、在其花季之年就成為“四八烈士”之一而死于空難。
黃曉莊,貴州貴陽人,1926年出生于江蘇南京。他的祖父即貴州著名的教育家、進步民主老人黃齊生,他的表伯(齊生老人的外甥)即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王若飛同志。黃曉莊于1940年曾在重慶國立音樂院短期學習過鋼琴和大提琴,1941年入教育家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音樂組學習大提琴。當時他在音樂創作上已表露出突出的才能,先后創作了獨唱曲《花》、合唱曲《往哪里逃》以及鋼琴曲《小花鼓》等幾十首作品。1944年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任延安“魯藝”音樂系教師。1946年隨黃齊生、王若飛、葉挺等從重慶返回延安時,于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時年僅20歲!
陶行知的“育才學校”是當時重慶一所著名的進步私立學校,學員大多選自“大后方”的“戰時兒童保育院”,有少數為共產黨及民主人士的子弟,實行的是“半工半讀”性的學制。這所學校的經費均依靠陶行知向社會捐募,重慶的統治當局是不給一分錢支持的。但是,他們卻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如“音樂組”的教師均是當時重慶音樂界的著名音樂家和教師,如賀綠汀、李凌、任虹、任光,還有黎國荃、范繼森、姜瑞芝、朱崇志、胡然、姚牧、夏之秋等均在那里任過教。這些教師在那里幾乎都是不拿工資的義務教學。當時“音樂組”學員(總共不到20人,而且都是少年)的所謂“工”,主要就是在社會上舉行頻繁的義演,為學校掙得少量的收入。為了演出的需要,除了表演一些現有的中外名曲外,也促使“音樂組”的學員(如莊嚴、黃曉莊、杜鳴心、熊克炎等)自己動手進行創作。黃曉莊大多數音樂作品就是為了當時“音樂組”的小型演出而寫的。
根據現在保留的曉莊的手稿(其中有的還是殘稿)及友人的回憶,他的創作大體可分為三類:1.獨唱歌曲;2.齊唱或合唱歌曲;3.少量器樂創作。
黃曉莊的獨唱歌曲有:《花》《眼淚》《守望》《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我的心呀,在家鄉》《秋思》《仰望同情的手》及《友情》(二重唱)等。這些作品大多采取帶伴奏(鋼琴或四把弦樂器)的“藝術歌曲”的模式。作品的題材上,如女聲獨唱《花》(又名《我不情愿呀,我的小冤家》,洪遒詞)以及《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丁香花開香又香》等,是反映在戰時環境中的愛情。曉莊對這類題材寫得較多,旋律流暢,感情質樸,表露出年輕人的真摯追求。有些(如《眼淚》《守望》《我的心呀,在家鄉》等)是表現人們在戰時對故鄉、親人的想念和對敵人的痛恨。還有根據古代詩詞譜寫的,如《秋思》。盡管它還沒有淋漓盡致地深挖出古詩詞的含蓄意蘊,但作品在寧靜中體現出的悠悠真情,對一位還不到20歲的青年作者來講是難能可貴的。
黃曉莊的齊唱及合唱作品是他音樂創作中最主要的部分,題材的面寬而緊貼時代,音樂表述方式多樣而性格突出,因而其社會影響也較大。其中像《學生從軍》《青年進行曲》《伸出同情的手》《迎今年的七七》等,都是以進行曲的方式體現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在陰暗重壓的“大后方”仍堅持支援前線進行抗日斗爭的的強烈決心。在《學生從軍》中,作者運用的二部合唱似乎受到當時中國青年人所喜愛的一些蘇聯歌曲的影響,音樂的進行果敢有力、充滿朝氣。《鳳凰山上》雖然是“育才”學生對學校的歌頌,但其中也透發了時代的氣息和開朗奮發的性格。《十字歌》則是一首非常親切的民歌式的齊唱曲,表現出作者對民間音樂開始發生興趣。齊唱曲《往哪里逃》(舒模詞)可能是曉莊最后一首社會影響較大的作品。該曲寫于1944年“湘桂大撤退”之后,表現了人民群眾對反動派不顧國家人民、只圖保存自己實力的憤怒和抗議。 這首作品也表現出作者力圖運用老百姓所熟悉的語言的“民族化”的追求。旋律的進行既流暢又有力,作品后半部的二部卡農的寫法自由靈活,可以看出冼星海的合唱音樂對他的有益影響。類似的還有混聲四部合唱《元旦又到了》,作者以模仿民間鑼鼓歌唱的手法,生動體現了在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獲得勝利的形勢下,中國人民預祝抗日戰爭勝利的歡欣鼓舞的心情。我們知道當時在解放區曾出現了這樣的作品,但在“大后方”則比較少見。女聲領唱及混聲合唱《我們立在》(馮至詞),可以說是曉莊生前最宏偉的一首大型合唱作品。作者運用豐富的對位化的合唱技法,配以生動的鋼琴伴奏,表現了中國人民的自信和自豪。上述作品,除少數選用當時著名詩人馮至、袁水拍、王亞平等的作品以及古詩詞外,其他作品都由他本人作詞。他曾是“育才學校”學生詩歌社“榴火社”的成員。
黃曉莊的器樂創作數量不多,只有兩首大提琴獨奏和一首鋼琴獨奏。他的大提琴獨奏作品在創作上還沒有充分地展開。這與他在這個領域還處在學習中,對如何發揮大提琴的演奏特點特別是與中國大提琴曲的創作還只是處于初創的階段有關。他的鋼琴獨奏《小花鼓》是一首表現力豐富、音樂生動、形式結構嚴謹的作品,對鋼琴技巧的發揮也有一定的深度。這在當時中國鋼琴音樂創作還不多的情況下,應是一首值得矚目的作品。可惜作者的原譜已經遺失。最近杜鳴心同志根據回憶對作品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將在《音樂創作》上發表。我相信它定能成為一首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鋼琴文獻,充實到中國鋼琴音樂遺產的寶庫中。
黃曉莊到延安后也沒有中斷創作,據他在日記中記載,他曾寫了《當我漫步在延河邊》《防旱備荒小調》《紅軍打進了柏林城》等,并且正在構思一部以陜北民歌為主題的《和平交響樂》。遺憾的是上述手稿在解放戰爭的戰亂中均遺失了。
作為一個創作生涯非常短暫的青年作曲家,黃曉莊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他并沒有得到扎實的技術訓練,沒有得到安定的創作環境,只憑自己的熱情和才氣橫溢,就在短短幾年時間里留下各種形式的幾十首作品(陶行知對他的挽辭中提到:“肄業一學期中作曲48首”)是難能可貴的。當然,不能將他與一位成熟的作曲家來相比,他的有些作品還顯得稚嫩,對技法的運用還不夠嫻熟。這是客觀歷史環境的限制所造成的,也是中國音樂界的不幸所致。
古人喜歡把一些充滿才情而又不幸夭折的青年比作遭受無情風雨摧殘的鮮花。而曉莊則是在含苞欲放之年就遭受不幸的典型,更顯得中國的過去真是不幸!這個不幸的年代現在已經過去整整60年了,中國已經度過了自己的不幸,走上生氣勃勃的新時代。今天我們紀念他,不僅是為了回顧過去的音樂史,補上過去忽略的這一筆,更重要的是,我們作為后輩的音樂工作者,應以更大的努力,從前輩的遺業中取得有益的啟示,為中國音樂的美好未來作出新的貢獻!
汪毓和 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專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