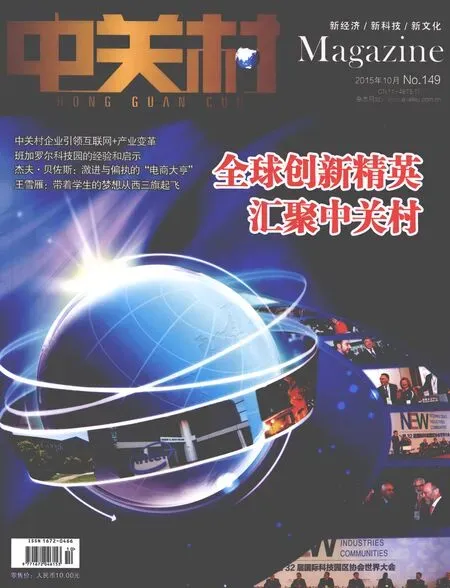呼喚創新型政企關系
魏 新

中國經濟若想持續高速增長,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根本出路,打造創新型企業是根本基礎。兩個根本之根本是,創新型國家與創新型企業的創新型政企關系。國家創新體系與企業創新體系必須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動,它既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大包大攬,也不同于前些年轉軌時期的不管不顧大撒把。
政府是企業的“鎮山之寶”
前不久,我再次考察了韓國三星集團而感觸更深。三星經驗一直是我思考的課題:中國的市場比韓國廣闊,中國的工業配套體系也比韓國發達,中國的人力資源也比韓國豐富,但迄今為止,為什么沒有一家中國企業(不包括資源性或壟斷型)能夠達到三星集團的高度?
韓國三星在1969年,憑借為日本三洋貼牌加工小黑白電視機起步。1972年開始生產三星品牌的黑白電視機。20年后,三星董事長李健熙在1993年提出“把三星電子打造成世界一流IT企業”的宏偉藍圖,如今三星電子在八個領域居全球第一,他們的目標完全達到了。三星集團2004年純利潤達103億美元。
三星的戰略遠見是令人欽佩的。但三星的成功之路給我的最大啟示是,政府以超級手段扶持了三星的超級能力,進而以超速成長成為超大企業而獲取超額利潤。韓國政府當年幾乎傾其所有,以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來扶持三星、現代等本國重點企業。政府出面擔保,金融機構給企業巨額貸款,其數目曾高達被扶持企業凈資產的很多倍。同時,政府出面把海外的韓國精英請回來致力于國內技術研發。此外,韓國政府的大量采購訂單也為韓國企業起飛助一臂之力。盡管韓國于1997年爆發金融危機,金融系統和政府財政險些崩潰,由此全球經濟界人士對韓國模式頗有微詞。但風雨過后,三星等企業真正成為世界巨頭,它們一方面還本付息,另一方面巨額納稅,其回報促進了韓國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我了解得知,韓國政府并非不知道當年之舉風險甚大,但不鋌而走險將永無出路,在權衡利弊之后以破釜沉舟的魄力,將巨額資金扶持當作風險投資,殺出血路而一舉成功。韓國政府大賭大贏,韓國企業大舉大得。
放眼世界,不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幾乎所有重大技術創新背后都有政府之手的強力推動與支撐。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屹立于全球市場的企業,無一不得到本國政府的垂青恩惠乃至鼎力相助。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也是企業的“鎮山之寶”。
三分天下“扶”其一
聚焦中國,華為公司的成功已為世人矚目。華為人在“貿工技”道路上為之整整奮斗了16年,終于在通訊領域的高端環節擁有了自主核心技術,并且在全球市場上獲得了較高附加值。殊不知,華為近幾年的研發投入每年都高達數十億元,占其銷售額的10%乃至更高比例,而華為自身利潤不能承受之重,在其背后是政府巨手的推動與支持。
中國為何沒有多出幾個華為?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企業重大創新能力的形成與增強既有賴于國家創新體系的培養扶持,也必須得益于企業與國家兩套體系的互動式相輔相成。同樣值得指出的是,普遍扶持的策略已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中國應該認真梳理產業,在重點扶持行業還需篩選重點扶持企業,重在取舍。 “撒芝麻鹽式”的普遍扶持實際是無足輕重的,調動廣大企業的普遍積極性只是一廂情愿。有限資金再不能無限分散。
我對應由政府重點扶持的行業與企業有一個“三分法”:
第一類是在全球的新興領域,中國企業與國外企業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對于諸如互聯網之類的新興行業的新興企業,政府扶持重心應在軟環境而非硬投入。這些行業和企業因想象空間巨大,并且因其不確定性而風險巨大,因此最適合利用國內民間風險投資與國外風險投資,尤其是利用國際資本市場。
第二類是對于發達國家大量轉移且中國不具優勢的夕陽產業,政府應以“適者生存”原則而徹底放手,任其在市場搏殺而獲取頑強生命力。
第三類是全球市場前景廣闊且具一定競爭優勢的成熟行業,國家必須以非常方式大力扶持其超常規發展。因為在成熟行業按部就班發展不可能趕超,只能是亦步亦趨的跟隨者,永遠無法實現跨越式發展而成為行業領導者。
中國目前的優秀企業大都在這些成熟行業,但處于行業的中下端位置,不僅無暴利可言,甚至利潤稀薄。這些成熟行業技術發展趨勢清晰,一般不會出現技術方向突變而行業格局大變,有助于中國企業在國家扶持下拾級而上地爬升到產業鏈高端環節。同時,這些行業需要巨大市場作為載體,而中國強大的內需足以把中國企業養成全球的重量級強手,而這些重量級企業一旦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其體量強大將成為中國經濟的強有力支柱。并且,中國產業將圍繞這些超級航母而形成配套的產業集群,形成一種強大實力,避免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低端化與邊緣化危險,使得中國經濟進入全球經濟主流。
我們必須承認的普遍現實是,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必須巨額投入研發,而利潤稀薄則又無力加大研發投入。以方正為例,方正具有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對于某些領域的技術方向與趨勢也具有較強把握能力,甚至清楚能夠帶來超額利潤的主攻目標,但這些重大研發所需投入少則幾億多則幾十億。所以,方正在幾個具有看得見的廣闊前景的重大研發項目上,都只能憑著自身的利潤慢慢滾動投入,下了狠心卻下不了狠手。
中國特色自主創新
改革開放28年來,中國的政企關系的變革一直以“政企分開”為主旋律,這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獨特歷史背景所造成。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通過計劃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進行嚴格管理和調控,企業不過是行業主管部門的生產車間。從1978年開始轉軌,政府逐漸給企業放權松綁。而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雙軌運行時期,政府部門的“越位”、“缺位”及“錯位”這三位于一體之中,但總體趨勢是政府對企業在放權讓利的同時,直接扶持力度銳減。我認為,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政府轉變職能的又一場“自我革命”開始,在面對強大的國際競爭壓力下,政府如何扶持競爭力相對薄弱的中國企業,將成為突出而重大的主題。
2005年10月,中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在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又強調“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我的理解是,在明確企業為創新主體后,政府不僅要迅速進行推動企業創新的制度創新,更需要建立國家扶持企業創新的支撐體系,政府創新與企業創新與時俱進。
創新型政企關系的第一關鍵是政府要界定清晰“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領域與范疇,另一關鍵是政府扶持企業創新時應當“如何為”。在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一語中的:抓緊制定切實有效的激勵政策,完善鼓勵自主創新的金融財稅政策,改善對高新技術企業的信貸服務和融資環境。
企業創新有風險,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政府與企業共擔風險。一些創新風險可以通過企業的研發管理與風險控制加以規避,另一些風險卻只能共同面對,這是創新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我非常相信我們中國人的創造精神與聰明才智,只要國家能夠以大投入支持大創新,中國企業就能創出大奇跡。“神六”當數尖端科技,而中國人的研發投入只相當于美國人的1/9。因此,創新型政企關系是政府必須對重點企業的重大創新進行重磅扶持。
當今中國,許多重要領域的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仍需大量進口,科技創新的空間巨大。中國多數企業不是不想自主創新,不是不清楚創新所創造的超額價值。但是重大的科技創新需要雄厚的實力,當中國企業自身能力不足,國家必須作為堅實后盾。
(作者系方正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