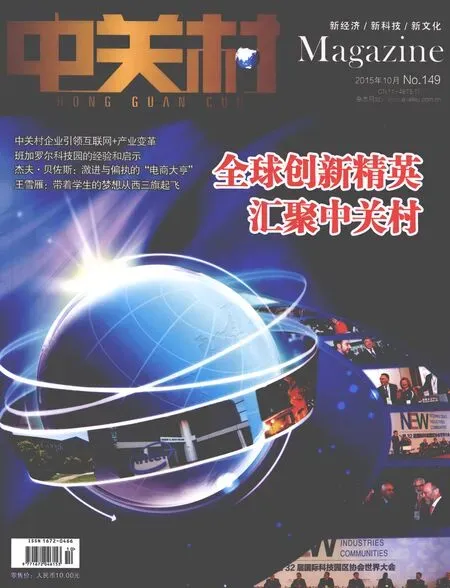任正非的大是非
劉 頔

華為正當年,任正非是本土企業家里相對更成熟、更老練和更神勇的企業家之一。但是,華為有一個致命的短板,任正非愈來愈接近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旋渦中心——企業家是靠自己的個性來完善一間企業并一往無前?還是靠確立、樹立和強化企業的價值觀來使公司基業常青?
另類華為,異樣任正非,如果能在獨來獨往的天馬行空中將自己在脫穎而出后成為世界級企業和一流企業家,那一定是本土企業在世界市場上因為“黑馬”和“冷門”而成就輝煌的圖騰。但眼下的問題是,任正非一生打拼奮斗不息的——結果:是一個著名的企業家?是一個了不起的企業?是一種偉大的產品或服務?還是一種企業家精神抑或是一種燦爛的企業文化?
企業家要不要有個性?
將企業的“企”字拆開,說的是企業止于人。做企業就是做人。于是,松下幸之助有“先造人后造物”之說。而像比爾·蓋茨那樣通過發明產品、創立企業和賺得金錢滿甕之后再將慈善進行到底,似乎是企業家作為人的價值的最終體現,也是企業家的國際性流行活法兒。
在任正非這里,正在造著的即不是人,也不是物,更不全然是錢,而是“神”。由神秘企業家創立的神奇企業,顯示出盤古開天的氣魄,演繹了夸父逐日的慘烈,弘揚了儒墨道法的精髓——任正非將學者的思辨、智者的膽識、軍人的風度、大師的風范、思想家的深刻和作家的浪漫……和著華為20年風雨和愈來愈彩虹的經歷,打造了一尊神圣——任正非和他的傳奇:以2萬元起家,20年做到300多百億。退伍軍人任正非超越了市場領先了同仁創造的華為企業,成為本土IT行業不可多得的功勛性企業。其“軍人”、“硬漢”、“土狼”等稱謂恰恰是這一切成就的背景式原因。
華為太有個性了。它不上市,不合資,在自我封閉中自力更生中獨闖江湖;它不引進,不吸收,在獨立自主進行科研開發中閉目塞聽;它不怕鬼,不聽邪,在全世界范圍內逼平思科叫板微軟令愛立信膽寒。
如果這樣的企業也能成功,那一定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并領先世界的標志性企業的樣板式勝利。而假如這樣的企業失敗了,但任正非仍然成功——因為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人性輸出和人格表現。
企業家的個性,其因素包括:先天遺傳變異、后天專業學習、社會影響、文化侵淫和經歷、閱歷等。將其中的某些方面加以綜合性的強化,就成為其個性特征。而一旦創辦了企業,就將這種個性“帶入”企業文化之中。
考察華為的“個性”,其實是任正非的“人性遺傳變異”。 “任正非出身普通家庭,建筑學院畢業,從過軍,他的技術成就曾獲得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1978年他參加過全國科技大會,是年輕人中的技術尖子。”透過這行簡單的介紹,復雜的華為和任正非之謎昭然若揭了。
因為“出身普通家庭”,所以為人謹慎,行事低調;“從過軍”,所以形成軍人作風;因為出身平凡但卻在從軍后因為“技術發明”而使個人價值大放異彩——任正非的這種經歷,是華為成長、成功和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任正非在創立了企業后更加放大個性的動機,更是任正非將華為創辦成為“物我一體”即自我價值客觀化的初衷。
人性,仁者愛人是人性,好勇斗狠也是人性。從血染沙場到決戰商場,有那么一種人,他們天生好斗,他們自強不息,他們以苦為樂,他們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任正非就是這樣的人。華為,就是這樣一個企業。他們,又都是本土文化的產物。
“軍人”,任正非是軍人,長虹的倪潤豐、三九的趙新先也是。將三個軍人出身的企業家聯系起來看,在管理風格和個人作風上,是不是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如果是借鑒軍隊管理的某些經驗,借鑒軍事戰爭的某些學說,本無可厚非。但是,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僅知識白領已經成為企業普通員工這一條,就不能照搬軍隊管理和強硬作風,因為它已經不合時宜和不得人心了。
“科技動物”,任正非堪稱純粹。早年延續下來的科技崇拜導致的后果是,在中國企業處在后發的科技陣營里,幾乎所有科技型企業都是靠引進+開發、大引進+小開發的模式進行科技創新的時候,任正非和他的華為以10%甚至大于這個數字的科技投入在關起門來做下去里自力更生了。
而事實上,華為錯過了2G的市場時機,在GSM上投入了十幾億元研發經費,在1998年就獲得了全套設備的入網許可證,但打拼了八年,在國內無線市場上仍沒有多少份額,甚至沒有收回成本。 目前,華為在3G上又展開了更大規模的研發和市場開拓,每年近10億元的研發投入,已經堅持了八年,因為在國內市場收不回成本,華為不得不到海外尋找生存空間。
于是,我們看到,純粹是任正非個人的從軍經歷,也是私人化的愛好上了科技發明,最后全都變成了——企業的邏輯、企業的市場運作規律和公司文化的精髓!
企業價值觀因何迷失?
創造價值即利基是企業的第一使命。華為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制造出多少適應市場和客戶需求的產品并由此獲得一定的利潤。
華為為此奮斗了20多年,銷售指標和業績在幾經徘徊中沖頂,在沖浪式遞增后多次遭遇滯漲——任正非的市場預期即此類企業應該達到的高度與華為實際的贏利水平,一直壓得所有人都透不過氣來。英特爾每年能做到300多億,華為也能。但前者卻是美元。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差距,直到今天,當胡新宇因為加班而染上過勞死之后,華為的“床墊文化”才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而就在輿論界和操作層紛紛反思其間的時候,任正非繼續強調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做強做大華為,以此對員工過勞死與床墊文化等做了回應。
艱苦奮斗,永遠是企業文化的內涵。特別是在IT行業,當時間與效率成為它的鐵律,在快魚與慢魚總是處在生死攸關之際,那些擔負重大科研課題的研究人員,其實就是要豁出命來拼死一博的。
但是,一個企業,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上能否以這樣的大勇氣與相應的大智慧的統一來將艱苦奮斗進行到底。
華為的企業文化,說到家其實是任正非文化。20年華為,最大的文化積淀是任正非盡管從不接受媒體采訪但還是廣為流傳的一些文章與著述。任正非用了一種媒體和輿論無法“信息過濾”的方式,類似宗教的傳教術規范了統一了以“華為基本法”為代表的“任正非主義”。
然后,透過整篇“基本法”和其它相關文章,任正非的大疏漏是——當以IT為前沿的全球管理科學由管物(產品管理)→管人(勞動管理)→管理知識(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中,華為顯然并沒有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知識管理”平臺。
試舉一例。李一男在華為四年,以火箭速度升為華為的副總。因為缺少一種關于“職業生涯設計”的知識,所以無法進行“員工生涯規劃”的管理。結果,李一男,還有好多華為的專業技術人員在“偷藝”后辭職華為,另起爐灶,一方面令任正非痛心疾首使華為遭受一次次重創;另一方面,像李一男這樣的“專業型”人才,因為到最后也無法成功轉型為“管理型”,在迷途知返中,還是不得要領:成功了,蒙的;失敗了,更蒙。
如果有人能為李一男在大學畢業來到企業后,在繼續教育中補上這一課,使他認清自己的專業特長、人文特征,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從而堅定地走專業發展道路,何至于“另立山頭”從而導致“拍賣港灣”到最后還是舊船票登上新客船的折騰呢?
如果李一男懂得“職業生涯設計”這門學科, 他應該在成為華為的技術副總裁后,爭取再做到財物、人力和營銷副總,在利用華為的內部資源在企業內部先將自己的羽翼真正豐滿起來。如果條件不允許,他也可以和那些副總成為知己通過“偷藝”來長自己的見識。他甚至可以將那些副總策反,與自己一道在離經叛道中再造一個華為。然后收購華為。
可惜的是,在利潤尺度和市場杠桿打壓下的華為,缺少這樣一種基于“知識管理”的人力資源戰略。
像華為這樣的IT公司,一方面,通過約束和競爭兩個機制來促進企業效率與效益的提高,已經成為每個企業在管理實踐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而另一方面,這種“高壓”的“壓強”的管理中形成的職場壓力,又使得員工們不堪重負,導致管理層與基本員工層的心理摩擦、矛盾激化和一系列突發事件的發生,與此相伴隨的還有離職率上升,出勤率下降,使整個企業蔓延一種不安、惶恐和應激情緒。這種可怕的狀態,可以導致情緒失控和心理紊亂,最后形成心理恐懼和應激狀態,是一種“精神瘟疫”,在軍隊里就是“厭戰”和由此而來的“兵敗如山倒”;而在職場上,如果任其蔓延,就會使成本上升,士氣低落,業績徘徊,產生一種很令人費解的現象——人們仿佛更忙了,但就是沒效益、沒生氣和沒效率。
從創業伊始開始,任正非多次撰文,不斷演講,幾乎忙的是一件事情——將華為的4萬員工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這個出發點沒錯。但錯在,第一,華為的員工是知識工人,知識工人的一個特質是,不僅要賺錢養家糊口,還要實現人生價值升華生命質量即活出自我(就像任正非那樣的叱咤風云和特立獨行——誰知道就在華為的4萬員工里有多少羨慕并且發誓要比學趕幫超任正非的嗎?)第二,對待這些和傳統意義上的員工有本質區別的知識白、銀、金領們,唯一有效的管理是“知識管理”——讓他們在繼續教育中獲得知識創新,在知識創新中昂揚革命斗志,將華為的事業當做自己的事業。
但是,還有一個“終點”,華為人幾乎都不知道——跟著任正非這樣干下去,員工們能夠最終得到什么?讓任正非這么領導下去,華為最終是什么樣的?華為的“愿景”、任正非的創新、4萬員工的出路、中國IT樣板企業——向何處去?能去到哪里?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將一腔熱學和滿腹經綸奉獻給了華為,他們這樣做的價值觀是什么?
在“藍領”占很大比重的海爾,張瑞敏還是創立了激勵員工創新的平臺,其中有一條是,如果哪個工人發明了科學的工藝和流程,就用誰的名字來命名并可以千秋萬代傳誦。
怎樣復制總經理?
MBA之所以將“復制總經理”作為經理人的一個必須完成的使命,其一是說,總經理不太好復制;其二是說,得總經理自己來復制;其三是說,只有由總經理自己來復制,才好復制。
任正非,就是個不好復制的總經理。
首先,強烈的個性化色彩是任正非作為總經理的特征。也就是說,即使想復制,原件有,但沒有復印紙。任正非不是“生產線”上的產品,無法批量生產。他是一瓶雪藏的老酒,是一件沉封許久的古玩,是一匹霹靂呼嘯的戰馬,是一位出奇制勝的劍客。于是,按流行的國際通用的“職業經理人”來衡量,任正非應該是不“合格”。但是,他卻創立了不僅合格而且優秀的華為公司——這就是中國企業家的世紀性和世界性問題。
其次,仍然帶有強烈“草創”色彩的至今也沒有找到“北”的任正非,復制他的什么?“人不能同時踏入同一條河流”,古希臘哲學的這個命題,強調了中國老百姓的一句大實話:打下啥底兒就是啥底兒。
任正非單槍匹馬創業,沒有合作伙伴,在形單影只中這么些年里,始終沒有能與他齊肩的戰友和同伴,那個被人們好不容易挑出來的孫亞芳,很像張瑞敏身后的甘為人梯的楊綿綿,卻不像格力的那位說一不二的董明珠,她沒有李一男那樣突出的能力,也沒有很多副總的驕人業績。她與任正非在性格上可以形成互補,但卻很難成為任正非的繼任。
問題的關鍵似乎不在由誰來接替任正非,而在于接替他的什么?或者說任正非交給接班人一個什么樣的華為——華為是一家優秀的企業,但卻不是一個成型的、有數的和能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企業,這是一個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充滿了變數的和前途未卜的企業,是換了任何人都找不到它的機關、要害和規律的公司,在任正非強烈的、傳統的和深刻的憂患意識作用下,華為生于憂患,卻無法終于安樂。
再次,這樣一個充滿未知和變數的企業,其實就是沒有完成公司文化與企業家文化的磨合,或者說怎樣跟進也無法和任正非踏出一個節拍的華為,能產生“任正非二世”嗎?
華為有400多名中高級管理者,副總裁以上的100多位,副總裁又分常務副總裁、高級副總裁、執行副總裁、部門副總裁、地區副總裁、產品副總裁等等。這說明華為有很深厚的干部基礎,但反過來也使很多人感到競爭接班人難度巨大。
在這樣的競爭狀態下,最關鍵的是華為是否有一套成熟的“復制總經理”的體制和模式。要不然,分布在有50多萬員工之眾的福特汽車公司怎么“復制總經理”?總是像華為這樣找不到“北”嗎?
而問題的關鍵是,當華為就是任正非和任正非就是華為這樣的理念,幾乎就要掩蓋了華為科學地建立“復制總經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這幾年個最要命的問題時,任正非想不想、要不要和能不能看開華為并進一步看開自己的生前身后事?
一位呼嘯著的“吶喊”者,能否打破華為的“鐵屋子”?當所有的人將目光都最后投向任正非,問題的解決就開始接近了真理。
最后,說到底,能否復制任正非?不能!“世界上連兩片相同的葉子都沒有”。
華為有幾種活法?應該不只一種!魚有魚路,蝦有蝦路嘛!
“任正非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路線嗎?
思想家任正非,在成功的創立并將華為做到如日中天之后,是滿足于做那個窩在地上以手托腮做苦思冥想狀(羅丹作品)的“思想者”?還是希望自己成為建立12件大功的大英雄赫刺克勒斯?
企業家任正非,是做一家最成功的中國樣板企業?是發明創造出一種全球性的絕世產品?還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緒、張揚了個性和實現了個人價值最大化中“附帶”著將一個其實并不扎實和并不完善的華為——奉獻給世人?
總之,任正非已經帶來的最具價值的思考是——中國企業家和本土企業如何實現真正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