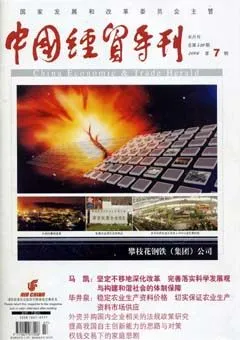議歐盟反傾銷法與對華反傾銷中的不合理因素及對策
(一)
自1979年第一起歐盟對華反傾銷案至今20多年的時間里,許多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被歐盟反傾銷法判為傾銷,即使這些中國企業對歐盟市場索取的出口價高于其產品在中國國內的市場價。但是,在歐盟反傾銷法下,他們不僅被判傾銷,并且經常被施加高額的反傾銷稅。中國企業有理由問:歐盟反傾銷法關于中國出口商品的傾銷判定標準及其實施結果是否合理公正? 下面我們解讀歐盟對華反傾銷關于傾銷判定的法律標準及相關實踐,以及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事實上,正是由于這些不合理的因素,導致了對中國企業的不公正的待遇。
一、根據GATT和WTO反傾銷協議的要求,歐盟反傾銷法將傾銷存在作為實施反傾銷措施的首要行為要件。在歐盟反傾銷法中,如果一國出口商品對歐盟的出口價,低于其在正常貿易過程中在本國市場銷售的相似產品的可比價(或正常價值),則構成傾銷。如果該進口傾銷品對歐盟產業的主要部分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或損害的威脅,如果歐盟委員會認為對其征收反傾銷稅符合共同體利益,依據歐盟反傾銷法的規定,對該進口品征收反傾銷稅的三個必要的法律要件已經具備。
可見,傾銷存在是實施反傾銷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根據歐盟反傾銷法,傾銷存在的判定必須以正確確定出口價、正常價值,以及對兩者的公正比較為前提。歐盟委員會所進行的傾銷調查就是針對出口商的出口價、正常價值所展開的一系列的認證過程,并最終通過對兩者進行適當的比較,得出是否傾銷以及傾銷多少的結論。由于出口價和正常價值是確定傾銷存在與否的兩個基本因素,所以,相關利益方特別是被告方有理由知道決定他們是否傾銷的主要因素——出口價和正常價值是怎樣被確定下來的。
但在歐盟對華反傾銷實踐中,歐盟委員會經常以信息提供者的資料的保密性為理由,拒絕向中國被告透露關于出口價和正常價值的基礎數據、計算方法以及計算過程。這樣一來,在出口價、正常價值的認定過程中,如果存在任何錯誤或使用了任何不適當的方法,中國被告無法知道,無法為自己辯護,也就失去了指出和要求更正的機會。由于中國被告無法知道他們的正常價值是怎樣被確定的,他們的平均出口價格是怎樣被計算出來的,也就無法知道關于他們的傾銷的結論最終是怎樣被決定的。中國企業無法就這些構成傾銷的主要的因素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說,在這樣的反傾銷訴訟過程中,他們的基本自衛權利被剝奪了,這對中國企業是極為不公平的。
二、歐盟反傾銷法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傾銷判定的標準和實踐,對被告存在更多的不公正的因素。根據歐盟反傾銷法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傾銷判定的相關規定,非市場經濟國家傾銷商品的國內價格,由于受國家控制,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價值,不能被用來作為正常價值,因而市場經濟第三國的同類產品的價格,通常被用來代替非市場經濟國家出口商品的正常價值,并以這個替代的正常價值作為判定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商品是否傾銷及傾銷多少的依據。這樣一來,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商品的傾銷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替代價值的大小,也就是取決于替代國的選擇結果。而在歐盟反傾銷法下,由于缺少一個明確的替代國的選擇標準,使得這樣的替代在總體上伴隨著潛在的不準確。
歐盟反傾銷法并沒有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替代國的選擇建立嚴格的標準。毆盟反傾銷法第二條第七款簡單地闡述了它的寬泛的替代國的選擇原則。它強調被選擇的替代國應該是“適當的”,“不是不合理的”。基于這一原則確定的替代國就是有效的。但該法沒有進一步說明什么是“不是不合理的”,什么是“適當”的,這給歐盟委員會選擇替代國的實踐提供了很大的自由決定權。正是依照這樣的標準,許多具有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被選為中國的替代國,致使來自中國的進口很容易被判傾銷,并且傾銷幅度被嚴重夸大。
基于這一極富彈性的選擇標準,使得替代國的選擇結果基本上是不可預計的,事實上導致了對中國企業的不公正的待遇。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依據這樣的選擇標準,他們無法預計哪個國家可能被歐盟選為替代國,什么價格可能被用來確定自己傾銷與否的依據。從而也就無法在進入歐盟市場前確定一個符合歐盟反傾銷法要求的正確的出口價格。中國企業只有在歐盟委員會對其產品啟動反傾銷調查后,才知道誰是替代國以及替代國的價格水平。而他們在確定對歐盟市場的出口價時,中國企業根本無法預見替代國價值,從而也就無法將自己的出口價確定在等于或略高于這一替代價值之上。由于替代國的選擇標準過于寬泛,選擇結果不可預計,使得中國企業無法通過自己預先的努力來了解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傾銷的發生。所以,歐盟反傾銷法關于替代國選擇的法律標準不具備法律在社會生活中對人們的行為所應該發揮的規范作用和指引作用。
三、面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對外開放的擴大,歐盟反傾銷法將中國視為完全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已經不符合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經濟現實。由于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也考慮到美國等其他西方國家反傾銷法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成果的承認,1998年歐盟理事會條例905/98 承認中國是一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對于中國的具有市場化取向的公司,在歐盟反傾銷程序中允許被賦予“市場經濟地位”和“個別對待”的待遇。但能否有資格享有這一待遇,舉證的責任在于中國公司自己。歐盟理事會條例規定了關于“市場經濟地位”和“個別對待”的相應標準,只要中國公司能夠證明自己已具備其規定的條件,在反傾銷程序中就可以按市場經濟國家出口商的方式加以對待,也就是符合條件的公司可以使用自己的價格和成本資料(公司實際的正常價值)作為判定其是否傾銷的依據。新政策使那些能夠取得個別裁決的中國公司獲得了同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商基本相同的待遇,這一改變緩解了對中國企業的不公正的對待,使得針對他們的傾銷的決定,與以前相比,較少了主觀性,較多了連續性和可預見性。盡管這一改變滯后于其他的主要西方國家的反傾銷法,但它畢竟是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予以承認的方向上的積極的進步。
但是,不幸的是,條例同時規定,替代國方法在總體上繼續有效,對于不能得到市場經濟地位和個別對待的企業,仍然繼續使用替代國的方法。而且,由于條例對“市場經濟地位”及“個別對待”所規定的條件極其嚴格。僅有極少數的中國企業可以獲得這一待遇。
(二)
通過對歐盟反傾銷法及其對華反傾銷實踐的研究,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歐盟對華反傾銷存在許多明顯的不合理因素,事實上導致了對中國企業的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時,這些不合理的因素也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大量的抗辯的機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以這些不合理、不公正之處為突破口,為贏得自己的公正的貿易利益和正當權利不斷地據理力爭,這對于改變自己在歐盟反傾銷法下所處的被動地位具有重要意義。雖然中國企業不能直接改變歐盟法律中對被告不合理、不公正的規定,但對于歐盟這樣的以判例為主的國家,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具體的個案來造成先例,以逐步改變其法律及實施中對中國被告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
雖然,在入世談判中,中國已接受美國、歐盟在反傾銷領域繼續使用替代國方法,但這并不妨礙中國政府、中國企業對替代國政策中不公正的做法提出挑戰。對于替代國政策的明顯的不合理、不公正之處,至少應要求做出幾方面的修改,第一:放寬中方企業對初始選定的替代國進行市場調研和發表評述的時限;第二,如果替代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國,應該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承認中國產品的比較成本優勢,允許根據中國產品的材料及人工價值,調低替代國的正常價值;第三,允許以享受正常調查待遇的中國企業的正常價值作為其他中國企業產品的正常價值。在這樣幾個原則問題上弄清是非曲直,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減輕替代國政策對中國的危害。特別是在最后一個問題上,中方應該不斷地據理力爭,目前,歐盟仍然不允許用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的中國企業的正常價值作為其他中國企業的參照的正常價值,而是再在中國境外找一個不相干的參照國。寧可選擇一個不相干的市場經濟第三國,也不用具有市場經濟地位的中國企業的資料,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對于這類法律上的明顯的不合理之處,中國企業完全有理由堅持要求歐方考慮和接受中方的立場和意見。
既然歐盟已經給中國企業提供了個別對待的政策,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擺脫替代國困擾的重要途徑是提供全部有力的證據,充分證明自己實現了市場經濟地位和個別對待的條件。中方企業應根據歐盟法律的要求,提交能夠說明自己是按照市場經濟運作的證據,來爭取獲得以自己的價格作為正常價值的資格。但對于不能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和個別對待的企業,唯一的戰略就是密切關注替代國方法的運用。中國企業不僅應該指出歐盟替代國法律和實踐中的不公正之處,而且,還應該在調查前和調查中盡可能多地收集資料和數據,主動地向歐盟委員會提出關于替代國選擇的合理建議。只要中方的意見理由充分,證據有力,我想歐盟委員會還是會考慮和接受中方的建議的。
我認為,要贏得一個實質性的進展,還取決于中國企業繼續深化改革的結果,也取決于世貿成員國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傾銷判定標準問題的新的共識。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應該為推動這一進程作積極的準備。同時,中國政府應充分利用世貿締約國身份,利用世貿爭端解決機制進行交涉和裁決,盡快爭取在爭端解決上的主動地位。
對反傾銷訴訟的應訴、抗辯是法律賦予中國企業的合法權利。放棄這一權利,既失去利益,又失去市場,也等于接受了別人對自己的不公正的對待。積極應訴是反傾銷案勝訴的前提條件。
(作者單位:遼寧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