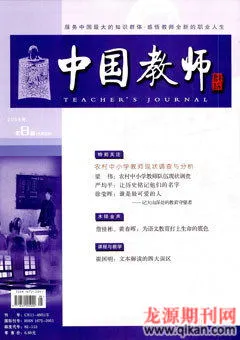“真性情”是作文的生命
真性情是生命的體驗,是個性的體現。真性情作文就是寫“真人、真事、真話、真情”,提倡說真話、抒真情。強調作文的真性情,是對人本思想的崇尚。
然而,受長期“應試模式”的束縛,作文教學中的“模式化”現狀,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學生的“真性情”作文。如作家冉云飛對2002年高考兩篇滿分作文(《愛心不銹》《君子,選擇了蘭草》)的評論,就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看了這兩篇高考作文,總體感覺文筆流暢,但文章詞藻華麗、頻繁使用排比,顯得空洞無真實感情。這不是學生之過,而在于高考作文命題者,強迫知識與人生觀尚不成型的學生,過早對道德進行評斷取舍。如是,學生失去自我,也就難以寫出好文章。就算學生沒動筆,美文與拙文已在老師心中立下標準。這是高考作文出題中的痼疾,20多年來如此。”這就在無形中嚴重壓抑了學生的真情實感。
同時,學生的真情實感如果與閱卷者的價值觀發生錯位,那么,學生十幾年的苦熬極有可能毀于一旦。最典型的就是在2003年高考中,一位在首屆全球華人少年寫作征文中榮獲金獎的南京金陵中學高三女生費瀅瀅,她毫無保留地把平時積淀的創作熱情釋放了出來,“從一個更高層次創造性地表達自己的理解和認知感情。”(作家蘇童語),難能可貴地寫成了《人情和季節》。作者拋開了眾多考生拼命迎合評卷者的終南捷徑,把應試文章寫得那樣地大膽,構思奇特,有小品文的風味,語言樸素,卻又含蓄、蘊藉。當然畢竟是關系重大的高考,作者還是不能完全免俗的,正如她自己所說的,“惟恐閱卷老師看不出我要表達的意思,特意加上了最后兩句畫龍點睛的話,沒想到,還是被判跑題”,只得了25分。這類現象值得我們思考和重視,同時也要考慮如何進一步完善高考作文評價。
“真性情”三個字是文學最基本的內核。古今中外文學作品浩如煙海,但真正的文學大師、能夠流傳后世的文學作品,都與“真性情”三個字分不開。從《詩經》到《紅樓夢》,從巴爾扎克到托爾斯泰…--拂去歷史的塵埃,都能看到的是“真性情”。
“好文章正是因為有鮮明的個性和創新的色彩才顯得分外有價值。”“真性情”是作文的生命。所以九年義務教育教材(2000年版)寫作訓練的第一課題目就是“作文——精神產品的獨創。”文中講到:我們要想創造閃爍著個性光彩,具有獨創性的“精神產品”,就需要打破條條框框,突破思維定勢,獨辟蹊徑,爭取“自由”。這種“自由”,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筆墨的自由”。所謂“精神的自由”,就是不輕易地為他人的意見所左右,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用自己的心靈去感悟。這就要在寫作訓練中,引導學生體味生活,始終如一地培養真情實感。
所謂“筆墨的自由”,指寫作內容是廣泛的,不受限制的形式是開放的,不受約束的,不要被一些人為的機械化的作文模式牽著鼻子走,在作文訓練中要淡化技巧,培養學生全神貫注于自己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用筆寫放膽文,以宣泄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用文字去貯藏自己不忍忘卻的瞬間,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勇氣和敢于批判的精神,做到以上兩點是寫好作文的第一步,也是使學生的精神產品具有獨創性的首要條件。總之,“個性”是作文的靈魂,獨創是文章的真正價值所在,讓我們在作文中大膽地用“我”的自由之筆,寫“我”的自得之語,抒發“我”的自然之情,顯“我”的自在之趣吧!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具有獨創性的精神產品。
2001年修訂的高考作文評分標準,就明確將感情真摯、真實列入其中,要求學生說真話、實話、心里話,不說假話、空話、套話。可見教材和高考對作文的真情實感是非常重視的。
我們的基礎教育“基本功”之扎實全球聞名,在國際學科“奧賽”中戰績驕人。然而,學生進入大學后創造意識和能力差卻是普遍現象,為什么會這樣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教學的過程壓抑了學生的“真性情”!所以我認為,作文倡導寫“真性情”,就是對學生創造性的一次解放。
當前學生作文普遍存在三招:一湊,二抄,三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文章擺不脫八股腔。重視和培養學生探求生活中獨特的感受,養成良好的習慣,把筆轉向摹寫自己的生活,逐步培養其獨創性和個性化的思維意識與能力,力求常中出新,平中見奇。這能從根本上解決寫作中抄襲和照搬的弊病。
由此可見,寫作中的真情實感何等重要,這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只要我們重視,認真引導,正確分析、認識具有極大差異的每一個學生,包括他們筆下出現的不同的作文,那么我們相信每個學生都能夠寫出“真性情”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