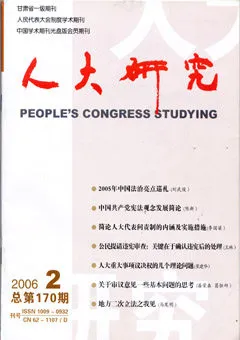為什么行使得不充分
近幾年來,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賦予的職責,對依法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進行了一些積極的探索和努力,討論、決定了一些重大事項。然而,從總體上看,這還是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多數地方人大常委會存在對重大事項決定權行使不充分的現象。一是作出有實質性、強制性的重大事項決議、決定數量不多。據有關報刊報道:某省過去10年中,共作出決議、決定141件,而有實質性、強制性的重大事項決議、決定只有5件,占4%。某市(縣級)人大常委會過去5年中共作出決議、決定68件,其中有實質性、強制性的重大事項決議、決定只有3件,占4%。二是作出的重大事項決議、決定質量不高,原則性要求多,概念化語氣濃,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三是“一府兩院”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重大事項欠主動,有些本屬人大常委會決定的事項都自己擅自越權決定了。四是對“一府兩院”貫徹實施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的重大事項決議、決定督查力度不大,沒有把重大事項決定權的行使納入法制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軌道,等等。造成地方人大常委會對重大事項決定權行使不充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筆者之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黨委決策權與人大決定權關系模糊
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是一項堅定不移的原則,而人大對重大事項擁有決定權也是憲法賦予的權力。黨委有領導權,人大有決定權,這兩種權力并不矛盾,它們都是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為根據,統一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中。然而,由于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以及“黨領導一切,指揮一切”和指導思想上的“一元化”、組織領導上的“一把手”、工作安排上的“一刀切”的觀念和習慣仍較為普遍,致使人大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的法律地位長期處于虛置狀態。同時,在我國的政治實踐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黨令政的現象還較為普遍,黨委領導權就極容易取代人大決定權。一些本應該由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的重大事項,卻由同級黨委直接決定,或由黨委、政府共同決定,或由黨委召開四套班子成員會議集體決定,避過了經過法定程序將黨委意圖變成國家意志的過程。
其二,政府行政權侵奪了人大決定權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應交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并作出決定。”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治”觀念作祟以及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憲政體制缺陷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遭受踐踏等因素影響,加之,縣級人大常委會1981年才成立,在此之前,縣級政府的運作模式一般都是重大事項請示同級黨委決定,并已形成工作習慣。縣級人大常委會成立后,一些政府組成人員仍習慣沿用以前的做法,以致常常出現越權行事的現象。一些長期從事人大工作的同志都有這樣的感慨:從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的字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權相當大,幾乎涵蓋了方方面面,但實際操作中,卻要受到來自黨委、政府的多種制約,黨委“給不給”、“給什么”、“給多少”,政府“想不想”、“聽不聽”、“做不做”,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權的行使。
其三,法律的原則規定“模糊”了人大決定權
雖然憲法和地方組織法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有規定,但對其范圍沒有作出全面的界定和說明,列舉的重大事項也過于原則、籠統,使地方人大常委會難以準確認定、把握和操作,“有法可依、無章可循”。有的地方人大常委會雖然也制定了關于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的條例或規定,但多數仍比較原則且不夠規范,使得地方人大對哪些事項屬于重大事項難以把握,而且經常造成人大常委會、政府對同一重大事項理解不一的問題,以至于人大常委會的“失職”和政府的“越權”行為經常發生。同時,有關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一府兩院”執行人大及其常委會關于重大事項決定的保障措施以及對不執行行為的懲罰條款,使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只具有理論上的約束力,而沒有實際的約束力,也影響并挫傷了地方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的積極性。
其四,自身工作乏力閑置了人大決定權
目前,在一部分地方人大常委會中,普遍存在對重大事項決定權不想用、不敢用、不善于用的問題。突出的現象:一是不能正確處理堅持黨的領導與自己依法履行職責的關系,從而導致人大常委會對屬于本行政區域里的重大事項很少作出決定的現象發生。二是擔心行使了重大事項決定權會影響與政府的關系,尤其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顧慮重重,動作遲緩,往往以“關系”出發,摸黨委意圖,觀“一府兩院”反應,因而,許多該由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重大事項也不決定了,明顯是政府及“兩院”越權決定的事情也不理直氣壯地追究了。三是對如何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也缺乏較為完備的決策及督查機制,使依法作出的決定失去了嚴肅性和權威性。
(作者單位:江蘇省高郵市人大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