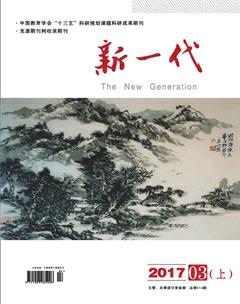淺析李商隱無題詩的意境
王治國
(通渭縣隴陽中學 甘肅 定西 743324)
摘 要:晚唐詩人李商隱以其獨創精神和獨特風格創造出朦朧幽深、含蓄雋永、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無題詩,把詩歌的欣賞推向了一個較高的藝術境界。在文學史上頗為引人矚目,為紛繁富麗的唐詩錦上添花,其中的一些名詞佳句廣為傳頌。本文筆者試從“深邃之美”“含蓄之美”“朦朧之美”三個方面來分析李商隱無題詩產生的的意境之美。
關鍵詞:李商隱:無題詩:意境
李商隱創作了大量無題詩并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在李商隱的詩作中,一部分以“無題”命名的詩,一般稱為無題詩;另有一些詩篇,以首句頭兩字作為題目,而題目與詩的內容又基本沒有聯系(如《錦瑟》《一片》)也可以看成無題詩。其中以《無題》為題的詩有十七首,代表了他詩歌的最高藝術成就。李商隱的無題詩意境含蓄、風格獨具、意境朦朧、深邃含蓄。詩中的形象,初讀使人產生恍惚迷離之感,因此有人評之為“隱詞詭奇”。但如果細細吟讀無題詩篇,就會有不同的感受,那種意境會使人陶醉,啟人遐想,令人回味無窮。下面我就從“深邃之美”“含蓄之美”“朦朧之美”三個方面來談談李商隱無題詩的意境之美。
一、深邃之美
晚唐前期宦官專權,藩鎮跋扈,黨爭激烈,世風薄劣,文人經世治國理想沉落,這一社會氛圍促使知識分子由詠贊外在盛世轉到追求個人內心情緒的表達,文人筆下多寫自己悲涼的心境。李商隱是位感情豐富的詩人,對人生充滿浪漫遐想,自小幾經離喪,飽受人生困苦,深感世態炎涼,情感細膩脆弱。由于獨特的人生經歷,詩人以病態的眼光看待世界,他偏愛使用枯敗陰冷的意象群、明麗凄冷的色彩,以此營構幽冷悲涼的詩境。在其無題詩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落蕊、枯荷、暮雨、飄燈、輕聲、流塵、細雨、珠淚、玉煙等枯敗陰冷的意象,如《春雨》一詩中為所愛者遠去而“悵臥”“寥落”“意多違”的心境是一層情思,進入尋訪不遇,雨中獨歸情景之中是又一層情思;設想對方遠路上的悲凄,是一層情思,回到夢醒后的環境中來,感慨夢境依稀,是又一層情思。書信難達的惆悵,表達得十分含蓄。思緒往而復歸,盤繞回旋。雨絲、燈影、珠箔等意象,美麗而細薄迷蒙,加上情緒的暗淡迷惘,詩境遂顯得凄美幽約,處處在含蓄美中體現出深邃意境。
二、含蓄之美
李商隱一生的坎坷遭際,使其詩注入了更為復雜的情感,著重表現處于重重壓抑之下難以舒展的情懷和充滿矛盾的思想。在藝術創作方面,他則追求隱蔽,著意隱藏自己的意圖,委婉地表達內容情志。詩人的代表作《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鵑”句,其中“托”字指托物言志、寓言假物,錢鐘書先生稱之為詩人的作詩之法。“托”一字顯出了李商隱詩歌筆觸深婉曲折的美學特征。將情感含蘊于形象之中,卻不作任何主觀說明,只給讀者提供豐富而富有想象力的形象,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間,讓讀者去品味蘊含在形象之中的“韻外之致”。即在讀者和詩歌形象之間造成一種距離,不同讀者基于自身閱歷和經驗對形象有不同解讀,這便產生了委婉曲折的美感效應。李商隱在其《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一詩中,它就是用委婉曲折的手法寫出了其愛情的曲折和內心的苦悶。這首詩開始就營造出一種離別時的傷感氣氛,情調是那么低沉,意境那么廣遠,孤獨之感,懷人之思,皆溢于言表。詩的首句中,兩個“難”使感情突兀而起,可見這段愛情本身就歷盡艱難曲折,轉而又以無力東風留不住春光,寓自己無法扭轉離別的悲局。然而在第二句作者筆鋒一轉,寫人雖分離,而“絲”不斷,“淚”未盡。“絲”同思,極言相思綿長,“淚”極言思念的悲苦,人不死,情永在。接下來第三句中,詩人以空靈的筆觸、虛實并用的手法,把讀者引入“一種相思,兩處閑愁”的纏綿境界。不言自己相思之苦,轉寫對方的境遇和心理,想像她因“愁”而“云鬢改”,擔心她難捱長夜月光的凄寒,婉轉道出了詩人自己的愁苦情狀。雖未直言,而思念之情盡顯。第四句在瀕于無望的情況下仍寄希望于青鳥傳書,含有自慰的意思,寄寓著詩人政治上屢遭挫折之后,既深感抱負難以實現,又執著地追求的矛盾。
三、朦朧之美
“撲朔迷離”就是模糊而難以分辨清楚。就詩歌而言,是指其表層藝術形象所顯現出來的一種難以琢磨或琢磨不透的思想感情。詩人往往不愿直接表達感受而閃爍其詞,隱約其義,忽斷忽續,或彼或此,使人產生一種朦朧、惝恍的審美感受。李商隱在其無題詩創作上就刻意追求隱蔽,即把自己的意圖隱沒于形象之后,通過生動的形象來迂回曲折地展露情思。這樣,詩中形象便產生了一種模糊的性質,具有了捉摸不定的迷離之美。李商隱的無題詩還常常以一些幾乎不相干的典故排列和似乎不相干的精巧象征從多個方面疊合起來,構成多棱面的、意蘊復雜的境界。但結構上隨意跳躍,從而形成有若干斷隔和空白的一系列意象,它們之間又有著某種內在的總體基調性聯系,生出一種飄忽不定、捉摸不透的美感張力。李商隱無題類詩在句與句之間,尤其是兩句為對的聯與聯之間,幾乎總是缺乏邏輯有序的相承關系,給入一種強烈的朦朧飄忽感。《錦瑟》一詩最具這一特征:首聯兩句中的多弦錦瑟與華年人生二者中缺乏一定的必然關聯,就如同尾聯兩句中的追憶此情與當時惘然二者也缺乏具體實在的連接一樣。而其最重要的中間兩聯中“莊生”“望帝”“滄海”“藍田”四句,呈現出李商隱無題詩典型的創作特征,遣詞用典極其工對精美,意境寄托極為深遠虛泛,但相互之間卻又基本毫無干連的奇特性狀,同時也傳達出了詩人迷惘、悲哀、傷感、虛幻的情緒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