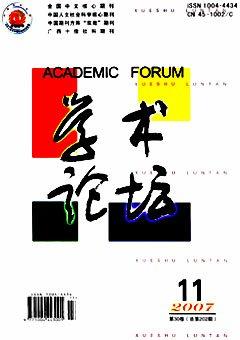需要的審美建構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陳 媛
[摘要]全球問題的凸現使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理想似乎成了一個“悖論”,人的需要的無限性與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是產生這一“悖論”的根據之一。人的需要具有可建構性,這種可建構性可以消解人的需要的無限性與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從而可以消解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悖論”。綜觀人的發展的當代境遇,消費主義和審美主義的共謀通過大眾傳媒建構出人的需要幻象,人的需要被欲望化、虛假化和泡沫化,人的發展深陷“物的圍困”之中。需要的審美建構是人類走出發展的當代物化困境的智慧選擇,也是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主體條件。
[關鍵詞]人的發展;需要;全面自由發展
[作者簡介]陳媛,廣西民族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廣西南寧530006
[中圖分類號]B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434(2007)11-0037-06
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人的發展的理想狀態,是共產主義的最高原則,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已經取得共識。但是,在學界內部和社會人群中,對于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實現、對于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持懷疑觀點或態度者亦始終存在。全球問題,尤其是資源與生態問題的凸現和惡化似乎使這種懷疑觀點和態度得到了某種客觀有力的支持。從馬克思實踐生存論立場出發來分析人的需要,可以發現人的需要的可建構性可以消解人的需要的無限性與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從而也可以消解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悖論”。
一、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悖論”
關于人的需要和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論述。這里只就其中涉及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需要和人的發展的關系、并比較廣泛地被引用和傳播的有關思想作為評述的根據。
在學術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需要和人的發展的關系的論述,比較廣泛地被引用的主要有以下幾處:一是共產主義社會是“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二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三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四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上的這幾個論述,對于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需要和人的發展的關系,人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一,在社會產品的分配上實現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第二,實現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第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人的需要的全面自由滿足為表征;第四,人的需要的全面自由滿足以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社會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為基礎。
在全球問題沒有凸現出來以前,人們質疑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的主要根據是:人的欲望是無限的,因此人的需要也是無限的,原有的需要滿足了,又會產生新的需要,社會永遠也不可能達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的水平,因此,人不可能實現全面自由發展,共產主義社會缺乏實現的可能性,最多是具有理想的價值。隨著全球問題,尤其是資源和生態問題的凸現,這樣一種懷疑的觀點和態度似乎得到了某種客觀有力的支持:人的需要是無限上升和發展的,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資源去滿足人的無限的需要,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人類永遠不能達到“按需分配”的狀態。由此,有的學者推論出:“只有當物質極大豐富,也就是相當于世界的無限擴大,世界大到人人能夠伸展的世界,才能有足夠條件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不會去壓迫、剝削和掠奪他人,每個人才能夠有自由。可惜這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一個世界不可能豐富到相當于包含無數個屬于個人的足夠大的可能世界的地步。一個有限的世界不可能變成一個無窮大的世界,這就是自由所以是個難題的真正底牌。這樣一來,如果一方面我們確認在共產主義社會可以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又肯定人的需要是無限發展和上升的,需要的滿足只能依賴于足夠多的產品。那么,從地球資源是有限的這個客觀事實來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顯然處在一種“悖論”境遇之中。既然人的需要不能夠全面自由滿足,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就實屬一種“烏托邦”的想像,共產主義社會永遠也不可能實現。
二、人的需要的可建構性及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悖論”的消解
前述的關于人的全面自由的“悖論”實際上是一個虛假的悖論,這個“悖論”的虛假性主要根源于對人的需要的先驗性、非歷史性和非社會性的理解。要證明這個“悖論”的虛假性,有必要先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實踐生存論立場對人的需要的有關論述。
需要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共同特征,它是生命活動的動力源,“生物體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更新依靠對外部事物的攝取和交換,因而客觀地存在一個需要及其滿足的問題”。對于人來說,人的動機、興趣、愿望都是需要的具體形式,它們引導著人的生命活動方向,從而也引導著人的發展方向。需要作為人的一個基本問題,在歷史上受到眾多思想家、哲學家的關注。但是,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家往往只從人的某一種屬性去理解人,從而把人的需要抽象化、思辨化和片面化。同以往的哲學家不同,馬克思從實踐生存論立場出發來理解人的需要,從而打開了通向人的真實存在的大門。“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實踐活動是人的一切秘密的誕生地。在人的問題上,馬克思一方面深刻地洞見到舊唯物主義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又睿智地發現唯心主義在人的主觀能動性問題上的極端性。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
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黑格爾雖然天才地指出勞動與人的關系,但遺憾的是,他的唯心主義哲學立場使他僅僅把勞動理解為精神勞動。費爾巴哈克服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根本缺陷,卻陷入直觀唯物主義的泥淖中。“費爾巴哈比‘純粹的唯物主義者有很大的優點:他承認人也是‘感性對象。”但是,費爾巴哈仍然沒有真正理解人,因為“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對象,而不是‘感性活動。因為他仍然停留在理論的領域內,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這一點且不說,他還從來沒有看到現實存在著的、活動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僅僅限于在感情范圍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只有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不僅把人當作感性對象,而且把人當作感性活動、當作主體來理解,我們才可能真正進入馬克思關于人的需要的真實視界。
從實踐生存論出發,馬克思把人的活動、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聯系和統一起來,從人的生命活動來理解人的本性,從人的生命活動去理解人的需要,“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人而言,“需要即他們的本性”。從人的生命活動來考察人的需要,我們可以發現人的需要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基本規定性:
第一,人的需要的客觀制約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特別說明過自己是從“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的人的問題的。“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現實的個人”有兩個最基本的要求:一是“現實的個人”不能離開自己的活動,特別是物質生產活動;二是“現實的個人”不能脫離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人是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進行滿足需要的生產活動的,“需要往往直接來自生產或以生產為基礎的情況”。人用以滿足自己需要的物質活動本身的客觀制約性規定了人的需要客觀制約性。
第二,需要的豐富多樣性。從人的活動的角度進行分析,人的需要包括三個最基本的方面:第一個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是生存需要,包括吃、住、喝等方面,因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第二個方面是發展的需要。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把人跟動物區別開來,這只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事實,而“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人不僅要生存,而且要發展,包括個體發展和類發展。第三,人還有享受的需要。人不僅要生存下去,而且還要生存得好、生存得美。“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在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人的生存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各自又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內容。“先是需要和滿足需要手段的諸多性,其次是具體的需要分解為個別的部份和方面,后者又轉而成為特殊化了,從而更抽象的各種不同需要。”
第三,人的需要的社會歷史性。“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人的需要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方面,總體上呈現不斷上升和發展的趨勢。在原始社會,人的需要是混沌未分化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沒有根本的界分,各個個體之間的需要比較一致。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的需要產生了分化,分化又進一步發展到尖銳的沖突,造成個體需要的巨大差異,使個體的人處于不同的發展狀態。其中,“一些人靠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數)得到了發展的壟斷權;而另一些人(多數)經常為滿足最迫切的需要而斗爭,因而暫時(在新的革命的生產力產生以前)失去了任何發展的可能性”。這種狀況,從人類整體來看就是帝國主義的發展方式,從公元前三十年的羅馬帝國開始,各種形形色色的帝國就是靠犧牲它的殖民國的需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的。從群體來看,剝削階級、統治階級、特殊行業、壟斷行業犧牲其他行業的需要來獲得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從個人角度看,“就個人自身來考察個人,個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變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發展,使他受限制”。人的需要的具體內容、滿足形式、滿足程度都歷史地變化著。
第四,人的需要的主體能動性。“需要也如同產品和各種勞動技能一樣,是生產出來的。”人通過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動來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人之為人經由人的自我創造來實現。動物依靠本能維持個體生命的存在和種生命的延續,它們的個體生命和種生命完全依賴自然所提供的現成條件。“動物用一套局限的手段和方法來滿足它同樣的局限的需要。人雖然也受這種限制,但同時證實他能越出這種限制并證實他的普遍性。”人類通過勞動自己生產自己所必須的生活資料。而“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了他自身的自然。使他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的控制”。勞動使人類取得了存在和發展的主動性,也獲得了需要的控制權和自主權。而且人
類越是發展,人的主體能力就越強,人對于自身需要的控制權和自主權就越大。
分析了人的需要的這幾個特性后,我們再來分析前述的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悖論”。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這是一個科學的、客觀的事實;人的需要是不斷上升和發展的,這也已經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所證明。但是,“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和“人的需要是不斷上升和發展的”這兩個事實并沒有構成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關系。首先,人的需要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的勞動實踐不僅滿足人的自然的、本能的生存需要,而且通過勞動實踐創造產生了人的社會的、能動的需要。人的需要的產生和實現雖然以特定的社會物質條件為前提,但是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不局限于這個前提,在根據這個前提來滿足人的已有需要的同時,他創造出人的新的需要,而人如何創造出新的需要、創造出什么樣的新的需要不僅取決于現存的物質生產條件,而且與人的價值理想密切相關。換而言之,人的需要是具有可建構性的,人的需要的上升和發展是有方向的,而把握這個方向的恰恰就是人自己。“人類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強度、滿足程度乃至特征,總是受先決條件制約的。對某種事情是做還是不做,是贊賞還是破壞,是擁有還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會成為一種需要,都取決于這樣做對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其次,人的需要是豐富的,“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和“人的需要是不斷上升和發展的”的所謂“悖論”,實質上是把人的需要偷換成了人的物質方面的需要。物質需要是人生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礎,但是,一方面物質需要的滿足有著心理的邊界(西方經濟學對此有精深的研究和現成的結論);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要才是人的超越本性的更為根本的表征。物質的東西與精神的東西相比較,物質的分享是消耗性的,隨著分享減少;精神的分享是增值性的,因分享而遞增。人的精神分享的增值性使得人的精神需要可以在不增加物質耗費的條件下獲得滿足和提升,精神需要的滿足與物質資源的消耗不是正比例關系,精神需要的不斷上升和發展與物質資源的有限性之間不構成悖論性關系。因此,人的需要是無限的,地球的資源確實也是有限的,但是人類可以通過合理建構人的需要的結構、控制滿足需要的方式來使有限資源滿足人類的無限需要。我們一方面承認人的需要的客觀制約性,另一方面又必須特別重視,并且合理運用人對自己的需要的建構能力,通過對需要的合理建構避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要的無限性之間的沖突,從而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三、人的需要的現實批判:日常生活“審美化”與人的需要幻象
日常生活審美化似乎是當代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真實景觀。其實由消費主義所主導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實質上是日常生活的非審美化,它制造了人的需要幻象,使“資源”成為人的發展的根本障礙,人的發展深陷物的圍困之中。
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我們可以發現“美”似乎無處不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的幽靈無孔不入——外套和內衣、鞋子和帽子、錘子和剪刀、羹匙和筷子、高腳杯和盛酒瓶、桌椅和床具、電話和錄音機、電視機和音像設備、手機和計算機、自行車和汽車、霓虹燈和廣告牌,無不體現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實存”。但是,這種所謂“審美化”本質上卻只是一種審美的異化,因為“它們是人創造的東西,它們是生活的寶貴助手,但它們當中的每一件同時又是一個陷阱,它們引誘人將生活本身與物混淆起來,把經驗與人工創造的東西混淆起來,將感覺與放棄自我、屈服混淆起來”。審美化社會的“審美”正在日益變成人的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宰制著現實的人。韋爾施對當代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的界定是十分恰當的:“‘審美化基本上是指非審美的東西變成或理解成為美。”當下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指認為消費主義和審美主義合流的產物,因為“這類日常生活審美化,大都服務于經濟的目的”。商人借助這樣一種生活審美化的趨勢,通過大眾傳媒操縱人的消費,用消費主義的原則去建構人的需要,企圖“把都市的、工業的和自然的環境整個改造成一個超級的審美世界”。但是這個“審美世界”不是為了產生美,而是為了產生各種各樣的需要幻象去引誘人沉溺于當下的物質快感之中,“美的整體充其量變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滑稽”。
人的需要的幻象首先表現為需要的欲望化。需要和欲望雖然都以消費為實現形式,但是二者在性質上是根本區別的,欲望的本質是占有,需要的本質是滿足。欲望把消費變成目的,而需要僅僅把消費看作是生存的條件。在前消費社會,“如果有一些人跌入消費標準之下,那么,就其他社會成員而言,這是一個道德恥辱;如果有一些人上升到消費標準之上,這同樣也是道德過失”。但是,在消費社會,“消費活動的靈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這是一個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無法理解的和反復無常的、本質上沒有所指的現象;這是一個自我產生和自我永恒的動機,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個目標或原因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進行辯解”。因此,消費時代的到來便使得…不斷地結束,不斷地重新開始不再是罪惡的象征,而是所有人都可得到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唯一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方式”。需要的欲望化帶來的后果是需要的虛假化。所有“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從外部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艱辛、侵略、痛苦和非正義永恒化的需要是‘虛假的需要”。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現行的大多數需要,諸如休息、娛樂、按廣告宣傳來處世和消費、愛和恨別人之所愛和所恨,都屬于虛假的需要這一范疇之列”。虛假需要的滿足“或許會使個人感到十分高興,但如果這樣的幸福會妨礙(他及旁人)認識整個社會的病態并把握醫治弊病的時機這一才能的發展的話,它就不是必須維護和保障的”。審美消費主義把虛假需要強加給人,使“人們似乎為商品而生活。小轎車、高清晰度的傳真裝置、錯層式家庭住宅以及廚房設備成了人們生活的靈魂”。需要幻象的具體表征是需要的“泡沫”效應,它使人的占有欲望無限膨脹。占有原本只是人的存在基礎,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當占有成為人生的主要目標和人的發展的主要衡量標尺,于是“人們把占有的范圍擴大了,對朋友、情人、旅行、藝術品都可以占有,就連上帝和自我也不例外”。“從前,人們總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一切都保存起來,盡可能長久地使用這些東西。購買一件什物的目的是為了保留它。那時人們的座右銘是:‘東西越舊越好!今天,人們買來物品是為了扔掉它。今天的口號是:消費,別留著。……今天的座右銘是:‘東西越新越好!新的就是美的,貴的就是美的,流行的就是美的,“新”、“貴”以及“流行”成為美的標準,整個社會被物欲所吞沒!
當人的需要被欲望所取代,人的精神緯度被架空了,甚至只能用物質的消費炫耀替代精神的滿
足,人的需要的不斷上升和發展被片面化為物質財富的占有和增加。于是,物質性宰制了精神性、理性遮蔽了感性、人宰制著自然、肉體需要擠壓著精神訴求,人的發展變成了物的占有和展示,手段變成了目的。
四、需要的審美建構: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主體條件
在當代社會,人在需要幻象的操縱下,人的活動完全被物質功利所宰制,人的發展為物所困,為物所累,為物所限,人的當代發展陷于物的困境之中,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思想上被質疑,在現實進程中受到阻礙。
“美是無一切利害關系的愉快的對象。”當對象向人顯現為審美對象時,人不是去占有和消費對象,而是去感受和欣賞對象。“審美帶有令人解放的性質,它讓對象保持它的自由和無限,不把它作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圖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對象既不顯得受我們人的壓抑和逼迫,又不顯得受其它外在事物的侵襲和征服。”只有用審美的態度去看對象,才能看到對象的美。這種美的態度,就是不合利害關系的態度,就是超功利性的態度。從人的生命存在特性來看,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自然生命的存在要求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為此,人首先要謀生,人的活動具有物質功利性的一面。但是,通過實踐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依靠勞動實踐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來同自然發生關系,人的意識具有主觀能動性,可以創造和把握人的活動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自然生命的物質功利性需要是人的一個前提性的規定,但是現實的人永遠都不會滿足于已有的規定性,他通過自己的活動創造和生成自己的歷史,又在自己創造歷史的活動中追求新的規定性,他不斷向著“應是”行進。因此,功利性僅僅是人的活動的一個方面,人的活動更重要、更根本的是人的超功利性質,這種超功利性質就是人的活動的審美性質。
人通過勞動實踐來滿足的需要,勞動實踐既有物質功利性的功用性質,又有超功利的審美性質。人的實踐活動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中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人的需要的現實滿足建基于人的社會關系,人的實踐活動的審美性質也表現為人的各種關系的審美建構。人的關系主要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三個方面,因此,需要的審美建構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超功利化。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從古至今,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在前現代社會中,人對自然主要是直接依賴的關系,自然直接的就是人的衣食父母,自然萬物被擬人化和精神化,人對自然充滿了畏懼感和崇拜感。自然對于人而言,不僅是生存的依靠,而且具有原始的、混沌未分的審美性。因此,前現代的人依靠自然并欣賞自然,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一種原始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相統一的關系。現代社會以來,人的理性的發現和運用使自然的神秘性逐漸消失,自然成為人依靠理性指導、通過實踐活動的征服而獲取物質財富的資源庫,人們盲目地向自然界索取,肆無忌憚地掠奪自然資源,自然的超功利性完全被功利性所遮蔽和吞噬。這種以功利性為主導的關系表現在發展觀上就是僅僅關注經濟增長,由于盲視而忽視了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人與自然關系嚴重地惡化。自然的祛魅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又導致自然審美性的消失。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目睹和經歷了人與自然的功利主導性關系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人們意識到保護自然的重要性,開始重視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但是這樣一種轉變仍沒有超越功利性主導關系的窠臼。人與自然關系的審美建構要求確立對自然的超功利性態度,把自然作為審美的對象來欣賞和建設,當代生態美學已經為此指示出一種方向。從人與社會的關系來看,現代社會建立在市場經濟社會的基礎上,商品是社會財富的存在形式,貨幣是社會財富的符號表現。商品的交換價值原則從經濟領域向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擴張和滲透,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完全被商品化和市場化。人與社會的關系完全在商品交換原則的操控之下,物質利益成為支配人與人社會關系之首要的和決定性因素,人與社會關系變成純粹的功利性關系。社會是人的生活形式,它不僅要滿足人的物質性需要,還要滿足人的精神性需要,包括人的審美需要。從人與自身的關系來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功利化使人與自身的關系也功利化了。以實踐為生存方式的人類不僅要通過實踐來滿足自己的生命存在需要,還要在自己的活動中直觀自己生命的本質力量,享受生命存在的愉悅與自由,完整的生命自我原本是功利性與審美性的統一。但是在當代,物質財富成為人的自我肯定的唯一標尺,人把自身變成生產工具和手段,人只是工具的延長和擴展。由于貨幣是社會財富的符號,人的自我功利化直接表現為人把自己變成一個掙錢的機器。對于人而言,“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為了能夠購買需要幻象制造的生活“必須品”,人們放棄閑暇時間,將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在了工作上面以便掙錢。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如此的繁忙,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和朋友,沒有時間鍛煉,沒有時間睡覺。人的心靈完全被物化,人的物質自我與精神自我是處于分裂狀態的,人在直觀自己的生命本質力量時只有物質的滿足感,生命的審美性無法顯現出來。人要在直觀自己生命本質力量時產生愉悅感和自由感,只有在人與自我之間建立起非物質功利的審美關系才有可能。
改變現狀是極其困難的,但是如果人類執意要繼續當前的發展方式,只能走向不幸的未來。人是具體的、現實的人,每一個時代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中,脫離社會去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當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談和抽象的假想。人不是神,無論是人類整體、人類群體或人類個體都不可能達到無所不能,因此不存在全能的主體,主體作為現實的人,總是受著具體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但是,無論是忽略人在自己發展中的主動性,還是濫用人在自己發展中的主動性都是不明智的。共產主義同樣是和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人的需要仍然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但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于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及他們發生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人“支配”自己的社會關系,從而真正地支配自己的消費選擇,成為消費的主人,從而成為自己的需要的主人。唯有如此,人方能審美地建構人的需要,使人真正成為自己需要的真實主體。這是人走出當代發展困境的智慧選擇,也是推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主體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