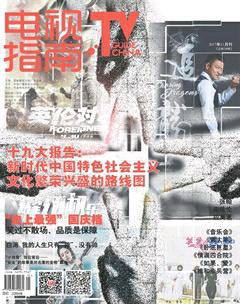《臥底巨星》 陳奕迅突破自我,黃金幕后強(qiáng)強(qiáng)聯(lián)合
《臥底巨星》講述了動(dòng)作巨星元豹(陳奕迅飾)走紅20余載卻從未得到過最佳男主角,因與泰國(guó)黑幫老大“八面佛”交好而被懷疑參與跨國(guó)販毒犯罪,鐵桿迷弟鐵柱(李榮浩飾)通過擅長(zhǎng)“潛規(guī)則”的副導(dǎo)(崔志佳飾)潛入元豹新電影的劇組,努力配合警方收集證據(jù)想為偶像洗脫嫌疑。在經(jīng)歷了戀上女一號(hào)童童(李一桐飾),得罪元豹經(jīng)紀(jì)人泰哥(陳國(guó)坤飾),晉升成為男二號(hào),目睹偶像用替身、耍大牌等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娛樂圈初體驗(yàn)”之后,鐵柱也終于離案件更近了一些……
在該片中,陳奕迅首次突破自我,飾演了一個(gè)“非主流”功夫巨星,每次出場(chǎng)都穿著“騷氣”的粉色服裝,本身搞怪的形象加上一貫夸張的造型,與元豹不謀而合。李榮浩則化身“迷弟”,調(diào)查案情到元豹身邊當(dāng)臥底。不僅與陳奕迅承包了所有的笑點(diǎn),更是首度出演感情戲,令人十分期待。陳奕迅坦言,李榮浩是他加盟該部電影的主要原因。“我一直覺得演戲不是那么自信,不像唱歌,就一直想著不耽誤人家。因?yàn)檫@個(gè)電影也是個(gè)大制作,但是當(dāng)知道對(duì)手是李榮浩,就想去試一試。”
戲里斗智斗嘴,戲外同是歌手出身的陳奕迅和李榮浩卻是惺惺相惜。陳奕迅還說起了自己和李榮浩的初始畫面。起初二人只是網(wǎng)友,后來有機(jī)會(huì)時(shí),陳奕迅竟然破天荒的給李榮浩發(fā)自己的房間號(hào)碼,邀請(qǐng)對(duì)方來聊天。這一行為被陳奕迅強(qiáng)調(diào)是生平第一次。看來二人真的是互相欣賞、很有緣分,導(dǎo)演也稱贊兩人的合作默契度超高。李榮浩說:“整個(gè)劇組拍攝的過程中都很歡樂,導(dǎo)致現(xiàn)在我看到導(dǎo)演和陳奕迅,都不由自主地想笑。”
而首度觸電大銀幕的新晉女神李一桐,則在片中飾演花瓶女一號(hào)。她也爆料了在片場(chǎng)三個(gè)人相處的趣事,吐槽陳奕迅飾演的元豹經(jīng)常給自己安排那種一進(jìn)去就被打死拖出去的戲份,而李榮浩飾演的鐵柱則會(huì)默默為自己做很多事,跟倆人拍戲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yàn)。李一桐表示:“雖然在戲里我演了一個(gè)不會(huì)演戲的女演員,但是我會(huì)努力把這個(gè)角色演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片的幕后團(tuán)隊(duì),導(dǎo)演谷德昭曾執(zhí)導(dǎo)過《大內(nèi)密探零零發(fā)》《家有喜事2009》等深受觀眾喜愛的作品,此次《臥底巨星》不僅延續(xù)了經(jīng)典喜劇的水準(zhǔn),還會(huì)加入爆破戲、高空激斗戲等動(dòng)作元素,可以說是一部更貼近年輕觀眾的喜劇動(dòng)作大片。
導(dǎo)演表示,自己一直以來都非常想拍一部喜劇動(dòng)作片,但是喜劇很難,加上動(dòng)作就更難,但這一次《臥底巨星》做到了。喜劇方面,電影不僅啟用了周星馳御用配角班底,還邀請(qǐng)了參演過《愛笑會(huì)議室》《煎餅俠》等多部作品的內(nèi)地喜劇才子崔志佳加盟,也為電影注入了北方喜劇元素。動(dòng)作部分有香港著名動(dòng)作演員陳國(guó)坤,與《殺破狼》系列電影中有出色表現(xiàn)的Chris Collins強(qiáng)勢(shì)加盟,同時(shí)針對(duì)武術(shù)功底較弱的陳奕迅,電影邀請(qǐng)動(dòng)作導(dǎo)演洪金寶次子洪天祥手把手進(jìn)行武術(shù)指導(dǎo),嚴(yán)格保證動(dòng)作戲的真實(shí)效果。加上曾為多部經(jīng)典動(dòng)作電影保駕護(hù)航的黃柏高為本片擔(dān)任監(jiān)制,無疑為這部動(dòng)作電影,注入了一針強(qiáng)心劑。
對(duì)話 主創(chuàng)
打得好看真不容易
Q:陳奕迅,這次你跟李榮浩合作,是你打他比較多,還是他打你比較多?
陳奕迅:這次對(duì)打比較多,之前可能都是被打的。之前像《愛作戰(zhàn)》等很多電影里都有動(dòng)作的部分,也有學(xué)到一些該怎么反應(yīng),給我一些經(jīng)驗(yàn)。因?yàn)閷?duì)打其實(shí)真的很講節(jié)奏。萬一一個(gè)比較快、一個(gè)比較慢,就不好看了。打得好看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說你平常有一些肢體語(yǔ)言,可能看起來很有自己的風(fēng)格,但在電影里可能就不是非常好看。打的時(shí)候整個(gè)人肢體要看起來比較有氣勢(shì)。另外用鏡頭來拍動(dòng)作,要拍得好看,真的要看導(dǎo)演跟動(dòng)作導(dǎo)演的品位,和對(duì)我的一些指導(dǎo)、調(diào)整。所以我很感謝他們。
Q:第一次挑戰(zhàn)動(dòng)作戲,你覺得過癮嗎?
陳奕迅:非常過癮。作為一個(gè)歌手在演唱會(huì)上表演,很多人不會(huì)對(duì)我有太嚴(yán)苛的要求,覺得我已經(jīng)很有經(jīng)驗(yàn)了,可能大家就算有意見也不會(huì)特別去跟我說。但是拍一個(gè)電影是靠團(tuán)隊(duì)的力量,大家不會(huì)把你當(dāng)成地位很高的一個(gè)歌手,很多東西你做得不夠好的,大家都會(huì)指出來。我很感恩有這個(gè)機(jī)會(huì)在電影上面從零開始。
Q:李榮浩,你從歌手轉(zhuǎn)型到當(dāng)演員,有沒有一些不太適應(yīng)?
李榮浩:《臥底巨星》算是我第一次花比較長(zhǎng)時(shí)間去拍電影。我去年拍過一部別的電影,那個(gè)時(shí)間稍微短一點(diǎn),這次比較長(zhǎng)。首先我會(huì)和Eason(陳奕迅)在一起,更多地先觀察,觀察大家都是怎么演繹的,然后私下里會(huì)討論,這里需要大聲一點(diǎn)或者什么,經(jīng)常有這種小的細(xì)節(jié)要注意。Eason跟我說了很多讓我覺得想不到的東西。比如說一開始以為打拳嗎,打就好了,其實(shí)不是,如果拳伸出去不直,鏡頭里就不好看,武打是要看整體的狀態(tài)的。
Q:李一桐,大家都知道你有舞蹈功底,打戲部分會(huì)有幫助嗎?
李一桐:舞蹈是一個(gè)線條性的東西,而武打是點(diǎn)和力量的東西多,我可能在做動(dòng)作的順序上會(huì)記得快一些,但是在力道上會(huì)欠缺一些,這個(gè)電影拍完之后,我在力量上加強(qiáng)了很多。而且我覺得配合非常重要。有一場(chǎng)戲我穿著巨高的高跟鞋,跟坤哥(陳國(guó)坤)對(duì)打,因?yàn)槲渲冈O(shè)計(jì)的動(dòng)作需要我們配合精確到0.01秒鐘,我劈下去,他閃開,才好看,不能做假或者借位,那樣的話拍出來不好看。我們當(dāng)時(shí)就沒有配合好,我腿劈下來的同時(shí),剛好就打到他的頭了。
Q:第一次拍喜劇電影,又搭檔了兩位巨星,分享一下感受。
李一桐:其實(shí)我們沒有刻意搞笑,或者故意做一些表情,就是跟著劇情去體現(xiàn)自己的角色,然后因?yàn)楣适聨?dòng)著我們的情感,也帶出來一些搞笑的元素給大家,不是沒有趣,一定要胳肢人去笑那種。 (編輯:彼黍離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