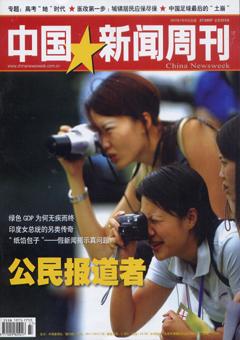“公民報道者”的尷尬
何忠洲
這些草莽英雄們在改變中國媒體生態的同時,也面臨著由外界和自身原因造成的尷尬
在湖南省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案爆發后媒體追根溯源的報道中,李新德不見蹤影。《南方周末》的相關報道中提到了新華社內參,但是李新德及其網站卻不在其列。原因在于:由李新德打理的網站并不被視為是一個正規媒體。
媒體沖擊波
盡管言不正名不順,“公民報道者”們依然在新聞競爭日趨激烈的互聯網時代,奮力演繹出了媒體草莽英雄的本色。
李新德說:我們這些以報道為業的人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群體,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這一群體開始在中國的社會舞臺上,在網絡的無窮空間里,在對社會產生相當影響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中國的媒體生態。
當初,郴州的黃元勛為了舉報曾錦春曾經踏遍媒體和信訪機構,最后不得不以向省委書記寫遺書的方式來以示抗爭。
而山東的李玉春為了舉報李信,懷揣著李信下跪的照片和相關材料走遍媒體,仍然沒人理睬。這種情況在中國并不罕見。
這種局面,在“公民報道者”那里得到突破。2004年,當《下跪的副市長——山東省濟寧市副市長李信丑行錄》公布后,網站的點擊率總量達到了170多萬人次,訪問者遍布60多個國家和地區。
這樣的點擊量雖無法和兩年后在博客上以一己紅顏與瑣事成名的老徐博客相媲美,但對于一個傳統媒體的傳播來說,已經相當可觀。
對新聞的狂熱,以及來自理想和本身性格的執拗,使他們對自己所報道過的事情時刻關注。與一般的媒體人相比,他們本身的著眼點并不僅在于信息的傳播,而更在乎事情報道后的結果。就單是李寶金案,李新德就連著發布了許多文章。
甚至有些“公民報道者”,直接參與了地方官場的反腐斗爭。李根,原本在當地媒體工作,在郴州官場地震爆發的前夜,屢屢配合有關部門調查。一位身在郴州官場的官員告訴本刊記者:李根對郴州的熟悉程度遠遠勝過我們這些當局者。在傳統媒體跟進報道之前,李根就在不遺余力地將郴州官場的是是非非抖摟出來。他因“湖南最牛線人”之名成了郴州家喻戶曉的人物。5月,本刊記者在郴州采訪時,親耳聽到諸多市民們對他的贊揚之聲。
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公民報道者”們開始改變“輿論監督只是新聞媒體的監督”的局面,而逐漸形成“人民群眾通過新聞媒體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的監督”。
德拉吉的中國式尷尬
與美國的德拉吉相比,中國的“公民報道者”更具“中國特色”。
首先是所處的環境。中國社科院的一位資深傳媒專家告訴記者,雙方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不一樣,這決定了雙方的社會功用與地位的不同。這也是德拉吉和中國的“公民報道者”們被社會所接受程度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展江教授告訴記者,實際上,李新德等人是深受新聞專業主義的影響的,這使得他們在報道時并不完全像德拉吉,而是更重視證據的收集與取證。當有人指責德拉吉報道所依據的都是些小道消息和謠言的時候,德拉吉回應說,“今天德拉吉報道上的謠言就是明天《紐約時報》上的新聞。”
而李新德告訴本刊記者,“我先后發布有近十起涉及廳局級官員的曝光文章,最后都被證明是真實準確的。”
但是,對證據的更加重視,也并不能使得他們本身如德拉吉般的成為大眾傳媒的寵兒。盡管李新德的網站點擊量也達到上百萬,但是,在正規的媒體人推薦里,沒有人會想到要為其留一席之地。這一點,就是在其得到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媒體的報道之后,也沒有絲毫的改變。諸如“土記者”“草根記者”的稱呼更像是一種禮貌的敬語。甚至連他們本身,也沒有將自身定位在媒體人的行列。中國維權服務網站長李鳴如此告訴記者:“我覺得自己更多的只是一個維權者,而至于媒體人,我沒有記者證,也沒有那么專業的新聞訓練,也沒有新聞單位要我。”
付費新聞的拷問
從一開始,對于民間報道的真實性與可信性就是爭議的焦點。在面對“不對消息來源進行核實,為了贏得轟動效應而不計后果,草率行事”的指責時,德拉吉曾經毫不客氣地說:“美國主流媒體所出現的長長的重大差錯清單是一個生動的說明:大型新聞機構并不擁有可信性、真實性、準確性或其他美德的專利。”
但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崔保國的擔心是:在傳統媒體,新聞的發布往往會經過審讀、復核這樣一個過程,雖然仍然無法避免錯誤的發生,但畢竟有一個減少錯誤的機制,而且作為一個媒體單位,本身可以很容易受到問責的制約。
事實上,所謂“公民報道者”目前的確處在一個灰色地帶。傳統媒體在更多的時候,與他們若即若離。在主流媒體的從業人員眼中,他們更接近“線人”的角色,只是現在這些“線人”已經不是單純的“報料”,他們甚至還有自己的發布渠道——網絡。
在德拉吉借助于“德拉吉報道”的超強人氣,開始接受廣告、每天能夠有大量進賬的時候,中國的“公民報道者”卻普遍的處于經濟窘迫的境地。
李新德在若干年里都靠著以前的一點積蓄過活。而李根,則只能靠寫點文章拍些照片糊口,每年的收入只有一萬多。
這種窘迫對于完全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多重的煎熬。開支是必要的,收入卻是不固定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適當收費成了惟一的選擇。
2006年6月,一位“公民報道者”公開聲稱將專職民間維權并收取合理費用。
這一聲稱道出了很多“公民報道者”的心聲。
但這也使得人們有著更多的懷疑:他們到底是要做新聞報道?還是要借機搞錢?因為此前在北京那些上訪群體中,出現了很多打著網站旗號,聲稱可以幫忙解決問題的“媒體人”,前提是對方能夠付得起足夠的費用。
發生在去年的一起網絡詐騙案讓人們記憶猶新。完美(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狀告以中國投訴網記者的身份向其敲詐勒索380萬元的李凌。2006年11月,經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李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經過許多年的摸爬滾打之后,李新德毫不諱言經濟問題:我們在他們走投無路時替他們呼吁,很多時候就是幫他們討回本應該屬于他們的經濟利益,所以他們為此支出相應的路費和誤工費是應該的。“這一個問題應該公開,而不應該總是遮遮掩掩的。”
不過他強調:只要是有價值的新聞,舉報者沒有錢,他和他的朋友們也一樣全力支持。
這的確是中國新聞界目前面臨的新問題。傳統的新聞觀念,已在受到挑戰。“公民報道者”們更像一把雙刃劍,他們試圖在客觀、真實的鋼絲上行走,但他們缺乏應有的制約,因此也就具有相當的危險性——不論是對他人,還是對他們自己。
不過,在對這一新生事物還沒有制度安排的時候,他們更多地是在接受生存的考驗。而他們的存在,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應該面對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