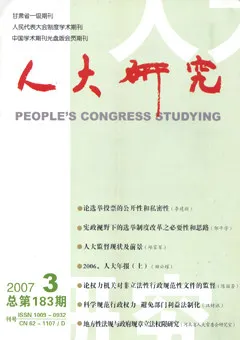轉型期公民政治參與的特點
“政治參與是普通公民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加政治生活,并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和政策過程的行為。”[1]公民的政治參與活動是現代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開展,我國正經歷著由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轉型,由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倫理社會向法理、法治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我國社會發生的這些重要的結構性變革,促使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公民主體利益意識迅速覺醒,政治參與能力不斷提高,新利益群體相繼產生,利益分配的調整,國家政治民主化程度逐步提高,公民政治參與方式不斷更新,這些因素為公民參與政治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推動了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發展。
社會轉型不僅促進了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發展,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政治參與的形式與內涵,使之表現出一些新特點:
第一,參與熱情與冷漠并存。社會轉型時期,由于公民意識的覺醒、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等原因,推動了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水平,使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逐步提高。他們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有序地主動地參與政治,表達意愿,促進了公民與政府的溝通,促進了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但與政治參與的熱情相反,我國還存在著大量的政治冷漠現象。即使是在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中,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投票這一基本形式來講,其中有的是出于信任和自愿,有的只是隨大流,走形式,后者所占比例有擴大趨勢。選舉人大代表,通過人大代表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這本是我國人民實現民主的基本途徑,然而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人認為如何選出代表或選誰做代表與自己沒有多大關系,很多人采取消極的參與態度,甚至是不參與。
第二,正式組織與自治組織參與并存。我國政治參與的正式組織載體主要有:各級黨組織、各級人大、各級政協、工會、共青團、婦聯、職代會等,公民通過參加這些政治組織及其活動,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與此同時,隨著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形成了大量政治參與的自治組織載體,如各種形式的行業性、商業性聯合會和權益性協會、群眾自治組織等,公民依托這些自治組織參與政治,開辟了政治參與的新渠道,推動了政治參與的發展。
第三,制度化參與與非制度化參與并存。制度化參與是指公民的政治參與和國家對政治參與的管理都依據法治原則,以法律規定和確認的方式和程序進行的參與方式。它能保證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法律化、經常化、秩序化,這是現階段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與此相反,社會轉型時期,由于民主政治體制尤其是政治參與機制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以及有些公民具有較強的社會挫折感,因此,在政治參與實際當中,也存在一些非制度化的參與方式,如”抵制性參與、過激參與、過分擴展的參與乃至暴力參與”[2]等,影響了我國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
第四,政治性參與取向與利益性參與取向并存。現階段,由于我國政治參與主體的復雜性,使得不同層次的公民有著不同的參與動機與要求。大部分公民的政治參與動機是具有政治取向的,他們出于對國家和民族命運和前途的關注,出于對政治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關心,以期通過政治參與來反對官僚主義、腐敗和社會不公現象,以實現社會的公正和正義,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這也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主流方向。但與之相對立,在社會轉型時期,也有一部分人的政治參與動機是利益取向的,他們參與政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或影響政府活動,以獲取更多的自身利益,如農村基層出現的“富者為官”現象等,使政治參與走向了狹隘的方向,這是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的現象。
第五,參政意識較強與參政能力較低并存。改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