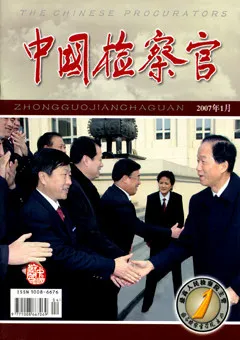從定罪與司法邏輯、共同關系與共同犯罪解析犯罪的認定
內容摘要:在司法實踐中個案的爭議往往隱寓著對法律問題的不同理解,通過對不同觀點的梳理和討論,能夠將理論研究引向深入,形成合情合理的法律解釋,指導司法實踐。尤其是辦案實務中的案例,不僅包括相近罪名間的混同,也包括相互不可及罪名的加入,趣味并復雜。
關鍵詞:敲詐勒索 尋釁滋事 打擊報復證人 犯罪構成 共同犯罪
[案情] 2002年12月,通州某小區兩戶居民住宅被竊,丟失照相機、筆記本電腦、玉佩等物,該小區保安經理滕××為協助公安機關破案,積極查尋線索,買回了筆記本電腦等部分贓物,并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了作案人員馮××。后因證據不足,未全部認定上述兩案均為馮××所為。2003年6月,法院以盜竊罪和銷贓罪判處馮××有期徒刑二年。2004年年底,馮××在獄中給滕寫來一封信,暗示將對滕不利(馮、滕二人案前即已相識)。
2005年1月,馮××刑滿釋放。2005年1月25日,馮××約集陳××、田××(在逃)、大剛(在逃),滕××也約來與馮同村居住的劉××,到聚友軒飯店“說事”。對于“說事”的內容,雙方供證差異較大。
馮××供稱,滕××說:“你剛回來,我肯定幫助你,我會給你補償補償”,并定好次日細談。
滕××證稱,馮××說:“我剛出來,衣服和鞋都是新買的,花了一萬元,這些錢都是借的,你拿錢我得還人家,現在我每天吸粉也需要一千元”,“你先給我拿五萬元,我先花著”,(滕××說:“現在沒錢,等過段時間你再找我”),“武××我得找人干了他,因為是他找人點的我,讓我進去的,我今天沒有找著他,找著了就干了他”。
陳××最初供稱,馮××說:“我剛出來,身上穿的衣服花了一萬多元買的,我剛出來沒錢,你得幫我。”滕××說:“你要不抽大煙我可以幫你”。后推翻原供,稱“我只聽見馮××讓滕××幫他,我沒聽見馮××跟滕××要錢。具體怎么幫,他們沒說,我就不知道了”。
劉××最初證稱,馮××說:“我這身西服和鞋都是新買的,花了一萬多”,“我因為給你點了,進去兩年多,在里面受了挺多的苦,你得補償”,“你就先拿五萬元我花著,完了之后再說”。并證稱馮、滕二人約定次日單獨談。后推翻原證,稱“當時我沒有聽見馮××向滕××要錢。馮××只是問滕××怎么辦,滕××說第二天上午我們單獨聊,馮××就答應了。以后我沒聽見他們說這事。”特別是否認曾說過馮××向滕××要五萬元的話。并稱其妻能予證實,其妻確予證實,并證稱劉當時還對記錄提出了異議。有關民警也對其妻在詢問劉時亦在場的情況予以證實。
雙方分手后,滕××、劉××到京東垂釣園歌廳,滕電話約來武××,后武××又叫來山東老二(在逃)等人,與馮××等人再次會面。其間,雙方發生沖突, 武××與“山東老二”等人離去,馮××亦離去。陳××、田××、大剛借口“滕××生事”對滕進行毆打,致滕輕傷。
武××證稱,在歌廳,滕××說:“馮××找了三個社會上的人,跟我要補償費”其問“要多少錢”,滕××說:“那還少的了,明天再說,馮××還找你呢”,其問“找我干什么”,滕××說:“還能干什么,要錢唄”。
本案是由證據的認定繼而引發定性和處理的分歧。公安機關以馮××構成敲詐勒索罪(敲詐數額五萬元)、陳××構成尋釁滋事罪移送審查起訴。經審查,本案證據的焦點在于馮××是否提出了明確的敲詐勒索數額。審查認為,在案證據不能支持馮××敲詐勒索五萬元的認定。基于此,對于定性及處理形成了以下幾種意見:
1.馮××從獄中寫給滕××的信及馮、滕相見時的語言,反映出其威脅系隱性存在,程度不強,且無證據顯示馮索要錢財的數額,敲詐勒索罪難以成立,現有事實證據不符合起訴條件,對馮應作存疑不起訴。陳××構成尋釁滋事罪定罪起訴。
2.馮××的信件、語言表示及其行為,基于人們的一般理解,可以判定馮××的敲詐勒索行為,雖然五萬元的數額難以認定,但幾項言詞證據均可以支持對其敲詐數額以下限一萬元的認定,故對馮可以敲詐勒索罪(未遂)起訴,對陳以尋釁滋事罪起訴。
3.雖然幾項言詞證據均提到了一萬元的數額,但從馮的語言環境判斷,所謂一萬元只是向滕實施勒索的一個示例、借口,表明其敲詐勒索的意向,而非具體的犯罪數額,故應認定馮××的行為為敲詐勒索罪(預備)起訴,認定陳××的行為為尋釁滋事罪起訴。
4.以敲詐勒索對馮××定罪處理,在證據和犯罪構成上都存在一定的瑕疵。但馮××的行為包含于打擊報復證人罪的內容之內,故可以該罪對其進行處罰。同時,陳××也應以此定罪處罰。因為兩起事實是有機的整體,馮××基于報復的動機糾集陳××等人共同實施的行為以及陳××等人單獨實施的行為,馮××、陳××等人應共同承擔刑事責任。若對陳××另定尋釁滋事罪,則割裂了兩起事實之間的聯系,也降低了馮××行為的危害程度,同時,難以解釋馮××對于陳××等人毆打滕××的行為未指使、未參與的情況。
5.認同把前后兩起事實作為一個整體,但認為應以涵蓋于打擊報復的動機之下的特征比較明顯的尋釁滋事罪定性處理。
就上述意見,無論支持哪一種意見,都可以有充足的文字為文,但是,筆者認為,對本案的爭議,足以引起我們對立法司法中一些基礎問題的深入探討,盡可能地統一認識,減少類似爭議,這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定罪與司法邏輯
面對刑事案件,正常的司法邏輯一般是,通過犯罪概念對罪與非罪作出抽象的判斷,再通過犯罪構成把犯罪的概念具體化,以確定犯罪的成立。抽象判斷與具體化二者有交叉和重合。這一過程中,抽象的判斷一般是隱形的,多數情況下也是可以省略的。對于一個經過專業訓練的司法人員,根據其司法的先驗便可以作出判斷,這種先驗包括法律規范、法學理論的掌握和司法經驗的積累。
當對犯罪的抽象判斷被忽略時,就造成了邏輯偏差,即直接以犯罪構成的條件框套案件事實以決定罪與刑,狹隘地關注先驗的某個罪名(一般是司法人員知識體系中最熟悉的罪名)的犯罪構成所需的條件是否滿足,而忽略該構成之外的其他情況的綜合把握(包括一些不常用的罪刑設定),難免造成司法判斷的錯誤。
通過犯罪概念和犯罪構成的交互作用,判斷該案罪在哪里,犯在何條,不會直截了當地切入某個條款加以論證,而可能會在幾個條款中選擇最適用的條款。所以那種直接引證某罪的觀點實際上是忽略了對犯罪的抽象判斷。
根據我國《刑法》關于犯罪概念的設定,犯罪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其中,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
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突出表現在對《刑法》法益的侵害,本案中,馮、陳的行為侵害了多個方面的法益,包括公民的財產、健康、社會秩序、司法活動,因此,應當在較大的范圍內根據具體的犯罪構成確定犯罪的成立。也就是說,要用事實去對應犯罪構成,而不是用犯罪構成去取裁事實。我們說某人犯某罪,并不代表其行為只侵害一種法益,究竟以何罪對其科處,還是要看其行為符合哪種罪的犯罪構成,也就是要對犯罪的刑事違法性進行衡量。
在犯罪構成的考量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問題影響著對一個案件的規范評價,也就是說,案件有時不以犯罪構成的規范形態呈現,當我們以最適合犯罪顯性樣態的犯罪構成去評價時,卻往往發現它在一些要件上存在缺失。這樣的情況既有立法缺陷的問題,也有應用的問題。從現行法律效力的角度,不符合犯罪構成要求的,當然就不能成立該罪,也就當然地需要考慮其他的犯罪構成評價,而不是簡單地作非罪處理。我們不能以最適合犯罪顯性樣態的犯罪構成去評價時,可以以符合條件的犯罪構成去評價,確立該犯罪構成所成立之犯罪應施予的刑罰處罰。
對以上所述總結說明如下:
1.犯罪概念的抽象判斷與犯罪構成的具體判斷在司法中不可或缺;
2.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可以作出多重判斷,決定了刑事違法性的判斷也具有多樣性;
3.確立案件性質的是最符合刑法設定的構成條件的犯罪,而不是最適合犯罪顯性樣態的犯罪。
還需要說明的是,犯罪人的犯罪故意與刑法評價的關系。筆者認為,犯罪故意不是指犯罪人主觀上犯某罪的故意,而是實施某種行為的故意,而確立該故意為犯某罪的故意,是司法機關給予的評價,這種評價從屬于對最符合刑法設定條件的犯罪構成的判斷。
還需要引申的是,《刑法》條文設定中的保護關系。我國以四要件構成為標準的犯罪構成模式,是一種平面整合式的一次性判斷,不可能涵蓋犯罪的各種復雜情態。但是,從立法技術的角度,我們會發現,有些犯罪的設定其包容量是相當大的,這種寬松式的構成(如打擊報復證人罪等)與要求嚴格的緊縮式的構成(如敲詐勒索罪等)形成了一種保護關系,當不符合后者的條件時,應考慮前者的應用。
還需要提示的是,罪刑法定不僅是出罪所擎的大旗,也是入罪的綱鼎。我們不能以罪刑法定遮掩司法的無能,放縱犯罪將貽害無窮。司法人員應該合理運用法律技術最大限度地制裁犯罪,善于在法律的適用中發現和延伸法律的活力。
根據本案的顯性特征,可以先驗地判斷以敲詐勒索罪的構成加以評價,但很明顯,在犯罪構成上存在缺失,這種缺失決定了圍繞敲詐勒索罪的努力的“完形”處理都是值得攻訐的。但當我們以打擊報復證人罪加以評價時,卻會發現本案未出離于該罪的構成,可以適用該罪對馮××定罪科刑。
二、犯罪的共同關系與共同犯罪的認定
認定犯罪,要綜合全案事實,通過對全案事實的分析從中取裁犯罪構成所需的事實,而不是以某一犯罪構成人為地割裂事實。任何犯罪,都不是一蹴而就,在行為上都會有一個持續的過程,從行為的發生、發展、惡化到有結果的產生,也許某犯罪構成只關注惡化或結果產生那一段的行為,但并非其他行為就是無意義的,也就是說在判斷犯罪之成立時是不能被拋開的。特別是在有數人參與的案件中,首先要確立數人的行為是否具有共同關系,以判斷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各參與人有的可能參與全部行為,有的可能只參與部分行為,如果缺乏對全案事實的綜合考量,往往會割裂事實,造成認識上的障礙和結論上的錯誤。前述案件分歧意見中,就有這樣的情況。
共同犯罪意味著共犯人之間的行為相互利用相互補充而成為一體,每個人的行為都和結果之間有物理或心理的因果關系。從本案的全部過程來看,馮××因與滕××結怨,蓄意報復,并召集陳××、田××(在逃)、大剛(在逃)幫助其實施,報復的直接目的是向滕××要錢,最初是由馮××與滕××具體交涉,陳××等三人站腳助威,案件在報復的前提下呈現出敲詐勒索的面貌,但由于數額要件的缺失,以敲詐勒索罪定罪顯然難以成立,因而案件繼續沿著報復的走向發展。此時,馮××、陳××等人的行為與行為結果不僅有物理上的因果關系,也有心理上的因果關系。其后,滕××電話叫來武××,試圖把武拉入自己一方,以對抗馮××,因“山東老二”等人的介入,馮××暫時中斷了其個人行為。但是,馮××前期的行為與此后案件結果的心理關系并沒有中斷。陳××等人的行為自開始就是在幫助馮××實現其犯罪目標,因為滕××叫來武××并引起“山東老二”一派勢力的介入,才形成了對滕××的不滿,繼而有毆打滕××并致輕傷的行為,是幫助馮××實施報復行為的繼續,也可以說,后期陳××等人的行為仍然與馮××有著共同的報復目的。馮××雖然中斷了個人行為,卻對陳××等人的行為聽之任之,并沒有截斷心理上的因果關系,所以,本案應成立共同犯罪。
三、共同犯罪的罪名確定和罪質的補充關系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論的重要問題,也是司法實踐中的常見問題。在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中,對于共同犯罪有兩種對立的解釋: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犯罪共同說認為,共同犯罪是指數人共同實行一個特定的犯罪,認定共同犯罪是否成立,以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為標準,簡單地說,共同犯罪是共犯人共同犯某一罪。行為共同說認為,共同犯罪是數人由共同的行為完成各自意圖的犯罪,也就是說,數人的共同行為可以跨越數個犯罪而實施,認定共同犯罪是否成立,以共同的犯罪事實為標準,共犯人可以構成不同的犯罪。行為共同說對于共同犯罪的解釋更加突出了共同犯罪與單個人犯罪相較的特異性,使共同犯罪處罰原則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原生于犯罪共同說和行為共同說又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和觀點。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并沒有兩大學說的明顯分野,但對于共同犯罪的不同主張,仍未脫離于上述爭議,只不過表述方式不同而已。按照犯罪共同說,共犯人同犯一罪,罪名只能定一個,按照行為共同說,罪名可以不同一,然而行為共同說并不適合我國的犯罪成立模式。我國理論界還提出了部分犯罪共同說,“只要二人以上就部分犯罪具有共同的行為與共同的故意,便成立共同犯罪;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又存在分別定罪的可能性。”然而筆者認為本案還沒有涉及到這個復雜的問題。
如前文所述,馮××與陳××等人在行為初期即達成了報復滕××的共意,此后陳××等人毆打滕××并致其輕傷的行為仍是報復行為的繼續,所造成的傷害后果也并未超出打擊報復證人罪的客觀評價范圍,從量刑上看,故意傷害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打擊報復證人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者也大體相當,所以,不必要進行傷害罪的獨立評價,二人的行為均認定為打擊報復證人罪。假如陳××等人毆打滕××致重傷,該結果已超出打擊報復證人罪所能涵蓋的范圍,那么筆者就會贊同部分共同犯罪說,認定二人在打擊報復證人的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對陳××以故意重傷罪定罪處罰,對馮××以打擊報復證人罪(情節嚴重款)定罪處罰。
該案的分歧中,主張對陳××單獨定尋釁滋事罪而馮××不定罪的觀點是以否定共同犯罪成立為前提的,因筆者已論述過共同犯罪的成立,在此不再贅論。主張對全案以尋釁滋事定罪的觀點,無法解釋馮××的共同行為,難以立論。
此案法院以馮××犯打擊報復證人罪、陳××犯尋釁滋事罪定罪科刑,又形成了一種新的分歧意見,且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性意見,筆者持異議。
對馮××定罪是以確立共同犯罪為前提的,而且本案的全部事實也支持對馮、陳二人行為的共同評價。法官作出如此判決只能是基于對二人行為的分別評價,那么對馮只能評價毆打滕以前的敲詐勒索行為,在法定刑相當的情況下敲詐勒索未成立犯罪而打擊報復證人成立了犯罪,則是說不通的。認定馮××的行為構成犯罪,必須加上后面的毆打致傷情節,但單獨評價馮××的行為時是難以把其沒有參與的行為評價進去的。以尋釁滋事罪評價陳××的行為,如果拋開了前期的行為背景,很難解釋毆打他人的“隨意性”,而當考量毆打他人的行為背景時,又難以作出該毆打行為就是“隨意”的判斷,所以,得出尋釁滋事罪的結論是武斷的。
另外,尋釁滋事罪在刑法罪名體系中的定位相對于有關犯罪而言是一個堵截性或稱兜底性的條款,是將客體區分上不便納入其它類罪的,以及未達其他類罪的犯罪標準,而又需要進行刑罰處罰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聚合設定的,當行為符合某一具體的犯罪構成時,一般以該具體犯罪論處,除非該具體犯罪之處罰與其危害性有不相協之處,可以利用想像競合的原理認定尋釁滋事罪以維護罰當其罪的原則。當然這是本文探討之外的問題。
責任編輯:苗紅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