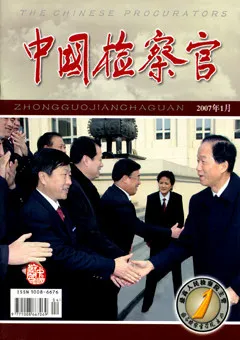轉化型搶劫罪共犯及既未遂的認定
內容摘要:轉化型搶劫罪屬于真正身份犯,其共犯問題,應堅持法益概念和共犯從屬性觀點,視不同情形進行處理;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未遂,應以實施暴力、脅迫之后是否取得財物為判斷標準。
關鍵詞:轉化型搶劫罪 身份犯 共犯 既遂
根據我國《刑法》269條的規定及轉化犯的有關理論,轉化型搶劫罪是指行為人在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之后,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轉化型搶劫罪為身份犯,屬于真正身份犯。這是因為,行為人在轉化前的盜竊者(詐騙者、搶奪者)身份是事后搶劫罪的基礎,如果之前不具有盜竊者身份,則事后所謂的轉化型搶劫罪便無從談起。
一、轉化型搶劫罪的共犯問題
共犯論被部分日本刑法學者稱為絕望之章,而共犯與身份的交織,使問題更加艱深難解。本文對待該問題的立場是堅持法益概念和共犯從屬性觀點,因為唯有如此,共犯與身份的諸多問題方得以妥當解決。例如,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實施真正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性質應由實行犯的實行行為決定。無身份者教唆或幫助有身份者實施真正身份犯,有身份者成立實行犯,無身份者成立教唆犯、幫助犯。無身份者能否成為真正身份犯中的共同正犯,關鍵在于無身份者在真正身份犯中能否形成功能性支配。有身份者教唆或幫助無身份者實施真正身份犯,有身份者成立間接正犯,無身份者成立幫助犯。對于轉化型搶劫罪的共犯問題,本文亦堅持上述觀點,然而對具體情形仍需仔細討論。
第一種情形,無身份者有故意、有行為。甲盜竊后在反抗或逃跑過程中,遇到乙并告知因盜竊而案發,要求乙幫其排除抓捕和追奪,乙便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對此,不管甲是否與乙共同實行暴力、脅迫行為,乙與甲均構成搶劫罪的共同犯罪。
第二種情形,無身份者無故意。如在上例中,甲遇到乙喊道:有人追殺我,幫我一下。乙對甲的盜竊者身份并不知情,但出于朋友義氣,對失主丙實施了暴力。該情形類似于間接正犯中這種情形,即被利用者對利用者意圖實現的犯罪沒有故意,但對其他犯罪具有故意。例如,某甲意圖殺死在屏風后面的乙,命令不知事實真相的丙向屏風射擊。丙具有毀壞財物的故意,但沒有殺人的故意,對于殺人行為而言,丙僅是工具而已。甲構成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1]因此,甲構成了間接正犯,應成立搶劫罪;乙在不明知甲的身份前提下,不具有事后搶劫罪的特定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不能與甲成立共犯,但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
第三種情形,無身份者主動承接。例如,甲在被追捕過程中,乙見狀主動上前接過甲手中的贓物逃跑。如果之后甲與乙共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兩人成立搶劫罪共犯自無疑問。即使只有乙一人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而甲在現場不加制止,這實際上是一種默許,不能排除其主觀故意,甲與乙仍然構成搶劫罪共犯。但是,如果在上述情形中,甲與乙各朝不同的路徑逃跑,乙獨自在“當場”的時空范圍內基于護贓的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此時,對甲乙應如何處理?對于甲,由于其沒有教唆乙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對此也不知情,所以對乙的行為不需承擔責任,而只定盜竊罪。對于乙,由于其主動承接了甲的身份,并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所以構成搶劫罪。
第四種情形,有身份者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無身份者暗中相助。例如,甲盜竊后逃竄,并對追趕者丙實施暴力,乙出于幫助甲的故意,對丙也實施暴力,對此甲全然不知。在此,甲構成轉化型的搶劫罪。而乙構成片面的幫助犯,這是因為,幫助的意思并不要求意思的聯絡,在正犯不知情的場合,幫助行為仍然可以使實行行為更為容易,只要行為人以幫助的意思,實施幫助行為,促進了法益侵害,就應當認定為幫助犯。[2]因此,乙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幫助犯。
第五種情形,有身份者未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無身份者暗中相助。例如,甲盜竊后逃竄,乙出于幫助甲的故意,對丙實施暴力脅迫,對此甲全然不知。在此,對于甲,由于其沒有教唆乙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對此也不知情,所以對乙的行為不需承擔責任,而只定盜竊罪。對于乙,由于甲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所以乙也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幫助犯。對乙如何處理,應視具體情況而定。如果乙實施暴力行為的場所仍屬于甲盜竊行為的延伸“現場”,那么由于甲的盜竊行為仍未實施終了,則乙構成甲盜竊罪的片面幫助犯;如果乙實施暴力行為的場所已不屬于甲盜竊行為的延伸“現場”,那么由于甲的盜竊行為已實施終結,所以乙的暴力行為只構成故意傷害罪。
二、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問題
關于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未遂問題,理論界爭議很大,主要存在以下觀點:
其一,轉化型搶劫罪只有在盜竊既遂的場合才能成立,其既遂、未遂的標準,應該根據盜竊者采用暴力、脅迫手段是否達到防止所竊財物被他人奪回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