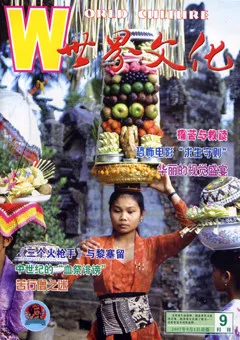至純至美的牛津與劍橋
出倫敦,往西北行數(shù)十公里可達(dá)牛津,向東北去幾乎同樣的距離則是劍橋,這兩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成犄角之勢,已對峙了數(shù)個世紀(jì);這兩顆英格蘭教育皇冠上璀璨的寶石,交相輝映,始終是世界各地學(xué)人心中不滅的燈塔。
牛津位于泰晤士河的一個拐彎處,地勢較低,且有丘陵遮蔽,樹木掩映。若乘車進(jìn)牛津,翻過幾道山坡,經(jīng)過幾條窄街,你會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早已置身城中,鱗次櫛比的古建筑令人目不暇接,新鮮的驚喜一個接一個。去劍橋則不同。越過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高坡,眼前豁然展現(xiàn)一片廣袤的綠色原野,無數(shù)哥特式尖頂,在陽光下頌歌般地升騰,劍橋毫不吝惜地向每位來者,立即亮出了它完整的身姿。
牛津首次被《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提及,是在公元911年,位于市中心的牛津最古老的建筑撒克遜塔,已有近千年的歷史。牛津的著名,主要是由于牛津大學(xué)。但如今,究竟是城市創(chuàng)辦了大學(xué),還是大學(xué)造就了城市,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般,已無人能說得清。劍橋的歷史與牛津相差無幾,但劍橋大學(xué)的歷史卻稍短于牛津大學(xué)。有這么一則故事:1209年,在師生和市民間的關(guān)系已很緊張的牛津,一位婦人被殺,市民懷疑是學(xué)校里的人所為,于是,一場針對師生的報(bào)復(fù)行為,在城中大規(guī)模地展開。師生們被迫遠(yuǎn)走他鄉(xiāng),其中一部分人來到劍橋,創(chuàng)辦了劍橋大學(xué)。
然而,這本是同根生的一對親兄弟,長期以來竟始終相互懷有某種淡淡的敵意,這也許印證了中國那句“一山不容二虎”的老話。兩所大學(xué)在清楚地意識到對方強(qiáng)大實(shí)力的同時,彼此仍要不時顯示一下自我的優(yōu)越或?qū)Ψ降牟恍肌r至今日,在社會民主化和教育現(xiàn)代化的大背景下,在兩校的交流與合作越來越密切的大趨勢下,“對立情結(jié)”仍糾纏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比如,兩地人在言談中大都有意回避“牛津”或“劍橋”的名字,而互稱“另一個地方”。又如,牛津的子弟去劍橋上學(xué),或劍橋的本科畢業(yè)生去牛津讀研究生,仍往往會遭到家人和朋友的反對。在與兩地學(xué)人的交談中,我發(fā)現(xiàn),他們的互貶中,其實(shí)并無多少惡意,而更多為自賞,甚至是幽默。至于兩校間一年一度的賽艇、橄欖球和田徑對抗賽,雖每每劍拔弩張,氣氛熱烈,卻早已被視為一種友好的溝通。
一本旅游手冊關(guān)于劍橋這樣寫道:“劍橋在每個方面都與牛津競爭,它雖然在年歲和賽艇上處于下風(fēng),但在吸引力和景觀上卻稍勝一籌。”相較而言,牛津更深沉,劍橋更玲瓏;牛津更城市化,劍橋更像大鄉(xiāng)鎮(zhèn);牛津似乎更愿炫耀歷史,劍橋則較多地著眼于未來。但對一個外來人來說,兩地之同其實(shí)遠(yuǎn)大于異。至少在我看來,牛津和劍橋的美是不相上下的。在近千年的城市發(fā)展史上,這兩座城市從未經(jīng)受過大的革命和戰(zhàn)爭,幸運(yùn)地保存下各世紀(jì)的建筑代表作,使它們成了不可多得的、活的歐洲建筑藝術(shù)博物館。站在牛津的撒克遜塔和劍橋的圣瑪麗塔上放眼四望,周圍是一座座風(fēng)格各異的古建筑,一個個綠色的尖頂,一條條狹窄彎曲的街道,它們仿佛是隨意安排的,可相互間卻又有著完美的和諧和有節(jié)奏的呼應(yīng)。常有一群鴿子,在建筑群上瀟灑地飛過,于是,古老與新鮮,靜與動,便構(gòu)成一種奇妙的對照。兩座城市都有一條著名的河流。泰晤士河環(huán)繞牛津,河邊是寬闊的草坪,河上悠閑地游動著一只只天鵝,一對對野鴨,河邊散落著一張張長椅,椅上刻有一些逝去學(xué)長的姓名,還有一些親切、感人的話語:“我們感謝這座花園。”“這是我們深愛的河流。”“我們曾在這里度過最美好的時光。”……這是已逝學(xué)長自己或他們的親友捐贈的。小小的劍河則在劍橋城中蜿蜒而過,流經(jīng)一座座小橋,串起一個個深院,一年四季,都有學(xué)子或游人泛舟河上,在岸邊的柳樹下緩緩地穿行。在泰晤士河和劍河邊漫步,我常常會想起曾在牛津就讀的詩人雪萊留在他墓碑上的那句話:這里躺著一個年輕人,他的生命是用水寫成的。河流造就了城市,河水記錄著歷史,牛津和劍橋這兩個已不年輕的文化巨人,其生命也是用水寫成的。
牛津和劍橋的相近,更在于其濃厚的文化氛圍。作為世界上著名的兩座大學(xué)城,這里的居民多半與大學(xué)有關(guān),城里到處洋溢著濃重的書卷氣和文化味,書店、劇院和博物館比比皆是,多得與城市規(guī)模不成比例。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xué),都各有數(shù)十個歷史悠久的學(xué)院。劍橋的彼得學(xué)院建于1284年,而牛津最古老的大學(xué)學(xué)院已在籌備慶祝750周年校慶。這一所所學(xué)院散落在城市各處,都有自己獨(dú)立的校園,校園一般都由兩三個院落組成,院中也必定有高高的教堂、考究的飯廳、參天的古樹和綠色的草坪。一茬又一茬的學(xué)生,像院中的青草般生生不息,學(xué)院的傳統(tǒng),如古樹般莊嚴(yán)、挺拔。年復(fù)一年,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躊躇滿志地來到這里,由牛津和劍橋造就的各界名人,真可以說數(shù)不勝數(shù)。牛津和劍橋,是世界上僅有的兩所基本保持歐洲中世紀(jì)教育體系的大學(xué)。在這里,師傅帶徒弟式的教學(xué)方式得到廣泛運(yùn)用,教師授課是面對面的,一位教師只帶幾個學(xué)生。大教室中的公共課很少見,也就是說,兩校的本科生實(shí)際上是在享受研究生的“待遇”。盡管如此,如今也有人就這種教學(xué)體制的合理性及其人才產(chǎn)出效率等提出疑問,但這一方式的獨(dú)到價值還是顯見的,即有助于受教育者獨(dú)立人格和探索精神的形成。
走在牛津和劍橋的校園中,時而恍若置身于修道院:每個周末,學(xué)校教堂里都有禮拜,禮拜由駐校牧師主持,由音樂專業(yè)的學(xué)生演奏管風(fēng)琴,由師生組成的唱詩班放聲歌唱,歌聲和著此起彼伏的教堂鐘聲,久久回蕩在空中;在節(jié)日慶典、開學(xué)和結(jié)業(yè)儀式等正式場合,乃至各種會議上,參加者均著深色學(xué)位服,平日里,也常見到這身裝扮的學(xué)人,神色嚴(yán)肅、步履匆匆地走過;參加考試的學(xué)生,一律深色西服,并在胸前插上一支白色或粉色的康乃馨;每周一次的師生聚餐會,在教堂般的大廳中舉行,身著晚禮服的教師坐在餐廳一端的高臺上,學(xué)生則坐在兩排長桌旁,就餐前,還要由一位學(xué)生代表和校長來一段長長的拉丁語對話……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禮節(jié)和儀式都非強(qiáng)迫。也許,牛津和劍橋的學(xué)人,在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延續(xù)著他們的悠久歷史;也許,就在這近乎刻板、顯得守舊的規(guī)范和舉止中,對學(xué)術(shù)的虔誠、對傳統(tǒng)的珍重、與潮流的抗?fàn)幍葍?yōu)秀的學(xué)術(shù)品質(zhì)得到了培養(yǎng)。
傍晚離開劍橋,回首再望夕陽中的學(xué)城,頓時憶起徐志摩《再別康橋》(“康橋”為“劍橋”的別譯)的詩境: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其實(shí),面對牛津和劍橋這樣巨大的存在,你能帶走什么呢?當(dāng)然,你可以帶走知識,帶走學(xué)位,甚至帶走回憶,帶走愛情,但這里的氛圍和文化卻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