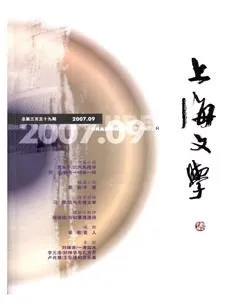舊書簽(六首)
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邊
春夜里隆隆的雷聲
將我從夢中驚醒
我不曾期望它會到來
像一位俠客蒙了面孔
多年了,即便他蒙上黑色的眼罩
我也不曾期望他是一位英雄
不曾。每逢這樣的時刻
他只會在黑夜里干咳幾聲
作惡多端的人不會
在雷聲中膽寒
善良和被欺的人們
也不會走出他們早已習慣的黑屋
沒有立場的春雷就這樣響著
我又回到了我虛妄的夢里
蚯蚓
泥土上出現了最小的山峰
一場春雨將它們喚醒
當我走過北京的街角
無意中看見了它肉紅色的背脊
這是一只首都的蚯蚓,很淺的泥土
讓我想起這個干冷的冬天
這被碾壓得鐵一樣的土地
如何藏下了它軟弱無鈣的身體
一條習慣了寒冷的蚯蚓
在黑暗中大概已學會了忘記
它很快藏起的一段暗紅
閃電一樣使我憶起了屈辱的前生
舊書簽
四十歲,身體的鈣質慢慢流失
就像下午的茶社,裝飾精巧
室內的花園布置別致,小橋流水
有音樂和女人的腳步
款款扭動的細節,倦意中仍然
騷動的思緒,片刻間不經意地迷失
四十歲,想不起第一次
走在鄉間田野望著城市時的激動
想不起第一次接吻女人的滋味
初嘗禁果時的顫栗,記憶褪色
就像九月里的樹梢開始慢慢枯黃
石縫間的秋草一天天變稀
四十歲,像一本看了多半的書
略有些乏味,但謎底尚未揭開
前面的故事已漸漸淡忘,只記得情節平平
節奏拖沓,缺少驚心動魄的波瀾
但讀到這個下午的一頁忽然心生恍惚
一枚掉落的舊書簽讓我視線模糊
一陣風吹過
坐在午后陰涼里的祖母
搖著她手里的一柄芭蕉扇
她松弛的乳房下垂著
宛若秋后干癟的絲瓜
一陣風吹過
在屋檐下編藍筐的祖父
哼唱著他爛熟的小調
荒腔走板,像一只夏末的蟋蟀
奔走在趕赴約會的路上
一陣風吹過
一冊酥黃的雜志翻卷在荒涼的板凳上
老花鏡已斷了一條腿
一根煙蒂還在冒著余煙
如記憶里的暮色一明一滅
一陣風吹過……
割草機
仿佛老年的幻覺
城市的空氣里傳來
割草機的轟鳴
和青草腥甜的氣息
童年粗鈍的鐮刀
劃向我悲傷的食指
劃開下意識的尖叫
像一聲劃開河流的汽笛
割草機,而今正像剃須刀
讓這個荒蕪的早晨
繃緊了神經
被修改的花園
流著新鮮好聞的汁液
卻蓋不住大片的傷口
來自記憶的疼痛和血腥
預言
那時,我們長眠在地下
親愛的,你的泥土混著我的泥土
就好像心貼著心,手挽著手
回想著,多年前的這個夏天
一場悲劇,一場暴風雨
一場發生又消失了的愛情
像盛開的鮮花,在風中化作塵泥
那時,我們將擁有一次
真正的長談,親愛的
沒有人打擾
沒人能聽得懂我們纏綿的詩句
可現在我們還活著,活在各自
堅硬又軟弱的軀殼里
那時,我們會很滿足地挨在一起
親愛的,就像我們不曾來到這個世界
不曾有過一場錯過
一場災難的相逢
不曾有,一場生與死的回憶
不曾有——
一場關于幸福和完整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