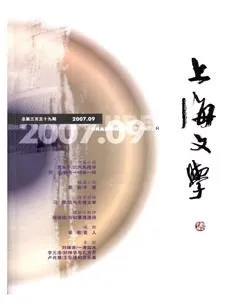財神爺與孔方兄
有貝之“財”雖然是金錢與物資的總稱,但漢字中的“財”本來就是造字六法中的“會意”字,由人手持原始的貨幣組合而成,主要不是指財物而是指金錢。在當今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商潮動地,錢浪拍天,過去被清貧與清高的眾生愛而慕之敬而遠之的“錢”,已經以“換了人間”的態勢,由“銅臭”而“錢香”,取代了過去的階級斗爭為綱的苦難歲月中的“斗”,獲得了君臨一切舍我其誰的地位,簡直成了身價的證明,豪門的標志,權力的象征,以致天下蕓蕓不可一日無此君。雖然身后是非仍然誰管得,古今一律,但現在已不是“滿村爭說蔡中郎”,而是滿城爭說財神爺與孔方兄了。
金錢,本來無知無覺,屬于無辜而有功之輩。當代美國作家泰德·克羅福德著有《金錢傳》一書,在山泉水清,他認為金錢起源于人類謀生存的一種神圣之心,和對群體式團結的向往,“其本來含義是犧牲、貢獻和分享”,他為金錢追本溯源,還的是金錢的清白之身。而一部分人先暴富起來而大多數人卻在溫飽線上浮沉,許多人甚至還在貧困線上掙扎,定會帶來許多心理的與社會的并發癥和后遺癥。兩千多年前詩經的《小雅·民勞》篇早就企盼過了:“民亦勞止,迄于小康。”先民呼吁的,是黎民百姓都能過上“均富”的小康生活。無論是個人的貧窮困苦,或是眾生的貧富不均,都是可怕的災難。報載,中國百分之十的富人擁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而在未來十年,超級富豪的人數會越來越多。金錢,應該如及時之雨普惠天下蒼生,使他們取之有道,儲之無虞,用之在德,豐衣足食,利行而安居。只有如此,金錢才是澤世的甘霖,可愛的寶貝,快樂的天使。
金錢是無辜的,有辜的是人,特別是那些極具占有之欲與貪婪之心的取之無道的不義之人。“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親愛如兄,字曰孔方”,舊時銅錢中有方孔,故人昵稱為“孔方兄”,西晉魯褒所作《錢神論》首先為這一名稱注冊,而宋代詩人黃庭堅在《戲呈孔毅文》一詩中,也有“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的名句。現在不少人深感世風日下,總是說“世風不古”,其實今古相通,古之世風雖大體勝于今日,但也常常并不怎么美妙,魯褒在《錢神論》中就指出當時“風紀頹敗,為官從政莫不以錢為憑”,而錢的秘效奇能則是“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而且“忿事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撥;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淡笑,非錢不發”,這似乎也是今日種種社會相的寫照。魯褒之后,唐玄宗時的張說寫過一篇奇文《錢本草》,他認為錢“味甘、性熱、有毒”,要以德義禮仁信智來聚積和使用金錢,否則就會“污賢達,畏清廉”,“召神靈,通鬼氣”。然而,時至元代,金錢更幾乎成了整個社會唯一的通行證,蕓蕓眾生唯一的主打歌。
按照草原游戲規則勃興壯大而且馬上得天下的元蒙統治者,一本草原共產大部落的遺風,國無定制,制無定法,除了歷朝歷代普遍皆然的內部你殘我殺爭權奪利之外,他們只知橫征暴斂,窮奢極欲,胡吃海喝,“國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飲,三者而已”,元人王坤在《秋澗先生大全集》中就曾經這樣說過。頭腦尚稱清醒的名臣耶律楚材,曾提著酒具勸誡皇帝不能整天狂喝濫飲,他的比喻是:石頭都可水滴石穿,何況血肉之軀?元蒙這幫統治者卻同時是現實快樂主義者,他們耽于逸樂,追逐眼前的官能享受,就必須以金錢為后盾,于是便一改以前漢民族的重農輕商,著力發展經濟,商業經濟發達起來,如同藤上牽瓜,餐飲業與娛樂業也同步繁榮。國家與個人追逐的都是財富,金錢就變成了使整個社會昏天黑地的沙塵暴,于是,元曲中與“錢”有關的作品便屢見不鮮:
這等人何足人間掛齒牙!他前世里奢華,那一片貪財心浸命煞。則他油鍋內見錢也去撾。富了他這一輩人,窮了那數百家!
——鄭廷玉仙呂·天下樂《看錢奴》
鄭廷玉所撰雜劇《看錢奴冤家債主》,是我國古典喜劇史上的杰作,其主人公貪財奴賈仁,絕對可以和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筆下的錢奴“葛朗臺”比美。上引之曲出自該劇的第一折。“富了他這一輩子,窮了那數百家”,一個人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財富的高樓,正是建筑在許多人貧困的洼地之上的。作者所指斥的,乃是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的歷史,歷史如鏡,也可鑒照今日的現實。
馬致遠的仙呂·寄生草雖是從另一個角度落筆,但也萬變不離其“錢”:
這壁攔住了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則這有錢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
此曲出自《薦福碑》第一折,《薦福碑》是馬致遠創作的雜劇之名,此乃劇中人物張鎬自嘆自唱之辭,窮書生張鎬寄跡于薦福寺,貧困潦倒,他嘆的不僅是貧富不均,而且是是非顛倒,聰明人與賢良者坎坷困頓,官員們與不學有術者卻十分富有,這,雖不是元代所獨有卻是元代普遍可見的一道灰色風景線,社會眾生相。
就像傳染病的惡性蔓延一樣,拜金主義在元代盛行,已經不是小氣候而是大氣候。除了一去不可復返的青春無法用錢買到之外,如元曲家薛昂夫在中呂·山坡羊《嘆金身世》中所說的“黃金難買青春再”,世間其他的一切,有什么是金錢所不能買到的呢?對這種世風或者說世相與世道,張可久的正宮·醉太平《嘆世》,為其定格顯影,沒有讓它與時俱逝:
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親水晶環入面糊盆,才沾黏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
“人皆”與“誰不”出之以肯定判斷句,寫盡了“錢”在社會中和人心里君臨一切的地位。“面糊盆”乃元時市井俗語,意同于今日所謂之“大染缸”,即使是純美如“水晶環”一樣的人,如果不自守自律,一入染缸也會近墨者黑。而“文章糊了盛錢囤”呢?則是指讀書人為權貴替富豪歌功頌德,敷粉涂脂,出賣自己的靈魂而換得殘杯冷炙,時至今日,那種傍官員依大款唯錢是命的偽文人難道還少嗎?清人有位陳眉公,他的《小窗幽記》寫得頗為清雅出塵,但為人行事卻與之相反,清詩人舒位有詩刺之:“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功名捷徑無心走,處士虛名盡力夸。獺祭詩書稱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只云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這,可以說是“文章糊了盛錢囤”的后代注腳。元代是一個縱欲與享樂的社會。“門庭改做迷魂陣”,正是形形色色的賺錢的色情場所的寫照,如同今日許多掛羊頭賣狗肉的場所一樣。“餛飩”,此處意為“混沌”,即糊涂混濁之意,而“清廉貶入睡餛飩”,即清操毀棄,貪欲雷鳴,元代官僚群體之愚昧腐敗,即可想而知。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蘇格拉底面對百貨俱備的集市曾說:“這市場上竟然有這么多我不需要的東西。”貪得無厭的官員們的心態則恰恰相反,他們恨不得施行另一種意義上的“萬物皆備于我”。張可久是元代后期散曲大家,與喬吉有“曲中李杜”之稱,其散曲工對偶,美辭藻,講究格律,善用典故,風格清麗典雅,但此曲卻悉排典語,獨鑄俚辭,結尾之“葫蘆提倒穩”亦是,“葫蘆提”是俗語也是雙關語,即喝酒與糊涂之意,如此正話反說的憤世嫉俗之語,正是清人鄭板橋“難得湖涂”的先聲。
貪婪聚斂民脂民膏以供追歡逐樂至死不悟,這是當時的貪婪者與掠奪者的本性,散曲大家喬吉山坡羊《冬日寫懷》,以三章為其寫照,下引的是第二首:
朝三暮四,昨非今是,癡兒不解榮枯事。儹家私,寵花枝,黃金壯起荒淫志,千百錠買張招狀紙。身,已至此;心,猶未死!
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第九章《元代的散曲》中,對此曲評價很高:“《冬日寫懷》三曲寫得最為沉痛,‘黃金壯起荒淫志’,這話罵盡了世人。”如何罵盡,有待于高明的藝術。對戲劇創作的結構,喬吉曾提出過“鳳頭、豬腹、豹尾”的名言,即開頭要漂亮,令人一見傾心,中間部分內容要充實豐滿,收結要有力,叫人尋索不盡。此曲正是如此。首句對仗,寫盡了世事榮枯盛衰之反復無常,引發下文,也遙通結尾;中間部分嘲諷罵世,對貪婪者掠奪者的斂財享樂,賣官鬻爵,作了窮形盡相的刻畫與揭露。結尾則指出他們至死不悟,一條道走到黑,短語長情,十分有力。試看今日的貪官污吏如成克杰、胡長清之流,簡直已經形成了一個貪官的“群落”或謂“群體”,而他們無一不是花天酒地地“荒淫”,養小蜜,包二奶,而最后落得一張供認不諱簽字畫押的判決書,從極樂的天堂墜入十八層萬劫不復的地獄。
在世界文學名著中,有所謂“四大吝嗇鬼”形象,那是刻薄的標志,鄙嗇的典型,貪婪的象征。英國莎士比亞名著《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是原始財富積累過程中高利貸者的典型;法國莫里哀的有關名著,就是直接以《吝嗇鬼》為書名,其主要人物阿爾巴貢,就是以高利貸起家致富的資本家典型;法國女作家喬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中的布芮可南,是由佃農一躍而成暴發戶的典型,而法國巴爾扎克四大名著之一的《歐也妮·葛朗臺》呢,刻畫的則是名聞遐邇的投機商與守財奴的典型了。元散曲中所塑造的此類人物形象,與上述西方名著中的同中有異,而最為成功和突出的,雜劇數鄭廷玉所塑造的賈仁,散曲則要推錢霖在般涉調·哨遍中所刻畫的“看錢奴”了。
字子長的錢霖,是松江(今上海市松江縣)人,不屑功名,家道寒素。現存作品僅雙調·清江引四首,套曲般涉調·哨遍一套,但他卻以此在散曲史上書寫了屬于自己的篇頁,尤其是他的僅此一套的套曲,今日的任何元曲選本都不敢將它遺忘。錢霖所塑造的這一“看錢奴”,其原型本是一既鄙且吝富而且驕的晚輩,但成功的文學形象的意義已不限于原型,錢霖所塑造的這一形象,已是對世間一切狠毒慳吝的剝削者貪鄙者的典型概括,而且這一人物形象的誕生,既啟示了清人吳敬梓《儒林外史》中對嚴監生的創造,也遠在西方文學中大貪鄙者形象呱呱墮地之前,這,大約也是連錢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
錢霖這一套數,由十二支曲子組成,為節省篇幅,只能作窺一斑而知全豹式的摘錄: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蓋,油鐺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后?曉夜尋思機彀,緣情鉤距,功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馳驅,馬足塵中廝追逐,積攢下無厭就。舍死忘生,出乖弄丑。
十煞漸消磨雙臉春,已雕颼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柜頭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
二煞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系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上木驢釘子輕輕釘,吊脊筋鉤兒淺淺鉤。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悠悠。
尾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里甃,任他日炙風吹慢慢朽!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套曲的開篇即是全文的主腦,一篇的綱領,全曲就是圍繞看錢奴的卑劣靈魂、丑惡行徑、可恥下場之“臭”而展開。看錢奴為了錢財,不怕油鐺插手,血海舒拳”,不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廝追逐”,不畏“舍死忘生,出乖露丑”,套曲從“十煞”至“五煞”,作者以五個段落,從多方面揭露看錢奴的丑惡行徑,和他們虛偽狡詐狠毒慳吝的性格本質。“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這不僅是對古代看錢奴的鞭笞,今日那些哄蒙詐騙花樣翻新的惡賈奸商,那些號稱“人民公仆”其實是“公仆人民”的貪官污吏,何嘗不可以或由他人驗明正身,或由自己對號入座?從“六煞”以下至“尾聲”五段里,作者描繪的是聚錢奴橫貪暴斂的后果與下場。生前只恨聚無多,待到多時塚沒了。結果是“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里甃,任他日炙風吹慢慢朽!”現在身敗名裂的污吏貪官和奸商惡賈呢?雖不再如古代那樣在通衢大道上暴尸示眾了,但卻會經由各種現代的傳媒紙媒而告示天下,受到法律的懲治與道義的譴責。如果他們能早日讀到錢霖的上述作品,也許會如醍醐灌頂而“金盆”洗手吧?當然,這只是我們的良好愿望而已,君不見舍生取錢的人不仍然在成群結隊視死如歸前赴后繼嗎?
中國的古人有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印度現代作家阿基蘭,在他的《畫中女》一書中也有如下的引語:“憑自己的本事和正當手段掙來的錢財,可以使我們贏得道義和幸福。”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中國古代的魯褒早在《錢神論》一文中就曾指出種種后患與惡果,而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之一的索福克勒斯,也早在其《安提戈涅》一劇中說過:“人世間再沒有像金錢這樣壞的東西到處敗壞人的道德”了。見錢眼開,一般平民百姓中的貪財者,對社會尚不會構成根本性的危害;欲壑難填,貪財者的貪官如果形成了一個人多勢眾的強勢群體,那就是社會腐敗之源,國家動搖之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廟堂與江湖都只知膜拜財神爺與孔方兄,缺乏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律令的自覺約束,拜金主義像疾風烈風颶風臺風甚至龍卷風一樣盛行橫行,那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大約就不止于杞人來憂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