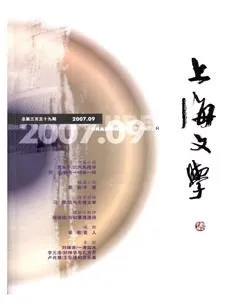我與先鋒文學
今天我就說說我和先鋒文學吧。“先鋒文學”的概念對小說家來說,不是一個特別情緒特別固定的概念。這頂帽子是學者們扣到我頭上的。說老實話,我寫小說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我寫的是什么小說。我的小說比較關心方法論、小說的構成。在早年大家特別著迷于結構主義哲學的時候,很多結構主義批評家都用結構主義方法來分析小說,包括分析我的小說。在很多年里,我戴的帽子是“結構主義小說家”。這聽上去好像比“先鋒小說”還拗口,至少“先鋒”后面沒說什么什么主義。
以我的記憶,“先鋒”這個概念定型基本上是在90年代中后期。人們在梳理已經經歷的一個世紀時,一些文學史家逐漸把原來不是特別清晰的一個作家群落歸結到“先鋒”這個大旗之下,叫“先鋒派”,或者叫“先鋒文學”、“先鋒小說”。
我對“先鋒文學”的名頭還是有一點疑問。今天我們說“先鋒文學”通常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通常我們知道在這個大旗下可能會有余華、格非、蘇童、馬原,或者還有莫言、洪峰、孫甘露、殘雪這些名字,但特別準確的定義我個人一直不是特別清楚。
中國有個很特別的年份——1985年,在這一年中國文學史上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這之前,從1979年開始,我們習慣上把它在文學歷史上劃定成一個歷史階段,叫“新時期”。1979年出現了一些小說,把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過的、全中國人民都關心的事件作為小說的主要內容。那時候有個小說叫《傷痕》,是上海作家盧新華寫的一篇很短的小說,寫的是一個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傷那么一個小故事。你們別小看這個小故事,可能今天在座的一半以上的人都會覺得這東西我也能寫,我寫得可能比他好,但是有趣的是,新時期文學就是從那么一個像習作一樣的小文章發端了。那一整個文學大潮都被冠上了“傷痕文學”的名字。這是新時期最初的一波大浪。在那個回合里,我們認識了很多我們的前輩作家,比如說像王蒙啊、劉心武啊,比我們再年長些的像馮驥才、從維熙。這撥作家突然對剛剛過去的那段時間給全國大多數人群所造成的心理或者事實上的創傷發生了興趣,所以當時一個作家寫一篇很小的小說,往往能一夜成名,變成全中國人民都知道的人物。就好像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比爾·蓋茨,今天我們生活里都離不開比爾·蓋茨開發的軟件,那時候全中國人民都離不開那些傷痕作家。那撥文學起來之后,誰也沒有料到它會在中國當代史上一枝獨放。劉心武寫過一個小說叫《班主任》,也是一個小短篇,大概萬把字,寫的事情也不太大。但是那么一篇小說一下子讓劉心武變得家喻戶曉,我看今天知名度能超過劉心武當年寫完《班主任》之后的名氣的人不太多。當時幾乎全中國人民都知道劉心武,都在看他的《班主任》和他之后的一些小說。這種關心自己身邊的人群、關心自己和身邊人的處境的文學浪潮幾乎一口氣就延續了五六年之久,從1979年差不多到1985年。那時雖然也有其他類型的小說,但是基本都是在一種關心自身處境、關心內容的情況下寫作。文學特別熱烈,和公眾的關系前所未有的接近。都說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特別好的年份:一個是30年代,一個是80年代。我相信30年代那撥文學對公眾的影響和80年代一定沒法比,這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在30年代,中國具有閱讀小說的能力和日常養成閱讀習慣的人群應該非常之少。我問過我父母,我父親要活著現在也是八十多歲了,他是國高也就是現在的高中畢業的。他說那個時候他的國高學歷在中國老百姓中是少之又少的,人家已經覺得他很有學問了。但是我爸說他根本不看小說。所以我覺得三四十年代“文學黃金時代”的說法有點可疑,可能更多是在文學史家們那里才成為文學的“黃金年代”。但80年代真的是文學的黃金時代。你們在座絕大多數都是80年代出生的人,在你們出生的那個時間里面,文學在很多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為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因為在那個年代電視還不太普及,沒有電視,沒有很多電影,整個公眾突然一下子對文學發生興趣,這要歸功于1979年開始的新時期文學浪潮。
但是這浪潮在它平平穩穩走了五六年后,突然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在今天看來非常大,但當時大家根本不知道出了問題。僅僅是有一小撮像馬原、余華、孫甘露、殘雪這樣的對寫小說有熱情的年輕人,他們當時心里覺得有什么不對了:那些小說不都是說事的嘛,那些事有什么好說的?他們家誰誰誰被誣陷了,他們家誰誰誰被冤枉了,他們家怎么怎么樣,這種事情說來有什么意思?就是有那么一撥當時和現在在座的你們年齡差不多的、可能比你們還年輕的年輕人,他們就覺得如果看小說只是光讓我看這些事,我并不一定非看文學吶,我可以看《故事會》、看各種各樣的法制小報,那里面都是案例和離奇古怪的事情,你們說的事情沒有多有意思。所以我說,在文學洪流平平穩穩向前移動的時候,有一些人慢慢覺得出了問題:那時沒人關心小說怎么寫,大伙關心小說寫了什么。在1984年末,突然中國有一篇很有趣的小說叫《棋王》。這個很奇特的小說突然被讀小說的人們發現了,覺得這故事跟別的故事不太一樣:命運都差不多,但是寫得不一樣,看上去有一點好玩、有一點特別。緊接著在1985年初的時候,在《上海文學》出了另外一篇小說,叫《岡底斯的誘惑》,寫小說的人就是你們面前的馬原。那小說是我1984年春節前后在青城山寫的。那時我在西藏,我從西藏出來住在灌縣縣委招待所,那時整個都江堰市只有一個招待所,沒有賓館,我就住在那個招待所里面。當時特別冷,我聽說我運氣特別好,趕上了一場一百年沒見過的大雪。那雪花的直徑大概有五公分,那么大的雪花漫天飄散,我有時候就想那時候那場雪是不是老天專門助我的興來了。我一個人住招待所,我寫作的習慣是我寫上一兩個小時就要出去一會兒,踏青去。踏不著青,踏得全是白。我從灌縣出來往山上走,那個大雪非常的奇妙,那應該是一二月之間的一段時間。我是自費出游,那時候自費挺奢侈的,你別看住招待所十元八元的,那時候拿出個十元八元也挺困難的。我懵懵懂懂地把小說寫了出來,當時我還算是個已經發過小說的作者。我把我的小說投到當時我非常心儀的《上海文學》,《上海文學》的老主編李子云老師很快就給我回了一封信,她說“馬原,看你的小說挺有意思,但是沒太看懂。我自己拿不準,又給編輯部其他同事看,有的說喜歡,但是大家也都說沒看懂。不好意思,給你退回來”。那時候你想想,老主編是我們很景仰的文學前輩,她說沒看懂,我稍微有一點沮喪。后來就是這篇小說被我另外一個老大姐——四川女作家龔巧明看到。她大學畢業去了西藏,當時我也在西藏。我們的私人關系很好。她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大姐,看了我的小說以后,她也是跟李子云老師一樣的態度。她說馬原,我覺得你寫得特別好,但是我怎么沒看明白呢。我說你什么意思啊,我寫的哪個事情你不明白啊?她說是啊,你寫的哪個事我都明白,可是看完了我不知道該說啥。結果就是這么一件事。然后龔巧明剛好去西安電影制片廠改劇本,她就碰到了我們另外一個文學前輩——李陀,當年他也是個小說家。龔巧明就把她的那份語焉不詳的激動傳達給了李陀,她知道李陀在文學上很有見地,又特別活躍,所以她就希望李陀幫我把小說推出來。她覺得不能埋沒了,就好像看到塊金子,看到它發光了,但是不知道它為啥發光。結果就把這篇小說拿到北京給李陀看,李陀那時在我們眼里是很大的人物了,估計也很忙。然后龔巧明回到西藏以后,我就從西藏出來,她給了我一個李陀的電話。到了北京我就給李陀打電話,我說李陀,我叫馬原,我有一篇小說在你這里,我想取回來,因為我沒有底稿。他就說啊呀不好意思,我還沒看呢,你能不能延我一天,明天我們見一下。我說可以,那我就在北京多逗留一天。李陀看了以后也挺激動。李陀可不是龔巧明、李子云,凡事李陀他都要說出一二三甲乙丙來。李陀當時就說,馬原,你的小說我得想辦法幫你發出來。結果我小說的手稿就留在李陀那里。后來我回西藏以后,聽說這小說又有了一連串的故事:走過幾個編輯部,幾個編輯部基本上都發不出來。因為人家總不能發一篇看不懂的小說。后來1984年下半年的杭州會議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個挺重要的事件,中國當代最有名的小說家、批評家齊聚一堂研討中國文學大事。圍繞這個會議日后都有很多文獻出來。李陀把《岡底斯的誘惑》帶到那個會議上,首先那些少壯派,就是我的同齡人們,他們一下子激動起來了。最早激動的是韓少功。盡管那時候韓少功是我的同齡人,但他那時已經功成名就,是長沙文聯的主要領導人了。他手里有一本刊物,那時候年輕人手里有一本刊物可不得了,那時候刊物都是像李子云老師那樣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掌管,而李子云老師也不過是副主編,巴金巴老師才是主編。韓少功說這篇小說沒人發我發。但是在開會的時候,李慶西啊、吳亮啊一撥朋友看了以后說,少功發在你那兒太虧了,發在你那兒誰看吶。韓少功想想也是,就帶著一群哥們的想法又再攻李子云老師,說李老師,有篇小說很有意思,發在你那兒吧,發在我那兒沒人看。怕明珠暗投。然后李子云老師說那小說是我退的,我很賞識這個作者的,我給他回過信,還在編輯部里傳看過。就這么一件小事情,在今天說這小說算什么呀,不過是作家玩了點花樣,在里邊寫了三個故事,偶爾還換換人稱,這三個故事關系好像還不是太大,亂七八糟的那么一個故事。在當時中國文壇大伙突然就覺得挺好玩的。在杭州會議上,李子云老師痛下決心要發這篇小說。因為一篇小說經常會把一份雜志砸掉的,你這篇小說發得不對了,這個刊物就有可能被封掉。我另外的小說也有差點把人家刊物關掉的,我有篇小說叫《大師》,差點把當年就已經非常著名的《作家》雜志封掉。我那《大師》出來以后,有人覺得我傷害了藏族人民感情,有關部門就發紅頭文件針對那篇小說。這是另外的話。《岡底斯的誘惑》是李子云咬咬牙發出來的,后來就這件事情大家有很多共同的回憶。我之所以用這些時間說《岡底斯的誘惑》這件事,因為今天要說的是先鋒文學,大家習慣上愿意把《岡底斯的誘惑》作為先鋒文學的一個事件來提。這篇小說里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呀?人家劉心武寫《5·19長鏡頭》,那是中國出了那么一個事件,大伙關心一下也正常。我這個小說盡寫我在西藏的那些亂七八糟拉拉雜雜的事,今天找野人明天看天葬的,這些事有什么意思呀?但是那時候馬原和馬原同時的那些作家,他們就覺得一天到晚看張家人受冤枉了,李家人受迫害了,也沒什么意思。在1985年這年里,中國的小說家里有一批人,他們一下子把小說關注的焦點從“寫什么”,從內容,一下子轉移到“怎么寫”,也就是轉移到方法上來。
1984年末的《棋王》、1985年初的《岡底斯的誘惑》這兩部小說等于說是吹響了先鋒文學的號角。吹響了這個號角之后,在1985年文學史上發生了更大的事情,那就是王蒙當了《人民文學》的主編。王蒙起用了一個枯干瘦小、戴著大眼鏡的上海男人,他就是今天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編朱偉。朱偉當時是《中國青年》雜志的編輯。王蒙在日常交往中發現了朱偉,他到《人民文學》當主編就把朱偉挖到了《人民文學》。朱偉年齡跟我們差不多,是一個特別有眼力、特別有見地的編輯,他當時一下子就抓到了一大批和以前主流的寫作特別不一樣的小說——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何立偉的《白色鳥》。就這么幾篇東西,再加上前面說到的《棋王》、《岡底斯的誘惑》,一下子就把文學的焦點聚過來了。那年王蒙很重要的一個舉措就是《人民文學》開了一個研討會,那是我生平第二次有幸參加正式的文學活動,有點誠惶誠恐。在那會上看到很多我們平時只能在雜志上看到名字的人物,比如說從維熙、鄧友梅、王蒙啊。這些名字能在媒體特別不發達的年代讓我們耳熟能詳,實際上他們都是大得不得了的人物。特別有趣的是,這個一兩天的會議上,真正唱主角的居然不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名作家們,而是那些說話聽上去也沒譜、一個個長得歪瓜裂棗的年輕作家。這些人說話在這些名家、大家面前只是幼兒園水平,有點兒胡說八道。但是在這個回合里,他們已經露出端倪。我和這群人——劉索拉、徐星、莫言、何立偉就是在1985年這個會議上認識的,而且在日后許多年里也正是由這些人領銜,撐起了整個中國文學的一片天。今天他們中的某些人,比如說莫言,還依然是中國當代小說的中流砥柱。那次會議的具體工作都是由朱偉操作的,等于說是在1985年里由朱偉組織,中國發生了一場文學運動。那次會議的主題——小說的方法論,實際上就是后來先鋒文學的主題。
“先鋒”兩個字,我不是特別贊成把它當作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現象去冠名。“文學先鋒”一定是超前的,把自己的時代落下一點距離的文學才稱得上“先鋒”。我們現在說的“先鋒文學”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二十年以后你還稱它是先鋒,它已經是個過去時,而“先鋒”在我心目中總是未來時。在我心目中,我一直不是特別認同把我們這群人的寫作叫做“先鋒文學”。我們肯定是“后衛文學”,甚至是“守門員文學”,我們的主要創作是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70年代。一代一代的先鋒已經跑到哪兒了?韓寒他們已經跑到哪兒了?韓寒他們充其量也就算個中場吧,現在真正的先鋒還在韓寒他們前面。歷史有時就是這么殘酷,也不知道是哪個文學史家提議,大家也認同了,所以最終把“先鋒文學”這個名頭,定位到我們1985年新出現的這撥作家身上。
“先鋒文學”在1985年僅僅是個端倪。它真正大潮洶涌要晚一點,發生在另一本刊物上。盡管1985年《上海文學》、《人民文學》出現了一批有意思的小說,但是并沒有形成勢頭。1985年以后開始,中國文學開始慢慢熱鬧起來。1984年的時候《鐘山》雜志決定改版,他們在1984、1985年之交,做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要當經紀人,要簽一大批作家:你只要和我們簽約了,你拿的稿費就比別人高。《鐘山》一口氣簽了四十多個人。我在我們那代作家里算是出頭比較晚的,我大概只能算是1985年出頭的,我的同輩作家都比我要早一點,他們在1985年以前就已經出名了。《鐘山》一下子簽了四十三個,沒排上我。我沒簽上的結果就是我損失很大,假如我要是給《鐘山》寫稿,別的刊物一千字是十元的話,《鐘山》就有可能給十五元。我每寫一千字我就要損失五元錢。那時候這可是不得了的事。《鐘山》一簽就是一兩年,你想想我們這些人勤快也罷、懶也罷,一年總要寫個十萬八萬字的。我要是寫十萬字,你想想我要少多少。
《鐘山》的那撥我沒趕上。后來我倒趕上另外一撥。就是我的一個大學同學,也是一個非常棒的編輯,叫張英。他在東北沈陽編了一本刊物叫《中外文學》,他因為和我比較投緣,他就拉我和他一塊兒辦《中外文學》。我就成了編外的大編。《中外文學》在當時中國文壇也是一份特別活躍的刊物,我不謙虛地說這當然有我的一份功勞在里面。還有原來就是中國文學中堅力量的《上海文學》、我特別景仰的一個老編輯主持的《作家》月刊,還有比如《花城》,他們都在這個回合里做了非常大的貢獻。文學這個東西,它要生長就一定得有平臺、土壤,可以這么說,當時它的主要土壤一定不是出版社,一定不是出書,而是雜志。在那個年代,雜志是一個特別火紅的事業,很多雜志都可以發行到百萬冊。我所在的遼寧就有一本雜志叫《鴨綠江》,現在我估計能不能過一千冊我不知道,但當時能發行一百多萬冊,非常非常厲害。這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情形,因為當時讀雜志的人太多了。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三本雜志:《收獲》、《人民文學》和《上海文學》。在這些名刊之下,還有我剛才提到的那么一批雜志。這批雜志對新作家的出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本雜志里有兩本是上海的,這兩本雜志孕育了一大批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作家,比如格非。格非的寫作就是誕生在上海,1985年他剛剛開始寫作,但是到了1987年的時候他已經成了先鋒文學的主將之一。蘇童的大批東西也是在上海,包括在《中外文學》上發表的。比他們更晚一點、但是年齡上很接近的一撥作家,像北村。北村現在的創作還依然保持著極好的勢頭,他的小說《我和上帝有個約》得了去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年度小說家獎,還有南京的朱文,這么一批極具沖擊力的小說家。
1987年《收獲》做了另外一件事,組了兩期專稿。有一期(1987年第5期)專稿也就是后來先鋒文學的雛形,是程永新用了大半年時間組的一期稿子。在那期上,有洪峰、蘇童、葉兆言、余華還有馬原。在那期雜志之前,《收獲》實際上還可能有一個更大的舉動,但是夭折了。在《收獲》整個發展的幾十年里,它沒以地域為專刊組過稿子,那時《收獲》的執行副主編李小林和程永新一起準備出一期西藏專刊。當時我人在西藏,對西藏的事情稍微熟悉一點。我在西藏的那段時間里有一批非常有個人特點的作家,你們現在有的人可能還知道扎西達娃,但另外一些名字你們可能都不太熟了,像色波、金志國、啟達。《收獲》這本能夠影響整個中國文學走向的大刊物,第一次專門以地域、以一個彈丸之地約了一期稿子——西藏別看面積很大,占中國國土的八分之一,但是我在的那些年,整個西藏總共不到兩百萬人,只有上海的一個區那么大。那期稿子說老實話是被兩個人給毀掉了:一個是馬建,也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現在在英國,是一個英國作家了,在英國也得過一個很大的圖書獎;還有一個就是馬原。“二馬”當年就把那期西藏專號給毀掉了。因為馬建當時寫了個小說,被《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點名批判;加上馬原在《作家》雜志發了篇小說,《作家》雜志被停刊整頓,當時吉林省的主要領導、中央委員還是候補委員,要坐到雜志社去整頓雜志,當時形勢很嚴峻。當然我之所以敢在這里跟你們提,是因為后來西藏自治區黨委開常委會,討論馬原有沒有傷害藏族人民感情,他們給我的結論是沒有。
在那個回合里,另外一些作家逐漸地走入了大家的視野,就是上海作家孫甘露。孫甘露的小說是非常奇幻的,非常詩意。在我眼里,他寫的是很虛幻的生活。雖然他寫的那些人物都是有形的實體,但是我看孫甘露的小說,我覺得他的人都像影子,都不太像人,有一種很縹緲的詩意。孫甘露多年來一直寫詩,他的文字有著我非常贊賞的縹緲的不確定性。那時候因為我也幫著一些雜志或者報紙編詩,有時候我順手就把孫甘露小說的某個段落拿過來,我一分行,就把它變成了詩,變成了“詩人孫甘露”,實際就是從他小說里隨便拿出一段來。我很多年以前就做過這樣的事情,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們編過一本文學描寫詞典,幫春風出版社還掉了它十七年的債務,那本書當時發行了幾百萬冊。那是我們一個老師的創意,我們一群學生編的。我編我那部分的時候用了一個特別有趣的方式:我喜歡雨果的名著《笑面人》,比如我就翻到《笑面人》的第十七頁,我從第二行開始到第十九行拿過來就抄上,因為它哪一段都精彩極了。雨果的那些巨著都是詩篇,我少年時候就迷雨果迷得沒辦法,不可救藥地迷雨果。那么我說孫甘露的文字就是有那種美感,隨便拿過來都是非常詩意的文字,特別特別棒。
跟孫甘露有可比性的,是殘雪。殘雪的故事也都像影子一樣。孫甘露小說的情境有點像我兒時讀的老舍的《微神》:就是一個男人到一個房間里,就覺得那個房間里什么都不真實。看到自己特別喜歡的女人,跟那女人敘敘舊,完了最后一捏那女人的手還是腳,結果是白骨,他一下子就給嚇壞了。孫甘露的小說有那種氣息,很美。而殘雪的小說不是,殘雪的小說都是影子,我那時讀殘雪的小說就覺得瘆得慌。我寫過一篇小說叫《虛構》,那里邊寫麻風村。我覺得殘雪小說里面的人物都像麻風村里見到的。那些人完全視你為無物,他們過自己的生活。他們的小說當時主要發在《上海文學》上。
前一陣子我知道80后他們也很憤慨:為什么要把我們放在一個框里,我們是不一樣的呀。韓寒是韓寒,張悅然是張悅然,郭敬明是郭敬明。他們覺得很不服氣。實際上,把我們這些人放在一個“先鋒文學”的框里,我們也很委屈。但我們都是過來人,委屈點就委屈點,他們委屈不忍著。實際上我們坐到一起,會發現我們不太一樣。比如說盡管余華和蘇童都是江南才子,一個是蘇州人,一個是嘉興海鹽人。這兩個作家的名字經常被同時提及,但他們有多少可比性呢?我看余華我就覺得余華特別狠,不停地殺人。他剛出道的時候殺人如麻,他每篇小說都要殺人,特別神經質。你再看蘇童,溫婉細膩,比女人還解風情。他的《妻妾成群》剛寫出來,現在遼寧省作家協會的主席叫劉兆林,那天就敲我門,問我看沒看《妻妾成群》,我說看了,他說他就奇怪了,蘇童多小啊,為什么越年輕越老道啊?蘇童寫得太絕了、太成熟、太老道了。我看《妻妾成群》的時候我覺得真是無懈可擊。因為好的作家一定是好的心理學家。他們一定會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群心理有更準確的拿捏,有更強烈地把他們放大的能力。像我們這些職業作家看小說可能跟你們不太一樣,你們看小說可能只是看個小說好不好,有興趣沒興趣,我們看它的起承轉合、變化、人物的性格邏輯、對白里的邏輯能不能成立。以一個行家的眼光看,《妻妾成群》這么個可以說是由少年完成的小說,幾近完美,非常之精到。無論是人物塑造、心理刻畫、對白、場景、環境都非常精彩。
而格非有種優雅和書卷氣。格非是個鄉下孩子,小學畢業以前基本都沒看過小說。但是格非的學養在我們這代人里一定是翹楚。我想跟你們說的是,實際上所謂先鋒文學、先鋒作家這些帽子里扣到的,是一些完全不一樣的人。你們再想一下莫言,莫言是個汪洋恣肆的作家,他的東西一點也不精致。我們這些人寫小說是很控制的,我們會把一個故事所有可能寫破的地方都盡量藏起來。我有時候甚至覺得莫言就是有那個本事,把一個指甲大的甲蟲放到臉盆那么大,那種雄渾那種力量。莫言后來的創作一直是非常大氣磅礴的。另外還有一個慢慢淡出大家視野,但前一段時間因為當街乞討重新被大伙注意的洪峰。洪峰是一個一直沉迷于世俗的“煩”和世俗的“樂”的小說家。他的小說里面永遠有一個在情場上春風得意的男主人公,永遠會有很多女孩子。洪峰寫過最好的一個中篇小說叫《講幾個生命創造者的故事》,他寫的是妻子生孩子的那一刻,特別精彩。
我給你們描述一下在這個大帽子之下扣到的作家,他們是一些特別不一樣的作家。但有時候歷史很無情,在這無情的歷史之下,我們就被這一頂帽子扣住了。“先鋒”在今天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在今天依然還有它不朽的意義。在它之后中國的文學開始呈現多樣化,而在它之前,從1979到1985年中國的文學非常非常單一。而在先鋒文學之后,我們知道有兩個巨大的流派,在許多年里面一直支撐著中國文學的整體面貌:一個是尋根文學。它基本上和先鋒文學是同時生成的,都在1985年。尋根文學里有一個特點,它聚集的都是成名作家,是成名作家對自己的寫作做出了改變。比如特別著名的“尋根”宣言的發言人韓少功,還有上海作家的大旗王安憶、北京作家鄭萬隆。他們改變了寫作的方向,讓自己的文學走進文化,使新時期前六年文學的單調輕薄得到了很大的補充;還有一個就是新寫實主義。里面有若干重要的作家,他們在后來十幾二十年的歷史當中都是舉足輕重的。主將有劉震云,他那時的名著有《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在當時影響大得不得了。也是寫日常生活,但是在方法論上有了長足進步;還有池莉,她在最近十幾年里差不多可以被列為暢銷書作家,她一直是被中國讀者閱讀得最多的小說家之一;還有另外一個武漢的女作家方方,她的寫作一直是腳踏實地,非常堅持,得到了許多同行的尊敬;今天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作家協會的主席劉恒,這也是一個風格獨具的作家,大家都知道他的小說《伏羲伏羲》改編成了張藝謀的電影《菊豆》。
從先鋒文學開始,中國文學呈現了豐富多彩的面貌,但是說老實話,這個面貌、這個80年代已經離我們的生活非常遠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文學慢慢地不那么熱鬧了。因為中國人的生活開始多樣化了,人們不再需要在多樣化的文學當中讓自己的生活豐富起來。他們直接把文學扔掉了:他們有電視可以看,有卡拉OK可以唱,有酒樓可以高談闊論,有地下賭場可以過過賭癮,有發廊可以讓那些想找樂的男人們開心。生活開始豐富,文學慢慢地離生活的中心遠了,慢慢邊緣了。
學生:我想問馬老師怎么看痞子文學和王朔?還有請馬老師點評一下賈平凹的《秦腔》。
馬原:如果讓我在我的文學經歷的這二三十年歷史中,說一個或者兩個最重要的文學家,我大概愿意說前期的北島和后期的王朔。在我們那個時代,詩人不是北島一個人。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個時候,北島的影響力之大是今天你們無論如何無法想像的。80年代中后期開始,如果說有哪一個小說家、文學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那么我以為王朔是最重要的一個。王朔個人的生活并不重要,他小說中關心的人群的生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從王朔開始開創了一個新的使用新語匯的歷史。王蒙在80年代末期有一次跟我聊起這個話題,他問你沒發現王朔的語言特別有力量?它會改變我們的生活。后來我就這個問題認真地想過不止一個回合。今天公司里的白領階層,他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聽上去特別像周星馳的語言,他們用《大話西游》、更晚近的《武林外傳》里的語言方式說話。他們的語言,包括周星馳電影里的語言都是從王朔那兒來的。王朔的語言是他在讀了我認為20世紀第一了不起的作家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以后形成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里面有一套語言體系,正話反話都以一個奇怪的腔調說。王朔的語言就是這樣,劉索拉也基本和王朔用一樣的語言說話。這個口吻非常奇怪,劉索拉有篇小說里有那么一個細節,小說里有個才女,單位領導給她一個任務,要她寫個什么什么歌詞,才女稀里嘩啦就寫出來了。她就是用一種特別瘋狂的語言方式,全是個人的、特別落拓不羈的、有點脫口秀味道的語言。領導說你這不是亂來嘛,這是什么東西?才女說這還不容易,你想要什么?領導就說我們要歌頌時代啊人民啊,才女就順手把每一個個人詞匯全換成公共詞匯,那個歌詞一下子就充滿了彈性,全是反諷。王朔的東西也就是那么一個東西。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影響了全世界,好像全世界的幽默都是約瑟夫·海勒教給大家的。不管王朔是和約瑟夫·海勒暗合,還是他可能根本都沒看過約瑟夫·海勒的小說,但他確實是運用約瑟夫·海勒的語言方式在說話。我個人以為王朔的語言方式影響了周星馳,而周星馳影響了我們很多人。
我個人特別看好《秦腔》。《秦腔》里沒有主人公,讓我想起前幾年得諾貝爾獎的西班牙大作家塞拉寫的《蜂巢》。《蜂巢》里就沒有主人公、沒有中心事件,寫的是一個群體的混沌,但是寫得非常的雄渾。我愿意把《秦腔》這種小說比作壁畫,壁畫就是沒有主人公的,個人不突出,但壁畫總是會給你恢宏之感、史詩氣息。
學生:為什么你們這些作家寫的作品,就我個人來看,還不及一部《紅樓夢》沉淀得多?看完你們的作品之后激發我寫作的欲望,還不及《亂世佳人》來得多?
馬原:我有一個勸告:別看活人寫的東西。死人的東西經過一代一代的時間的淘洗,那些渣滓、無用之物已經被淘掉了。《紅樓夢》已經經過了三百年,在這三百年里你知道要出多少書啊,一本《紅樓夢》卻能留下,仍舊是中國文學第一書。
學生:我是有這么一個意思:為什么以前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震撼力有那么強,而我們現在得到了他們那么多的東西卻還是寫不出那樣具有影響力的作品?是時代的力量嗎?
馬原:你自己已經回答了。實際就是時代的原因。那個時代是文學的時代,那時候文學多重要啊。那時人類有很多業余時間,孕育了那個時代的文學。今天的時代忙忙碌碌的,還談什么寫作啊,精力根本不可能集中。
你前面說的那話我不是特別贊同。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可能出現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不出《紅樓夢》,也許出部《金瓶梅》什么的。但是因為我們身在此山中,所以才不知廬山真面目。這要過三百年我們才知道,原來《岡底斯的誘惑》又是一部《紅樓夢》啊。
(錄音整理:陳蓓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