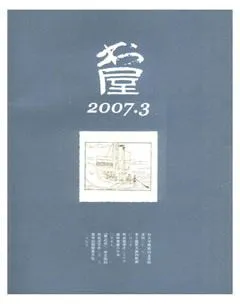現代文人的自創字
文字是勞動者創造的,它來自生產實踐與豐富多彩的生活,具有鮮明的符號特征與物象寫意的性質。但其中一些文字是由聰明智慧之士集中總結廣大群眾的集體創造,進行整理加工而首創的。
現代著名作家夏衍就創造了“垮”與“搞”字。1939年至1941年間,他在桂林主編《救亡日報》時首創這兩字,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我承認,這是我根據實際情況而試用的,但不久,這兩個一般字典上沒有的新字,就被其他報刊接受了。”時至今日,這兩個在《康熙字典》里查不到的字,已非同小可,幾乎成了萬能字,人們寫文章、說話總是少不了它們,《詞典》只好籠而統之地說,搞是做、干、辦、弄的意思。用得最多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會兒什么都叫搞,搞革命,搞運動,搞武斗,搞游行,搞大批評,搞生產,搞生活,搞一切事……
漢語詞匯中,“她”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是現代文學家劉半農(1891~1934)首創的。古代漢語中沒有“她”字,古代的詩詞歌賦小說中,第三人稱代詞是男女不分,一律寫成“他”。《水滸傳》第二十回有幾句話寫道:“那清河縣里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小名喚做潘金蓮……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里的“他”字,就是指潘金蓮。到五四時期,曾留學法國專攻語言學、著有《中國文法通論》的劉半農認為,白話文的興起,加之翻譯介紹外國文學驟增,第三人稱代詞使用頻繁,僅一個不分性別的“他”字是不夠的。于是,劉半農1917年在翻譯英國戲劇《琴魂》時,試用自己創造的新字“她”。隨后,為了表示第三人稱中性,又使用“它”字。另一個語言學家錢玄同在同一時期主張創造一個“女它 ”字來表示第三人稱女性,但沒有流行起來,倒是后來衍化為“伊”字。借用“伊”字來表示第三人稱女性的,在五四運動前后的文章常常出現。“伊’字本是古文字,通常表第三人稱,有時表第二人稱。
1918年,周作人在翻譯史特林堡《改革》的前記中說:“中國第三人稱代詞沒有性的分別,很覺不便,半農想造一個‘她’宇,和‘他’字并用,這原是極好……”,誰知這在當時文化界引起反響,有人支持,有人抨擊。為此,1920年6月,劉半農發表《“她”字問題》一文,刊于上海《時事新報》上。為推廣使用“她”字,劉半農1920年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后由趙元任譜曲,成為現代著名歌曲。
在魯迅小說《故鄉》中,寫到一種在海邊沙地里乘月偷吃西瓜的行動敏捷的小野獸,作者以“猹”字稱之。
在別處,人們從未見到過這個“猹”字,這是魯迅創造的字。魯迅一向告誡人們不要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語詞、字句。既然如此,他自己為什么要造出一個“猹”字呢?對此,魯迅曾作過說明:“‘猹’字是我據鄉下所說的聲音,生造出來的,讀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動物,因為這乃是閏土所說,別人不知其詳。現在想起來,也許是獾罷”(魯迅1925年5月4日《致舒新城》)。魯迅還造“女人”字,按魯迅意思,“女人”字指女性,如同“她”字指第三人稱的女性一樣,讀如“人”。魯迅還造“蟲遷 ”字,1923年,歷史學家顧頡剛認為夏禹是“蜥蜴之類”的蟲,魯迅不同意這種說法,他1927年5月17日在給章廷謙信中說:“查漢朝欽犯司馬蟲遷 因割掉卵秋而發牢騷……”意思說,如果夏禹是蟲,那么司馬遷也是蟲了,故在“遷”字左邊加“蟲”旁,以諷顧頡剛。
有一種說法,“烤”字相傳為齊白石所造。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清真烤肉苑”飯館請畫家齊白石題字,齊白石想寫“烤”字,可是當時字典上只有“烘”、“考”,他想到烤肉要用火,就想出一個“烤”字。他擔心遭人非議,就在“烤”字下面寫一行小字釋道:“諸書無烤字,應人所請,自我作古。”其實,這說法不夠全面,“烤’字確實未編入《說文解字》、《廣韻》、《集韻》諸書,但是1991年《漢語大詞典》首次指出了“烤”字始見于乾隆抄本《紅樓夢》第四十二回:“對粗磁碟子之類‘不拿姜汁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至齊白石題匾時“烤”字已有一百多年歷史了。
現代著名作家胡適(1891~1962)也創造了一個“ ”字。胡適是安徽績溪人,是白話文倡導者。據現在上海大場醫院耳穴專家、胡適的侄兒胡地松回憶,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胡適到上海河南中路一百八十四號“胡開文發記筆墨店”看望堂兄胡洪發(1891~1973),他喜歡胡洪發小兒胡地松,問胡地松“長大之后做什么?”小胡地松說“當醫生”。胡適很高興,當場教他識一個“ ”字(安徽績溪音讀“鹿”),并接著說:“這個字拆開來叫門內狗,只會在門里逞兇,到外面就不行了”,他教侄兒長大要做一個有用的人。然而,這個“ ”字沒有流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