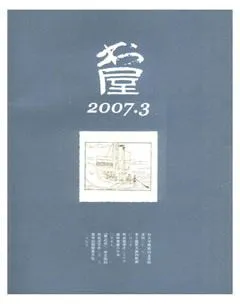孔夫子何需洋人撐腰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學者在談到中國傳統文化時,屢屢提到一件事,說是“全世界七十五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于1988年在巴黎聚會,討論新世紀世界的前途,他們竟然得出了一致的結論,認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如果要過和平幸福的生活,就應該回到兩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孔子那里尋找智能”。說實在的,盡管我對諾貝爾獎的獲獎者們敬佩得五體投地,但他們之中有幾位真正拜讀過《論語》,實在讓人拿不準,因此,我對那個結論總是將信將疑的。
近來翻檢舊書,偶然間在1997年第1期《讀書》上讀到李慎之先生的《諾貝爾與孔夫子》一文,原來李先生于此說早有所聞,但又對之放心不下,他不僅拜訪了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還托人從國外圖書館找來了法文的《世界報》,查對的結果,還真的開過那么一個會,而且“議題也確實是‘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和希望’,但是會議并無什么最后宣言……會上根本沒有提到孔子,甚至連中國也沒有人提起”。不單如此,李先生對當時盛傳的美國西點軍校掛雷鋒畫像一事也不放心,他就此事詢問了在那里教書的中國教授,答復是“沒有聽說過”。這樣的結果實在叫國人感到臉紅心兒跳。
如此這般現代神話何以會于當今之世,在講究仁、義、禮、智、信的中國產生幷且糊弄了許多人?這實在是件令人深思的事情。李慎之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好像到現在還沒有擺脫一種心理,一個人、一件事或者一樣商品好像只要得到洋人的夸獎或者起一個洋式的名字就覺得臉上有光”。他這是以崇洋心理來解釋,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我覺得,這恐怕還是一些人骨子里的阿Q基因在作祟。
長久以來,中國的讀書人多少都還殘存有一點天朝上國的心態,可是在近代史上卻偏偏又是中國吃虧的時候居多,于是形成了“崇洋”和“仇洋”兩種心理。“崇洋”一端人人皆知,略而不論。至于“仇洋”心理,魯迅說得極明白:“因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從孩子照相說起》)。也許,那些創造了諾貝爾獎得主們驚人結論的人覺得,中國的“四大發明”還只是物質層面的東西,不夠份量,干脆一幷通吃,連精神領域也拿下:如果沒有我們二千多年前的圣人所開出的濟世良方,則人類將熬不過二十一世紀!我認為,這無非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世界版而已,讓人禁不住想起阿Q的那句口頭禪:“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
照我看來,在這件事情上反映出來的阿Q精神,其實是崇洋與仇洋兩種心理的混合物。他有二進制算法,我早有陰陽之說;他有機器人,我有木牛流馬;他提出環境保護,我早有“天人合一”之說……總之,不管這世界上有什么好東西出來,對不起,我這里古已有之,正所謂“萬物皆備于我”,以不變應萬變,其奈我何?崇洋和仇洋都是缺乏理性的表現,絕非健全的國民心態,于民族振興毫無益處。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講真話原是學者的本份,也是做人的根基,愛國主義、民族自尊和群體認同只能建立在牢靠的地基之上才會穩固,任何假話、大話、空話都無濟于事,而只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孔子思想的精華在當今世界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這說明它確實具有跨越時代和國界的價值,完全用不著拿幾個外國人來替孔子撐腰。也許,只有到了跟阿Q揮手告別之日,才是我們民族真正振興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