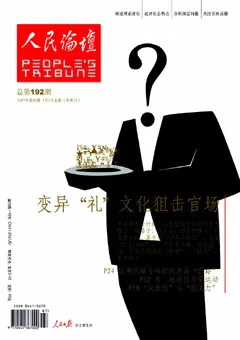三問“人情往來”
“年關易過廉關難”的現象在當今我國的政治生活中確已形成了一定的氣候。每到春節臨近,這種現象就會周而復始地提到我們面前,成為不可治愈的官場頑疾
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獄中所寫《我的罪行與反思》講到,他在沈陽市任職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級各類干部,每逢年節,大事小事,以各種名義送錢送物多達600余萬元。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把這種送禮行為看作是“人情往來”而坦然待之,直到事發。調查統計,相當一批出問題的領導干部平時尚能自律,但是節日期間則以“人情往來”而放松警惕,最終走上違紀違法的道路。為此,引來如下三問:
問一: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與民間的交往風俗不同在哪?
誠然,從表面現象上看,領導干部和普通百姓一樣,同為血肉之軀,也擁有七情六欲,利用新春佳節享受人之常情,本來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領導干部和普通百姓的最大的區別,就是他們手中掌握著決定他人命運的公共權力。這決定了一些人在年關期間針對領導干部開展的交往活動與一般百姓之間的交往風俗有著根本的區別。
其實,權衡一下二者之間的差異,最起碼有兩點:一是交往目的大相徑庭。普通百姓之間相互走訪互致問候,恭賀新禧。這其中透出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純情和健康,目的非常高尚。而一些人在年關針對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則透出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功利和頹廢,目的則比較庸俗。二是交往方式大為迥異。普通百姓之間相互走訪時略帶薄禮、講究君子之交淡如水,禮輕情義重;而一些人在年關針對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則出手闊綽,少則數千,重則數萬,當然這些錢極少出自自己的腰包,多數是公款送禮。僅僅有此兩條,就可看破這種交往的實質,無非是利用春節這個全民族的節日,借雞下蛋,搞權錢交易。
問二:何以總有人熱衷于對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
近年來,一些人在年關期間針對各級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之風愈演愈烈。對于現代官場上這種“人情往來”的時間源頭,因為沒有這方面文獻做過專門記載,無從考證。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這種現象的深入分析,因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并不復雜。剖析一個案例即可發現,“人情往來”中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方是領導干部,因為他手中掌握著控制各種稀缺資源的公共權力,因而他是“供方”;另一方是有求于該領導干部的人,因為他需要領導干部掌握的稀缺資源,因而是“求方”。從這兩個方面的情況來看,“供方”控制著稀缺資源,“求方”希望獲得這種稀缺資源,而這個目的的實現,必須獲得“供方”的認可。因而,他們之間實際就形成了一種供求關系。按照價值規律,只要存在供求關系,就意味著一種交易發生的可能性。毫無疑問,這樣一種供求關系的大量存在,是這些年來這樣一種特殊的“人情往來”產生的深刻動因。
問三:熱衷于對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何以成風?
僅僅有單純的供求關系,還不足以使這種“人情往來”形成氣候,因為這種供求關系的存在,只是為交易提供了可能性,這樣一種可能性最終變成一種風氣,還得需要合適的外部條件。
實際上自從公共權力產生以來,這樣一種供求關系就在所有的政治生態中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國家、所有時期都大量地存在著這樣的人情交易。在我國,近些年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特殊的政治現象。癥結在于:
其一,領導干部掌握了高度集中的公共權力。在熱衷年關送禮的人群中,有人是出自謀取經濟利益的,企圖通過領導的“權力庇護”,打通審批等關節,以小錢換大錢,取得更可觀的經濟回報;有人是出自謀取政治利益的,希冀博得領導的“權力好感”,以便日后在官職上能得到更快的升遷;還有的想得到領導的“權力照應”,謀取方方面面的社會利益。總之,不同人都希望在領導干部那里獲得稀缺的資源。
其二,領導干部所掌握的權力得不到切實有效的制約。法制完善的國家,一方面權力高度集中問題不像我們這樣普遍,另一方面即使是高度集中的權力也受到了嚴格的制約,健全的法治使得官員所掌握的權力受到嚴格的制約和監督。而在我國,由于當前法治不完善、不健全,還沒有形成一套嚴格的權力制約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僅僅靠領導干部的黨性覺悟和道德修養是靠不住的。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下,由于我們不能從體制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和權力制約乏力的問題,一些人針對領導干部的“人情往來”就會在年關找到合適的時機恣意生長,最終形成一種風氣。
基于以上認識,筆者認為在年關將近的時候,我們利用傳統的教育和懲治方式來加以治理未嘗不可,但是要從根本上杜絕這樣一種風氣,還必須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狀,建設完備的法治,只有這樣,才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