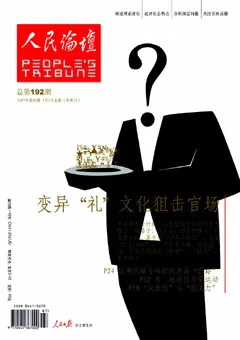何止一個“難”字了得

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利益多元化的發展,逢年過節之“禮尚往來”,漸漸地有些變味。同時也變成了許多下屬與領導的痛苦,這實在是禮儀初創者匪夷所思的問題
年關送禮:難字當頭
就不當目的送禮者與正當送禮者來說,對于送禮的感受是不同的。對于不當目的者來說,年關是其公關與攻關的絕好機會,巴不得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一年365日,天天都過年該有多好啊!對于真誠的送禮者來說,送禮是其美好情感的表達,并無絲毫的瑕疵與雜念。但是由于有了前述情況的存在,真誠的送禮者也往往會擔心自己的美行被誤解,也難免會被誤解。這對于真誠的送禮者來說,是極其殘忍的,因為,他們要尋找一個表達自己感激與感謝的機會也不易。好不容易等到了春節,又被那些不良分子給玷污了。自己美好的送禮行為也許會被誤解為行賄。高尚被誤解為低俗,這對于高尚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侮辱與傷害,甚至還可能衍生出恥辱感與恥辱。
就不良官員與廉潔領導來說,對于受禮的感受也是不一樣。那些極端的不良官員不惜以權弄法,平時都會以權謀私,到了年關,甚至也許更期望在年節的掩護下,更好地收受禮物,中飽私囊。因為年關對于他們來說,它的到來相當于斂財機會的到來。對于廉潔官員來說,年關也許是他們對于親情與友情的重溫,也可能是一場不大不小的考驗。他們既希望年關帶來友誼與親情,他們也多么希望永遠沒有年關啊。沒有了年關,他們就沒有了是否接待年節送禮者的痛苦。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態,是其他人所難以體悟的,廉潔的領導無不為之而頭疼。
年關的禮尚往來,對于下屬與上級來說,也是一個難題。這對于誠心要送禮的下屬來說,并無什么問題。對于本不想送禮的下屬來說,則是一件十分為難的事情。在年節,許多同事都去給領導送禮了,如果自己不去,多少總覺得有些另類;如果自己去了,總覺得有些別扭。去吧,違反自己的本意;不去吧,又擔心領導以為自己不給面子。社會上早就有趣語調侃說有的領導“不知道誰送禮,但知道誰沒有送禮。”送不送禮,對于不想送禮的下屬來說,難啊!
對于上級來說,也一點不比下屬輕松。下級說要趁節日來看看自己,歡迎吧,有故意收受禮物的嫌疑;拒絕吧,又有不給面子,脫離群眾的嫌疑。下屬送來禮物,不收,不給面子——不識抬舉;收下又總覺得不舒服——拿人手軟啊,而且還冒著收受賄賂之大不韙。其實,對于優秀的領導來說,收受這種禮物,只能是心理負擔。將廉潔者收受親屬、朋友、上下級完全出于情感而送來的禮物為受賄,簡直可以說是對他們的污蔑。然而誰又能完全分清其中的高潔與庸俗?
跳出困境:改革是唯一的選擇
既然年關送禮,對于下屬難,對于領導也難,可不可以不送不收?從邏輯上講是可以的,但是實際上則是不可以的。因為,年節畢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一年才一次啊。有的群眾會說,我不是要給領導送禮,而是要對領導表達我的心意,難道不行么?的確誰都不能說不行。領導說我不收貴重的,只收心意行么?也不能說不行。行賄不行,表達情感當然毫無疑問。年關啊,原來就使人那么難。下屬難,領導難,下屬與領導都為難。送禮或是不送,下級上級都為難。怎么辦?是送還是不送?如果同意送心意,什么又不是心意?多少數額以上是賄賂,多少數額以下不是賄賂?不同的主體,感受是不一樣的。
靜心一想,以上的種種想法都未必是錯的。我們僅僅是在現行不良狀態之下的思考,其實,我們沒有必要固守現有的狀態。因為現有的狀態就是不合理的。于是改革就成為了我們唯一而必然的選擇。然而改革又從哪里做起呢?
我們不妨追問送禮行賄者的目的何在?其目的顯然在于通過有權者權力的濫用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權力不能被濫用,還會有人通過送禮來行賄么?一定不會有。
關鍵在于權力必須依法行使。權力一旦嚴格依法行使,行賄者就失去了動機,真正以送禮表達感情與感謝者也有了正大光明的形象,而不至于隱晦于行賄嫌疑之中;受禮者也冠冕堂皇,而無受賄嫌疑之累。
何以使權力被嚴格依法行使,辦法只有兩個,直接的是法治,根本的是民主。法治是直接的決定力量,民主是最終的決定基礎。只有有了真正的法治與民主,權力才不可能被濫用。權力不被濫用,任何行賄就喪失了意義。這時,中華民族作為禮儀之邦、禮尚往來的美德,才可能真正成為完全的美德,而不被邪惡“假汝而行”。年關易過,廉關也易過。(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副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