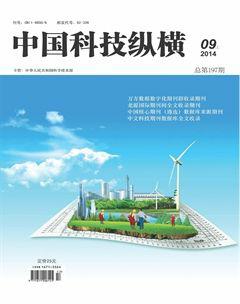天然藥物在現代醫療保健中的地位和作用
郭婷
(渭南職業技術學院,陜西渭南 714000)
天然藥物在現代醫療保健中的地位和作用
郭婷
(渭南職業技術學院,陜西渭南 714000)
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人類認識疾病、治療疾病的能力越來越強,但是這些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疾病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現代醫療保健要求人類對待疾病要從以前單純的治療疾病發展成為集疾病預防、治療、保健和康復為一體的醫療保健模式。而天然藥物在現代醫療保健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從天然藥物是研制新藥的主要途徑之一、天然藥物是現代新藥的重要成分天然藥品推動著營養類藥品的發展這三個方面闡述了天然藥物在現代醫療保健中的地位和作用。
天然藥物 現代醫療保健 地位 作用
制藥工業是人類歷史上開發的最偉大的工業項目之一,其誕生100多年來,研制出了大約500種新藥,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雖然人類治療疾病的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目前已經發現的疾病有3000多種,其中僅有三分之一的疾病可以用藥物完全治愈。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工作壓力不斷增大,一些疾病對人體的影響將會更大,比如患精神類疾病、心腦血管疾病、循環系統疾病、代謝系統疾病等疾病的人越來越多,甚至逐漸成為常見疾病之一。疾病譜的改變要求人類的治療理念也應當隨之而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回歸自然”。
1 天然藥物是研制新藥的主要途徑之一
大自然中的各種生物是人類研發新藥的基礎。歷史告訴我們從化學和生物學的角度對天然生物進行研究,可以發現許多臨床上有用的藥物原型;發現許多具有開發前景的新型化合物,通過對它們的結構進行優化可以更容易發現新藥。比如歐洲民間采用草藥水飛薊治療肝炎,后來通過醫學分析,成功分離出了具有保肝護肝作用的水飛薊素。瑞士山德士制藥公司通過對鬼臼毒素的研究,成功開發出了治療小細胞肺癌的足葉乙甙和治療腦癌的足葉噻吩甙兩種抗腫瘤藥物。該公司還系統的研究了麥角生物堿,從歐洲的麥角中成功分離出了麥角胺和麥角新堿,并對天然麥角堿-麥角隱亭進行了溴化,成功研制出了治療由于高泌乳素血癥導致的閉經、乳溢綜合征的有效藥物溴隱亭;美國的NCI(國立腫瘤研究所)從短葉紅豆杉這種植物中成功提取出具有抗癌作用的活性成分紫杉醇,從而成功開發出治療各種實體腫瘤的新藥Taxol。上述這些事例都充分說明大自然是天然的藥材寶庫,天然藥物是研制新藥的主要途徑之一[1]。
2 天然藥物是現代新藥的重要成分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有一半左右的臨床用藥來自于天然產物及其衍生品。而天然藥物更是全世界八成以上人口醫療保健的基本資源。根據美國《藥物化學年報》統計顯示,2000n年到2010年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生產和批準用于臨床的抗癌類藥物有六成以上來自于天然產物。其中包含天然產物,天然產物的半合成品以及全合成品。除此之外,有關機構對全球銷量最大的幾家制藥企業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多數公司都是以天然產物為基源研究新藥的。
據媒體報道,近些年全世界一共成功開發出124種新植物藥,其中有41%的新藥是以單一植物的提取物為主的,25%的藥以單一天然化合物為主,10%的藥是以多種植物的提取物為主要成分的。8%的新藥是復合天然化合物,5.5%的為原植物粉末。
而我國古人更是利用天然藥物發展形成了中醫,隨著現代醫療保健的發展,中醫以其天然、毒副作用小的特點贏得了更多的關注。
由以上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雖然現代制藥工藝融入了許多現代科技元素,但是無論現代制藥水平怎樣發展,它都離不開天然藥物,任何一種新藥都是在對天然藥物研究的基礎上,從中提取出對某種疾病有治療效果的成分,并進行化學或者生物學的加工、處理從而變成藥品。換言之天然藥物是現代醫療保健的根,離開了天然藥物,現代醫療保健將無從發展[2]。
3 天然藥品推動著營養類藥品的發展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關心營養和養生。具我國有關部門預測到2020年我國營養保健類商品的銷售額將達到6000億元人民幣,面對這樣的龐大的市場許多制藥企業都紛紛進軍營養保健市場,想從中分一杯羹,而傳統制藥公司進入營養保健市場的首選切入點往往是天然產品。比如美國強生公司進入營養藥品市場便是通過子公司McNeil買斷芬蘭艾瑞斯特公司的一種飲食成分油醇酯(一種抗膽固醇成分,主要用來制造人造黃油)而成功進軍該行業的[3]。
而我國企業更是以一些天然中藥材為原料進行加工,做成營養品或者保健品。比如安神補腦液的主要成分就是鹿茸、干姜、大棗、甘草等天然藥品[4]。
由此看見天然藥物不但是現代醫療保健的基礎,更對現代醫療保健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營養品、保健品的發展更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4 結語
大自然中的各種生物都是現代醫療保健重點研究的對象,通過對自然界中動植物的研究,可以從中發現許多具有藥用價值的成分,現代大部分藥品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天然藥物。所以說天然藥物是現代醫療保健事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離開了天然藥物,現代醫療保健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于此同時天然藥物對現代醫療保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以上就是筆者對天然藥物在現代醫療保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些看法,希望對現代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有所幫助。
[1]王普善.天然藥物在現代醫療保健中的地位和作用[J].精細與專用化學品,2012,05(07):25-33.
[2]張衛東.中藥現代化研究新思路——天然藥物化學與生物學研究相結合[J].中國天然藥物,2013,04(05):18-22.
[3]任原樂.天然藥物:為人類經營健康[J].粵港澳市場與價格,2014,02(04):11-15.
[4]史清文,李力更.天然藥物化學學科的發展以及與相關學科的關系[J].中草藥,2013,03(06):17-20.
渭南師范學院資助項目(12YZK063)
郭婷,女,陜西渭南人,寧夏大學研究生,渭南職業技術學院教師,助教。研究方向:天然藥物研究與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