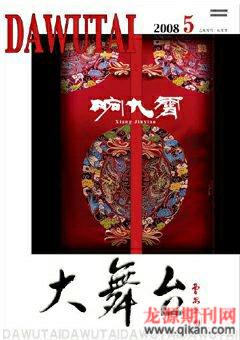淺論“四神”瓦當與秦漢設計思想
田 蕾
【摘要】“四神”瓦當是秦漢時期的藝術瑰寶,它自由奔放、氣勢磅礴,千百年來煥發著永久不息的藝術魅力。它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哲學思想與秦漢“大”、“和”設計理念所指導下的經典之作。本文通過對“四神”瓦當選材、造型、構圖的具體闡述,從而揭示“大”與“和”的秦漢設計思想。
【關鍵詞】四神 “大” “和” 設計思想
瓦當,是秦漢時期就被應用在建筑屋檐頂端的蓋頭瓦。班固《西都賦》曰:“裁金以飾珰”,釋“珰”為“椽頭飾也”。①可見,瓦當除了防雨、束水以及固瓦護檐的功能外,具有統一屋面的裝飾作用,它是古代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整個建筑裝飾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神”瓦當是漢代瓦當的代表之作。它以想象中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騰為題材,通過巧妙的構思,細膩而不繁瑣的線條勾勒,將漢代質樸渾厚、自由奔放、氣勢磅礴的藝術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極富浪漫主義色彩。
公元前221年,“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秦朝。秦漢統一后,為了使皇權能得到鞏固,統治者利用神權來鞏固其政治統一,建立神學經學,提倡“天人合一”的神學目的論。②由于人們無法抗拒和解釋許多自然現象,無法對付自然災害。加之統治者提倡“天人合一”的神學目的論,人們理所當然認為,人自古都要投身自然,崇尚自然。宇宙是無限的,力求與自然相融合,即“天人合一”。表現了人們追求內在統一和順應大局的思想。在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秦漢的設計思想體現出了一種“大”與“和”的設計觀念。這種思想是注重客觀事物的整體性、形象性、朦朧性、大而化之,是從宏觀角度來看世界。對客觀對象并不作窮根究底的分析和思辨,而是用一種整體的、大而化之的描述方式來形象的展現。在這種設計觀念下“四神”瓦當成為當時建筑廣泛應用的裝飾題材之一。也可以說,“四神”瓦當是秦漢設計思想的產物。
一、選材與秦漢設計思想
“四神”題材的選擇與秦漢的設計思想有著莫大的聯系。“四神”瓦當的題材是由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想象中的圖騰組成,分別施于東、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殿閣上,代表著東、西、南、北四方,又代表著春、夏、秋、冬四季和青、白、赤、黑四色。它是祥瑞的象征,是秦漢人祈求保佑的神靈。
青龍,是我國人民心中一個威力巨大無比,善于變化,能興雨雷而“利于萬物”的神意動物。漢代劉向在《說苑·辨物》中說“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也,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乎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③可見,龍是變化莫測世間所沒有的神性動物,它綜合了飛禽走獸及其它動物最突出的特點,經過創造性藝術加工而塑造的,它寓意著威嚴、勇猛和智慧等等。另外,由于當時生產力和科學水平低下,人們無法解釋許多自然現象,無法對付自然災害,于是對董仲舒宣揚的“天人感應”學說大為迷信。④君權成為神授之意,皇帝也即成為天子,天子是龍的化身,具有與龍一樣的“權力”。于是“龍”自然而然地也就帶上了強烈的皇家氣象,具有“皇權”之意義。
朱雀即鳳,也是人們憑想象創造出來的形象。在創造時以雉雞、孔雀等鳥的形象為原形。《說文》云:“鳳,神鳥也……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⑤“出于東方君子之國”說明“鳳”代表權貴,而“見則天下大安寧”表明了“鳳”預示著祥瑞,平安。“鳳”形象的出現即表明當時人們對和諧社會生活的祈盼。
總之,“龍”與“鳳”分別代表著“權力”與“富貴”,是當時人們崇尚和膜拜的對象,也是皇權的象征,理所當然成為創作之首選。因此可以說,從自然萬物到想象圖案“龍鳳”,到社會之“權貴”,再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無不體現秦漢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大”的設計思想。“大”的設計思想——即天地人整體思考狀態下的設計。整體性包含著由人到社會、由人到自然、由人到環境無限“大”的思想。
白虎,指白色的虎,白虎少見,故物以稀為貴。東漢王充在《論衡·物事》中說:“或問風何從虎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⑥虎具陽剛之氣,人們認為它能“直搏挫銳,噬食鬼魅”,并將這種被擴大和神化了的威力賦予了虎的圖像,使之成為守衛門戶的神獸。玄武的形象為龜蛇合體,正中為一龜一蛇,龜匍匐爬行,蛇蜷曲蟠繞于龜體之上。玄武為北方七星宿的總稱,包括斗、牛、女、虛、危、室、壁以形如龜而得名。雷圭元先生在《四神紋》一文中談到玄武時說:“對于玄武圖的出現,有研究者認為要從原始社會的圖騰信仰和氏族制度中求解釋。……龜蛇相交的玄武圖,可能就是寓有龜氏族與蛇氏族通婚的意思。后來,用龜蛇相交的圖像表示生殖。”⑦
可見,“守衛門戶”的白虎與“表示生殖”的玄武,淋漓盡致的表現了人們的美好愿望與追求。這種“愿望與追求”與“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影響下的“和”的設計理念相吻合。“和”要求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密切相關,融為一體。因此,“和”所指導下的圖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它物化了人的美好愿望與理想,融入了情與理、意與趣,達到了一種神韻美的境界。
二、造型觀念與秦漢設計思想
“天人合一”表現了中國人追求內在統一和順應大局的思想,這種思想在造型藝術中體現出了一種“大”的設計理念。這種思維方式并不對對象作一種窮根究底式的分析與思辨,而是用一種籠統的描述方式將對象形象地展示出來。
青龍,是由飛禽走獸及其它動物最突出、最富寓意的特點經過創造性的藝術加工 “綜合”而成的,其中包括蛇身、鹿角、虎眼、牛耳、劍眉、鷹爪、獅鼻、金魚尾、馬齒等等。漢代許慎《說文》云“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巨能細,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⑧可見“龍”是變幻莫測,人間所沒有的。朱雀,是各種飛禽與動物的綜合。《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前鹿后,蛇項魚尾,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由此可見,“鳳”是“綜合”鹿、蛇、魚、龍、虎、燕、雞最突出的特點經過藝術塑造而成的。龍與鳳的這種“綜合”都是在“大”的設計思想指導下完成的,使得造型既大膽又巧妙,雖然違反了生物的生理規律,但符合藝術的創造規律。然而,創造出的形象又是客觀世界所未有的,但其每個部分又源于自然界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是整個自然界事物的概括,是超于現實之上的新生命,這都得意于“大”的設計思想。
“白虎”雖沒有經多種動物的“綜合”。但在造型藝術上,也脫離了現實。為了使白虎更具陽剛之氣,頭部與尾部稍作了“夸大”處理。“玄武”紋中“蛇”的造型顯然脫離了日常生活中蛇的模樣,不僅給蛇添加了“羽”和“足”,還添加了與鳳相似的“尾”。添加浪漫色彩之余,讓它多了幾分神氣。這種藝術處理是在“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影響下,創造者既遵循自然事物之規律,又超越于客觀規律之外,而發己之肺腑,是從“物”與“我”兩方面整體全面的考慮,從而創造出秦漢設計思想下的經典之作。
綜上所述,“四神”紋的造型之所以唯美,是與秦漢哲學思想“天人合一”指導下“大”的設計思想有直接聯系的。這種海闊憑魚躍的宏大而寬廣的思維方式,體現了整體性、形象性,展示了東方特有的文化和獨特的思維方式。
三、構圖美與秦漢設計思想
“四神”瓦當的成功,不僅得益于它的造型美,構圖之美也是功不可沒的。秦漢時期,瓦當的形狀有半圓形和圓形兩大類,但圓形瓦當在秦漢時期占了重要地位。“四神”瓦當的形狀就是圓形。除了瓦當形制是圓形,里面圖形的構圖也是圓形。為什么秦漢時期的人們對圓形情有獨鐘呢?眾所周知,很久以前,古人就認為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即中國最基本的“圓”與“方”的圖形概念——“天圓地方”。“天圓地方”中的“圓”象征著天,代表著乾,是陽性和陽剛;方象征著地,代表著坤,是陰性和陰柔。這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思想,表現了人們力求與自然相融合。相比之下,人們更喜愛“圓”,常常用“圓滿”、“團圓”、“團聚”來表現他們的希望。這種“圓”也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認為事物是周而復始的運動變化,宇宙萬物的興盛與毀滅都呈現“圓”形軌跡。這與“天人合一”影響下“和”的設計思想相吻合。強調人與自然相互之間是聯系的,因果循環的,體現了濃厚的生活氣息。
“四神”紋的構圖美,先從姿態在圓形瓦當的位置說起,“四神”的頭部分別在“圓”形的左上側;“足”部都統一的“扒”在“圓”形瓦當的左下側與右側,其余均勻地站在下側;龍身、虎身、鳳身、以及龜身占據在“圓形”瓦當的重要位置—中下側;它們的尾部翹起居右上部位。由此可見,姿態相當的“四神”體現出構圖中的整體統一美與協調美。再從單個的特征來看,龍、虎兇猛的“足”與鳳、蛇蜿蜒的“足”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龍身、鳳身的鱗片紋與白虎的幾何紋、龜身的紋飾各不相同,對比鮮明;鳳獨特的“羽”與玄武是龜、蛇纏繞的“組合”都顯得與眾不同。這些都體現了對比與協調、節奏與韻律之美感。
姿態與特征無不體現著構圖美,體現著中國最古老的形式美法則——對立與統一、對比與協調、節奏與韻律、動與靜、黑與白、疏與密、虛與實、大與小、局部與整體。而這種形式美法則直接來源于傳統的哲學思想——“天人合一”與“大”與“和”的設計思想。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從“四神”瓦當的選材、造型、結構無不體現著宏觀整體性“大”的設計思想與人和自然融合協調“和”的設計觀念。可見,“四神”的出現與秦漢“大”與“和”的設計思想是緊密相連、水乳交融的。亦即是說,在秦漢“和”與“大”的設計思想指導下,成就了經典的“四神”。我們必須繼承古人積累起來的藝術設計思想,進而推陳出新,創作出既能弘揚民族文化,又富有創意的優秀藝術作品。
注釋:
①鄭軍《漢代裝飾藝術史》,山東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第124頁.
②任繼愈《中國秦漢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第4頁.
③⑧鄭軍《漢代裝飾藝術史》,山東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第130頁.
④王荔《中國思想發展簡史》,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10月第84頁.
⑤賈經生《“尚象”—中國傳統圖形設計思想的價值》一文,引自杭間、何潔、靳埭強著《中國傳統圖形與現代視覺設計》,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1月,專文.
⑥鄭軍《漢代裝飾藝術史》,山東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第131頁.
⑦鄭軍《漢代裝飾藝術史》,山東美術出版社,2006年9月第134頁.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