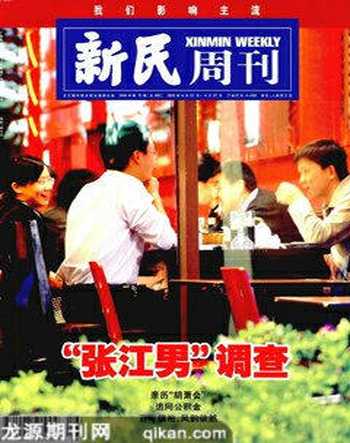顧曉鳴:“批判”張江男?
金 姬

張江男現象是一種現代產業病?
雖然“張江男”遠離傳統意義上的上海中心城區,但中心城里的一些學術名人似乎對他們早有印象。比如,對浦東和張江高科技園區的發展頗有研究的復旦大學歷史系顧曉鳴教授,就“固執”地認為“張江男”現象是一種現代產業病,我們的談話從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開始。
記者:我采訪的部分“張江男”自己也承認,他們干的是看似腦力活的體力活。這讓我想起卓別林1936年的電影《摩登時代》中的情節:卓別林自如地穿梭在機器中間,不停地在擰螺絲,擰啊擰,在他眼前除了螺絲,別無他物,人成為流水線的一個部件。
顧曉鳴:的確,張江高科技園區還沒形成自身的文化。“張江男”與《摩登時代》中的人物很相似,只不過以高科技方式重現罷了。而高科技產業內部更加細分,像“張江男”那樣的技術人員,如果只是做生產流程的一個部件,別無所長,人生被鑲嵌到一個MATRIX(矩陣)里,如果自己又不自覺,很可能就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廢棄的生命”,這在發達國家已作為理論問題提出來了。
記者:我和“張江男”接觸后發現他們都很優秀,也很善良,您的這種說法讓我有些難以接受。
顧曉鳴:我理解你的心情。年輕的“張江男”普遍都很單純,但其實這是從學校到企業“短路”過程中造成的幼稚。而張江作為集中的科技園區,遠離完整的社會生活和都市環境,這些人在其中往往過著長不大的生活。沒有足夠的社會交往讓他們去獲得應有的的個人經驗,他們也無法融入復雜的城市生活。工作和生活融為一體的簡單生活,科技上的追求和競爭,使他們無法體驗人生深層次的需求。“數字鴻溝”的說法已經廣為人知,我覺得“張江男”現象的產生,是“生活知識鴻溝”的一種體現。
記者:何為“生活知識鴻溝”?
顧曉鳴:我是指現代人生活知識的匱乏造成的人際落差。當一個人缺乏美學教育時,他就不能真正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也無法產生更深層次的追求。同樣,生活的能力、激情、趣味也需要有復雜的機制養成,如果在人生環節中缺了這樣的養成過程,“張江男”就有可能成為“IT動物”,他們既缺乏享受生活的時間,也對生活樂趣很無知。他們的生活圈子窄了,便逐漸會產生了惰性。“張江男”也許會懶得去認識女孩子,或是懶得去參加活動,似乎電腦滿足了他們所有的需求,其實這是一種“身心無能”的表現。
記者:您似乎在批判“張江男”?
顧曉鳴:我只是對這一現象做出一種解讀,我們更不可以把在張江工作的人武斷地概念化為“張江男”。我認為我們現在所說的“張江男”,是特指或多或少患有社會自閉癥的高智商、低社會能力的人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缺乏與社會的接觸,導致這批高學歷人群人格情感缺失,從而又對社交產生恐懼感,造成他們木訥和粗糙的個性。這樣的男孩子并不招女孩歡迎,即便他們收入不錯。也就是說,“生活知識鴻溝”導致情感體驗鴻溝,再引發人際交往的障礙。
記者:您認為“張江男”現象的起因是什么?
顧曉鳴:我認為“張江男”現象,是學校教育、企業文化以及兩者之間的橋梁出現問題的綜合結果。我們目前的應試教育體制,以分數掛帥,極大限制了學生對全面生活的參與和感知,導致大批高學歷人才不懂生活。而我們的企業或迫于競爭,或管理觀念陳舊,從而缺乏人文關懷,有意無意地把人才僅當作工具。我在MBA講課時,一直主張企業內部的HR(人力資源)應該改為HD(人力發展),前者感覺是在利用這份“資源”,而后者更是考慮到了人才的自身成長。
此外,像類似張江地區的企業,都是智慧密集型企業,高薪職位也帶來了人與人的區隔和壓力。這批高學歷的“張江男”如果在企業的層級中沒有發言權,他們的高強度工作在磨去他們棱角的同時,也在鈍化他們的青春活力。張江建立高科技園區已有16年了,我們現在關注“張江男”這一特殊群體還來得及。
記者: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顧曉鳴:其實美國硅谷自上世紀70年代發展以來,那里也有類似的“硅谷男”現象。美國30多年來都沒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也是一種“資本的異化病”。但我們可通過使學校教育和企業文化相銜接,尤其通過創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技園區文化;同時,為年輕知識員工創建“生活知識補償”環節,從而對處理現代化過程中的人和人才的問題,作出更有深度和前瞻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