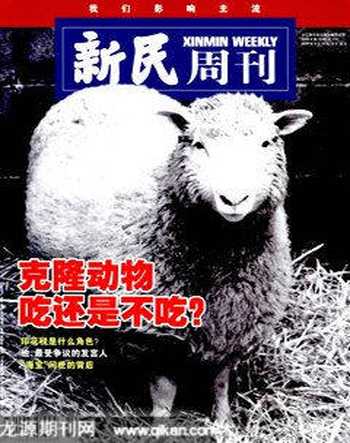調控難題:寰球不同涼熱
汪 偉
太平洋此岸對過熱的“調控”一波接著一波,彼岸卻是憂愁“衰退”的悲聲不斷。
因為6次加息和10次提高準備金率,2007年被稱作“加息年”。很多經濟人士預測,央行在2008年將繼續加息,至少加息3次,以應對市場上的流動性過剩。
2008年1月的CPI數據達到11年來的高點——7.1%,通脹的勢頭不減,似乎證明2007年的預測果然沒有過時。然而,春節之后,質疑加息的聲音已經隨處可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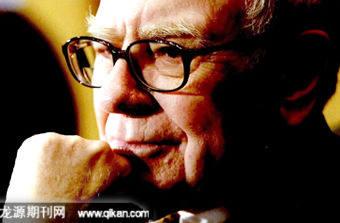
雪后看經濟
雪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明朗化。初步統計,雪災波及10省市,造成了129人死亡,4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1516.5億元。
從目前宏觀經濟的局面來看,消化雪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并非難事。在過去的4年中,中國經濟的主題是強勁的增長,一次雪災,即使是罕見的,并且發生在中國經濟的中心地區,似乎也難以阻擋增長的勢頭。但雪災帶給人們的真正的警示在于:超負荷的經濟增長是很脆弱的。
在雪下得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的南方地區,對低溫和大雪既無準備,又無經驗,煤、電、油、運頻頻告急,尤其是電網和交通,一度陷入癱瘓。能源和基礎設施向來是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瓶頸,中國也不例外。2003年和2004年的“電荒”和“煤荒”中,廣東、上海和浙江不少地方都不得不拉閘限電,一些企業因此蒙受了經濟損失。2005年之后,能源緊缺的局面有所緩解,但中國經濟像油門踩到了底的汽車,隨時可能因為缺油、路況不佳和突發事件而發生交通事故。2008年,事故果然隨著大雪發生了。
雪過天晴,除了災民的創痛一時難以愈合,經濟生活中的一切似乎和天氣一樣,都已經回復到了正常狀態。雪災顯然加劇了物價的波動,1月的CPI指數創下了新高。根據經驗,2月和3月的數據有可能在1月的基礎上繼續走高,但對于緊緊盯著物價指數的央行和中央政府而言,晴天就是最好的消息。由于春節是傳統的消費旺季,必定要推動物價上漲,所以1月的CPI數據雖高,卻并不出乎人們的意料。許多經濟學家估計,到4月之后,這一波上漲會趨于平緩。
但春節前開始實施的限價政策仍然沒有解除。央行和中央政府仍然在警惕發生全面通貨膨脹。由于雪災發生在經濟發達的南方,人們曾擔心災害會拖累經濟增長的速度。但隨著天氣轉好,中央政府迅速評估了災害造成的損失,緊接著對宏觀經濟做出了判斷。雪災的影響被認為是有限的,“過熱”仍然被當作2008年經濟生活中的頭號風險。雪災過后,“調控”之聲恢復了原來的音量。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近期表示,為了應對每年4000億-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帶來的基礎貨幣投放過多,2008年仍有必要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
防過熱還是防衰退
太平洋此岸對過熱的“調控”一波接著一波,彼岸卻是憂愁“衰退”的悲聲不斷。
《金融時報》高調警告美國可能陷入衰退。2月22日,該報評論員引述了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教授魯里埃爾?魯比尼的話說,美國可能陷入災難性的惡性循環,即“深度衰退導致金融虧損更為嚴重,反過來,不斷加劇的大規模金融虧損和金融崩潰又會令衰退更為嚴重”。
這篇文章有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叫做“走向金融災難的12步”;作者還特意提到,2006年7月,魯里埃爾?魯比尼率先預測了美國的衰退。“當時他的觀點極具爭議。如今已經不再是這樣了。”很有一點“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意思。
引發“美國衰退論”的次貸危機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拖累了全球股市。中國的經濟學界也有人擔心,美國一旦由于次貸危機陷入衰退,消費不振,將影響到“中國制造”的市場需求,出口下降又將影響中國經濟,從而引發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全球衰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有人提出,中央政府應該重新評估2008年的經濟形勢,防止過度調控,導致衰退。
中國建設銀行的張濤撰文說,“廣東從去年下半年就已出現的制造業疲軟,導致一部分中小制造企業面臨倒閉與外遷,而隨著美國經濟衰退的趨勢日益明朗,中國其他沿海地帶的以出口為依賴的制造業不可避免地受到打擊”。
張濤提出,宏觀調控應該在操作層面有彈性。而同濟大學金融系教授石建勛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文章更直接地說,要防止“調控政策失效或超調”,引發意外的“經濟衰退”。言外之意,“加息”和“從緊”的必要性,需要重新考量。
盡管從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到美國“股神”巴菲特都認為,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樊綱也認為,對美國的次貸危機,沒有必要反應過度。但“衰退”的確是眼下世界經濟學界最熱門的詞匯。圍繞“美國經濟是否會發生衰退”的爭論,使得“經濟周期”一說再次甚囂塵上。根據“周期”理論,經濟的增長與衰退是交替發生的。此前美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20多年,許多人一度認為,隨著各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能力日益加強,“周期”不再是經濟生活中的必然現象。但如果魯里埃爾?魯比尼對美國經濟的預測不幸而言中,毫無疑問,“周期”將在經濟學界取得新的勝利。
樂觀主義現在不太流行,但樂觀主義者仍有人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維森就堅持認為,次貸危機既不會拖垮美國經濟,更不會拖垮中國經濟。
在與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交換意見之后,李維森對《新民周刊》說,次貸危機并沒有影響到美國的實體經濟,也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民眾的消費意愿和能力下降。談“美國衰退”或“中國經濟外部需求下降”,都為時過早。

中國加息vs美國減息
對“衰退是否會發生”這個問題,回答有悲觀和樂觀之別,但經濟學家都為2008年的宏觀調控走向感到猶豫。經過2007年的6次加息,“加息”似乎變成了“宏觀調控”的代名詞,但這一政策卻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應對危機的重招就是降息。經過緊急降息,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由之前的4.25%降至3.5%,而在2007年12月的第6次加息后,人民幣一年期利率水平為4.14%,中美利率發生了倒掛。這使得美元投資中國固定收益市場的收益率上升,將吸引更多的熱錢流入中國逐利。這些熱錢兌換成人民幣之后,勢必又要加重市場的流動性過剩。
加息政策作為一把雙刃劍,危險之處還在于,調高存款利率要擴大銀行支出,對國有銀行微妙的利潤制造能力產生了威脅。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也要產生成本,需要央行來消化。與此同時,美元貸款利率也低于人民幣貸款利率,央行如果繼續上調貸款利率,國內企業就會通過各種渠道申請美元貸款,導致外匯占款將會繼續飆升。這也會進一步加大人民幣發行量。
加息的效果也一直是質疑的對象。通脹如山倒,加息如抽絲。這種局面屢屢被認為是加息政策“藥不對癥”導致的。
李維森認為,宏觀調控過于依賴加息,而加息的空間不斷縮小,已使調控走入了一個“貨幣政策至上”的誤區。在他看來,中央政府過于關注流動性過剩和匯率的關系,而忽略了財政政策在通脹中扮演的角色。
“目前錢最多的,不是私人部門和民營企業家,而是政府。”李維森說。中國GDP近年來的增長通常在10個百分點左右,而政府的財政收入一直在以20%以上的年增長速率遞增。2006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接近4萬億,2007年超過5萬億,增速在30%以上。
這一筆數額巨大的財政收入中,除了公共服務方面的開支,往往還有20%以上被用于政府機構自身運作經費,用作政府投資的經濟建設費用所占比例同樣高居不下,在2006年占到了財政開支的26.56%。地方政府投資經濟的熱情只會高于中央政府,因為經濟增長通常決定了地方官員的仕途。地區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色,也是促使各地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和國有企業的重要原因。大量的財政投資已經成了催生“過熱”的重要原因,而財政投資的命門則在于財政收支體制。
“財政收支制度不變,講宏觀調控,講遏制經濟過熱,講反對通脹膨脹,可能都只是說說而已。”李維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