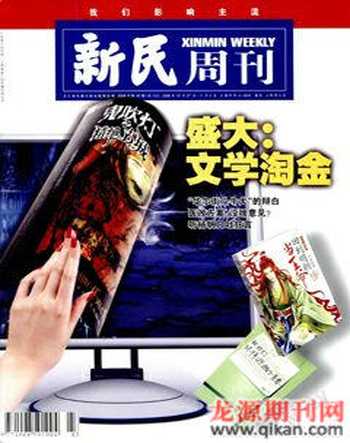土地流轉不會產生流民
葉 檀

重要的是要賦予農民市場博弈權,并進行細致入微的教育,防止農民因為小利而喪失了長久的保障。
中國改革要突破瓶頸必須解決農村問題,解決農村問題必須要解決土地問題,只有讓土地蛻變為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才能解決農民原始積累永遠無法完成的大課題。
7億多農民收入主要來源有二,一靠打工,二靠務農。民工收入雖然在上漲但趕不上物漲增速,務農收入更低。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針對“三農”問題連續出臺了五個“一號文件”,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但“三農”問題仍然困難重重。數據顯示,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來增幅最高,但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年。2005年,城鄉居民現金收入差距達到3.3:1,如果不采取措施遏制城鄉收入差距拉大趨勢的話,2020年按照預計城鄉收入差距有可能達到4:1。
這是中國改革的瓶頸,農業效率不提高、農民人數不減少、農民收入不上升,中國經濟發展無法走上壯大內部市場的內需之路。改革30年的實踐證明,不論進城務工還是務農,都解決不了小農經濟效率、農民收入低下的問題。不僅中國,在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在工業化階段都伴隨著成功的土地改革制度,使農民擁有原始積累資金、順利從農民過渡到農場主或者工人的身份。
只有土地才能解決農民缺少原始資金、缺乏財產性收入的問題。根據一些學者的估算,農村僅宅基地的市場價值就高達20萬億元,如果18億畝耕地使用權可流轉,那么將釋放出更多財富,從而成為帶動農村消費、城市化等一系列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
各界最擔心的是,農民在獲得土地流轉權后,是否存在因為經濟壓力急于兌現、或者不了解市場定價、或者在市場博弈中處于弱勢而以低價出售土地收益,從而失去最后的保障、淪為無地、無錢、無工作“三無”農民的悲慘境地。
這個擔心言之成理,需要出臺細致的配套措施加以規范。但前提是必須承認,土地承包權流轉保障了農民的權益,是對農民土地物權的確認。我國農民目前雖然擁有少量土地,卻由于缺乏產權與流轉權,而處于弱勢地位。
國家統計局曾對近三千家農戶進行調查,顯示耕地被占用前年人均純收入平均為2765元,耕地被占用后年人均純收入平均為2739元。湖北省社科院和湖北經濟學院2005年在武漢聯合做了一次有關調研,在前述武漢調研中,補償款到村集體手中一般為3萬元~5萬元/畝,每個農民拿到手的補償款平均每畝1萬元左右。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多數地方征地收入的分配比例的大致是:農民得5%~15%,集體得25%~30%,地方政府及其機構得60%~70%。
“三無”農民的產生并不在于產權能否流轉,而是出于農民無法維護自身權益。在現行土地制度下,失地農民仍然存在。據國土資源部統計,每征一畝地,將造成1.4個失地農民,當前中國失地農民的總數至少在4000萬人左右,且每年還以200多萬人的速度遞增。有關專家估計,如果考慮違規占用耕地,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農民的數量可能高達5000萬。
因此,如果土地實行70年長久承包制,如果農民的土地物權能以使用權的方式進行流轉,重要的是要賦予農民市場博弈權,并進行細致入微的教育,防止農民因為小利而喪失了長久的保障。
我國臺灣地區始自上世紀4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先是耕地進行重新丈量,登記造冊,隨后頒布了“實行耕者有其田法條例”,主要內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當于中等水田3甲(43.5畝)或者旱地不超過6甲,超過的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后頒給農民;征耕地價也是按耕地主要產物全年收獲量的2.5倍,“政府”用債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給地主。農民耕者有其田,地主則獲得股票補償,隨著經濟的增長,土地與股票全都增值。教育農民的工作深入田間地頭,以防止農民低價售地,造成失地問題。
因此,解決土地問題的關鍵在于,確定農民的土地物權,可以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完成從封建主義向原始工業社會的過渡,其次,通過工業化的進程,使農民融入城市化與工業化渠道,積累財產性收入,同時完成現代農業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