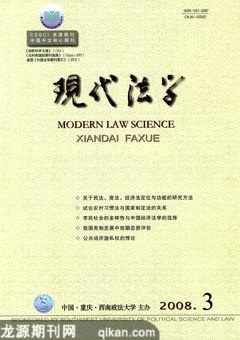推定在犯意認定中的運用
賴早興
摘 要:由于意識與意志的主觀性,在刑事訴訟中,犯意的證明一直是困擾控方的難題。在缺乏被告人自白的情況下,犯罪的證明完全依賴于推定這一手段。但推定結(jié)論的或然性引發(fā)了人們關(guān)于犯意認定中推定運用可行性的懷疑;犯意推定的證據(jù)標準也無法與直接證明的標準一致;推定還可能導致證明責任分配上的爭論。英美國家刑事訴訟中對于犯意推定形成了較為穩(wěn)定的規(guī)則,可資借鑒。
關(guān)鍵詞:推定;犯意;必要性;證據(jù)標準;證明責任
中圖分類號:DF611
文獻標識碼:Aオ
在證據(jù)學中,推定是指在缺乏證據(jù)直接證實A事實時,基于已經(jīng)得到證明的B事實,根據(jù)B事實與A事實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推定A事實的存在。推定的根據(jù)是事實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是人們在長期生活中通過反復實踐所取得的一種因果關(guān)系經(jīng)驗。在刑事訴訟中,犯意認定是否可以借助于推定這一手段?犯意推定的證據(jù)標準是什么?在犯意推定的反駁中,被告人是否承擔證明責任?筆者試圖基于英美國家刑事訴訟中犯意推定的運用實踐對這些問題作初步解答。
一、推定在犯意認定中的爭議
推定通常表現(xiàn)為人們利用歸納法從經(jīng)驗中推導出結(jié)論,其結(jié)論往往具有或然性。例如,有學者認為:“推定是人們基于經(jīng)驗法則而來的,人們對社會某種現(xiàn)象的反復認識之后,逐漸掌握了其內(nèi)在的規(guī)律,對這種內(nèi)在規(guī)律的認識即經(jīng)驗法則,具有高度的蓋然性……因為事實推定的機理是基于蓋然性,因而得出的結(jié)論并非是必然的,而存在或然性”[1]。“因為其他事實與待證事實間沒有那么高的蓋然性,從而通過推定來認定案件事實,相對于通過證據(jù)來認定,其出現(xiàn)偏差的可能性要大。”[2]正是這種非必然性,推定運用的可靠性一直受到人們的質(zhì)疑。關(guān)于這一點,弗蘭西斯?培根的觀點較為偏激,他認為,理性常常欺騙我們,我們須在理性的翅膀上系上重物,防止它飛躍,一切錯誤都是由推理造成的[3]。而英國哲學家羅素關(guān)于推定的質(zhì)疑觀點則具有普遍性,他說:“我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關(guān)于非證明的推理的討論是過于限于歸納法的研究。我得到的結(jié)論是,歸納的論證,除非是限于常識的范圍內(nèi),其所導致的結(jié)論是偽常多于真。常識所加的界限容易感覺得到,但是不容易用公式說出來。最后我得到的結(jié)論是,雖然科學上的推理需要不能證明邏輯以外的原理,歸納法并不是這種原理之中的一種。歸納法有它的作用,但是不通用作前提。”“我覺得以前是過于重視了經(jīng)驗,因此我覺得經(jīng)驗論這種哲學非大受限制不可。”[4]
我國法學界對事實推定是否應(yīng)當適用或是否能夠在定罪過程中運用一直存在爭議。一般認為,推定在訴訟中具有重要意義。如有學者認為,事實推定即邏輯推定在訴訟中具有間接證據(jù)的作用,對法院來說,可以增強對某種事實的確信;對當事人或檢察院來說,可以減輕其舉證責任[5]。但也有學者對事實推定的運用表達了擔憂。例如,有人從推定與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出發(fā),認為“推定可用于解決民事糾紛,但在刑事法律上應(yīng)該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凡是刑法上沒有明確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也不得在缺乏充分證據(jù)的情況下對行為人實施處罰,因此,絕對不能將推定的事實作為追究當事人刑事責任的依據(jù)”[6]。有人認為:“從事推論而違背經(jīng)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所在多有,民刑皆然。借自由心證、多憑情況證據(jù)或所謂間接證據(jù),為偏而不全之推論,甚至僅憑主觀之推測。由此建立一種結(jié)論,無異創(chuàng)造一種結(jié)論,危險殊甚,無可諱言”[7]。還有人認為:“推定中不僅包含有專斷和人為的因素,而且具有偏見的成份”[8]。
但在我國刑事立法與刑法理論中,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須以行為人具備主觀罪過為前提。從刑事立法上看,我國不但在《刑法》總則中規(guī)定了犯罪故意與過失,而且在《刑法》分則中規(guī)定的任何犯罪均應(yīng)當由故意或過失構(gòu)成。在故意犯罪中,部分犯罪的罪狀還規(guī)定了特定的目的,如以非占有為目的、以營(牟)利為目的、以非法銷售為目的、以傳播為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以出賣為目的、以泄憤為目的等。這些規(guī)定強調(diào)行為人行為的目的性,即只有具備法定的目的時,其行為才構(gòu)成犯罪或構(gòu)成特定的犯罪。但這些目的的證明如果缺乏被告人的供述,通常難以用證據(jù)直接加以證明。
二、犯意認定中推定運用的必要性
罪過的內(nèi)容是意識與意志。由于意識與意志因素均內(nèi)在于行為人的腦海觀念中,故而難以讓外界認識和把握。因此,哲學和心理學界均認為意識和意志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所言:“意識問題一直是科學和哲學研究中極其困難和復雜的問題”[9]。 “意識是心理學中的一個傳統(tǒng)基本理論問題,更是哲學、心理學上的老大難議題。”[10]由于意識與意志的主觀性,我們對他人意識與意志的把握相當困難,這也導致了刑事訴訟過程中罪過證明的困難。正如有學者所言:“你無法看到犯意,甚至最先進的現(xiàn)代技術(shù)也無法發(fā)現(xiàn)或衡量犯意”[11]。“證明犯意是相當困難的。在犯意下,公訴方必須將被告人基于所需犯罪心態(tài)實施了犯罪行為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例如,強奸罪的犯意標準通常要求公訴方證明被告人知道被害人不同意。犯罪心態(tài)確實很難證明,特別是當公訴方基本依賴間接證據(jù)(circumstantial evidence)證明其案件時。”[12]我國學者在論述“明知”時也認為:“‘明知作為人的一種心理活動,有一個非常復雜的形成及表現(xiàn)過程,目前的科學技術(shù)水平根本無法將其客觀地再現(xiàn)出來”[13]。
但這種困難并不說明犯意無法認識和把握,因為主觀性只是意識與意志的特征之一,其另一特征即客觀性使意識與意志可以為外界所認識與把握。正如有學者所言:“人們常講意識的形式是主觀的,這話不錯。其實,不僅意識的形式,就是意識(包括意識的內(nèi)容、要素、材料)也都是主觀的。但是,意識形式作為意識把握客觀世界的方式,它是客觀世界的反映,而不是純粹主觀自生的”[14]。正是意識與意志的客觀性使罪過認識成為可能。同樣,作為行為人犯意的意識和意志因素也可以基于外界因素加以認識和把握。例如,有人認為:“明知”這一主觀要件的認定,一般無法憑直接證據(jù)來證明,而只能通過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來認定[13]35。另有人認為:認定“明知”的惟一方法就是通過客觀行為來推定,因為人的思想是對客觀的反映,支配著人的活動。人的活動是人的思想的外部表現(xiàn),反映著人的思想。犯罪主觀方面是支配犯罪行為的心理基礎(chǔ),它必將通過犯罪的客觀行為表現(xiàn)出來[15]。
那么,司法實踐中應(yīng)當如何認識行為人的犯意?一般認為,自白是犯意的惟一直接證據(jù),但被告人很少承認自己的真實意圖。而且,即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了自己的主觀心態(tài),我們也無法純粹依據(jù)行為人的自白確定其犯意。因為《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guī)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jù),重調(diào)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jù)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在《關(guān)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強調(diào):“認定窩藏、銷贓罪中的‘明知,不能僅憑被告人的口供,應(yīng)當根據(jù)案件的客觀事實予以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應(yīng)當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或者代為銷售的,就可以認定。”所以,犯意的證明通常依賴于案件
中的間接證據(jù),而間接證據(jù)無法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它需要與其他證據(jù)結(jié)合起來才能作為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jù)。
如何以間接證據(jù)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意?這就要借助于推定的運用。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推理和推定是對抗式訴訟中事實發(fā)現(xiàn)的重要方法。對事實裁判者而言,從一個或更多的‘證據(jù)的或‘基礎(chǔ)的事實中推定某一犯罪要素存在與否是必要的。”[16]主觀故意的推定是事實推定的一個好例證[17]。我國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從行為人作案手段、作案工具、打擊部位等明知會發(fā)生或者可能發(fā)生不同的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jié)果的發(fā)生。因而,根據(jù)行為人的行為,可以推斷出行為人的罪過形式與內(nèi)容[18]。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推定被廣泛地運用于犯意的證明中。例如,一些故意犯罪對行為人主觀方面有“明知”的要求,而對行為人是否“明知”的證明就要運用推定。例如,《刑法》第310條規(guī)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構(gòu)成窩藏、包庇罪。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此“明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總結(jié)司法實踐中的成功經(jīng)驗,在《關(guān)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guī)定:認定窩藏、銷贓罪中的“明知”……應(yīng)當根據(jù)案件的客觀事實予以分析。只要證明被告人知道或應(yīng)當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或者代為銷售的,就可以認定。在《關(guān)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guī)定》更是明確指出:本規(guī)定所稱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應(yīng)當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視為應(yīng)當知道,但有證據(jù)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一)在非法的機動車交易場所和銷售單位購買的;(二)機動車證件手續(xù)不全或者明顯違反規(guī)定的;(三)機動車發(fā)動機號或者車架號有更改痕跡,沒有合法證明的;(四)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購買機動車的。又如,《刑法》第192條規(guī)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shù)額較大的構(gòu)成集資詐騙罪。在該罪的認定中,必須證明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曾經(jīng)規(guī)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yīng)當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1)攜帶集資款逃跑的;(2)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3)使用集資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4)具有其他欺詐行為,拒不返還集資款,或者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
聯(lián)合國關(guān)于刑事犯罪的公約中也有關(guān)于犯意推定的規(guī)定。例如,聯(lián)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5條第2款規(guī)定:“本條第1款所指的明知、故意、目標、目標或約定可以從客觀事實情況推定。”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第28條規(guī)定:“根據(jù)本公約確立的犯罪所需具備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據(jù)客觀事實情況予以推定。”
當然,只有在直接證據(jù)無法證明犯罪要素時我們才需借助于推定的運用,因為推定并不是犯罪證明的主要手段。正如有學者所言:“任何案件,主要是通過證明確認的,采用推定形式解決某些事實問題,不論在哪個國家司法中,都處于輔助的地位”[19]。“與證據(jù)直接證明相比,推定是一種降低了標準的論證方式,屬于不得已而為之,因此推定只能用于不得已的場合。”[20]
由于推定的不精確性,有學者提出,在刑事訴訟中要限制推定運用。如有學者認為:“為防止和限制事實推定的濫用,應(yīng)該明確其適用范圍僅限于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黑社會犯罪、恐怖主義犯罪等嚴重犯罪中涉及明知、故意、目的、目標、約定等主觀方面的事項,而不能任意擴大事實推定的適用范圍。”[21]
三、犯意推定的標準
推定的根據(jù)是推定事實與基礎(chǔ)事實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只有兩個事實之間存在內(nèi)在聯(lián)系才可能有推定的存在。而兩個事實之間的聯(lián)系是什么?在英美法系國家,推定的標準是基礎(chǔ)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在“合理聯(lián)系”(rational connection)。這一標準是在1910年的一個民事過失案Mobile, Jackson, & Kansas City Railroad v. Turnipseed(219 U.S. 35 (1910).)中,由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創(chuàng)立的。在該案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只要推定事實與已經(jīng)被證明的事實(即基礎(chǔ)事實)之間存在合理的聯(lián)系,推定就是合憲的。在Tot v. United States(319 U.S. 463 (1943).)案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強調(diào)了“合理聯(lián)系”標準在刑事案件中的運用。在Leary V. United States(395 U. S. 6 (1969).)案中,在重溫了Tot案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和其他刑事推定的案例后,哈蘭(Harlan)法官在為聯(lián)邦最高法院所寫的判詞中總結(jié)到:“該刑事制定法中的推定必須認為是‘非理性的和‘任意的,因此是不合憲的,除非實質(zhì)性地確保這種推定的事實極可能是作為其基礎(chǔ)的已經(jīng)被證明事實的結(jié)果。”
一般認為,“合理聯(lián)系”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chǎn)、生活中反復實踐后所取得的事實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總結(jié),這種因果關(guān)系是事實之間的一種內(nèi)在聯(lián)系。這種內(nèi)在聯(lián)系被實踐證明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真實的,具有高度的蓋然性,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產(chǎn)生例外。也就是說,基于這種內(nèi)在聯(lián)系,當某一事實存在時,另一事實就必定或極大可能存在。至于聯(lián)系的合理程度,則很難給出一個確定的量化標準,這通常取決于被推定事實與基礎(chǔ)事實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正如有學者所言:“推定規(guī)則的效果很難抽象的作出評價。這取決于基于經(jīng)驗和通常感覺事實X與Y之間聯(lián)系密切程度。如果X與Y聯(lián)系緊密,那么從一個事實推導出另一個事實的推定的可信度將顯而易見。相反,如果兩事實之間聯(lián)系完全不緊密,即事實Y通常不能視為事實X的充分證據(jù),那么這種推定將允許陪審團作出無罪判決,而不是相反。”[22]
“合理聯(lián)系”標準說明,推定事實與基礎(chǔ)事實之間存在經(jīng)驗上的、較強的聯(lián)系,但這并不能說明基于已經(jīng)被證明的事實必定就推導出推定事實,這種聯(lián)系實際上無法達到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證明中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英美刑法學者均認為犯罪包括兩方面的要素:危害行為和犯意。正如有學者所言:“一般說來,犯罪包括兩方面的要素:危害行為(actus reus),即犯罪的物理或外部部分;犯意(mens rea),即犯罪的心理或內(nèi)在特征。”[23]有學者認為:“通常將犯罪分為兩個要素:危害行為和犯意,任何犯罪均可分解為這些因素。例如,謀殺是故意殺害他人的犯罪,謀殺罪的行為是殺人,犯意是故意。”[24]從這些學者的觀點看,犯罪成立必須犯罪外部要素(危害行為)和內(nèi)部要素(犯意)同時存在[注:危害行為(actus reus)和犯意(mens rea)這一拉丁詞語是來自科克的著作《制度論》(Cokes Institutes)中的一個句子。(Jonathan Herring, Marise Cremona. Criminal Law.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p28.)不過,很多學者認為,此拉丁語模棱兩可,在使用時可能導致混淆。(Nicola Padfield. Criminal Law. Beccles and London: Reed Elsevier(UK) Ltd.2002.p21.)有學者認為,它們本身就可能導致誤解,這一用語已經(jīng)受到了來自學者和法官們的批評。在Miller案中,Diplock公爵使用的是“被告人的行為和行為時他的心理狀態(tài)”。(Jonathan Herring, Marise Cremona.Criminal Law.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p28.)即使如此,這危害行為與犯意這兩個術(shù)語在英美刑法中仍被廣泛地運用。],也就是說,控方必須將犯意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但很顯然,在運用推定認定行為人的犯意時,無法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因為基于一個事實推定出另一個事實,只是一種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大,也無法說明這是百分之百的準確。正如有學者所言:“在刑事訴訟中,推定允許陪審團從另一個事實推定事實,減輕了控方將推定事實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程度的責任。在某種程度上,被證明的事實與被推定的事實不可能完全一樣,從一個事實推定出另一個事實,正如一個積極辯護,構(gòu)成了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一個例外。在這一點上,推定在功能上相當于一個積極辯護。”[25]因此,犯意推定的標準與證明標準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國法定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這就要求犯罪主觀事實清楚,認定犯意的證據(jù)確實充分。對于這一標準,學界有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客觀真實說認為:“法院判決中所認定的案件事實與實際發(fā)生的事實完全一致。”[26]法律真實說認為:“所謂法律真實是指公、檢、法機關(guān)在刑事訴訟證明的過程中,運用證據(jù)對案件真實的認定應(yīng)當符合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guī)定,應(yīng)當達到從法律的角度認為是真實的程度。”[27]從推定結(jié)論的或然性看,犯意推定只可能用法律真實衡量其標準問題,無法達到客觀真實的要求。而且,即使以法律真實為標準,犯意推定也無法真正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程度。這說明在沒有被告人的自白且以其他證據(jù)加以補強的情況下,基于推定的犯意認定無法達到通常的證明標準的要求。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由于有罪認定對公民造成的嚴重后果,必須以基本事實的嚴格證明為基礎(chǔ),如不能達到這種證明效果,應(yīng)當推定其無罪。這無疑應(yīng)當成為刑事訴訟的一般原則。然而這一原則也有例外。這種例外是根據(jù)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策的需要,即為打擊某種行為的特殊需要;二是因為證明上的特殊困難,從而解決所謂‘一般證據(jù)走入死胡同的問題;三是行為人的先前行為本身導致其證明責任的承擔。”[28]“推定的實質(zhì)是降低證明標準,即由一般的定罪標準‘排除合理懷疑,降低為一種‘優(yōu)勢證明,即‘更大的可能性的證明。”[28]471
四、犯意推定與反駁
從分類上看,推定通常可以分為三種,即決定性的或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conclusive or ir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law)、非決定性的或可反駁的法律推定(inconclusive or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law)和事實推定(presumption of fact)。法律推定可細分為決定性的推定與非決定性的推定,而事實推定則沒有這種分類。其原因在于事實推定均為可反駁的推定,即推定的事實不是決定性的。由于刑事制裁的嚴重后果,沒有哪個國家在刑事法律上規(guī)定決定性的推定。因此,在刑事領(lǐng)域里的推定均是可以反駁的推定。我國有學者認為:“無論法律上的推定還是事實上的推定,都應(yīng)該允許反駁。這是由推定的不精確性或蓋然性所必然得出的結(jié)論。……從訴訟意義上來說,允許對推定進行反駁還有另外一種理由,即推定所依據(jù)的經(jīng)驗或常識有時沾染了理論,而理論有的是有偏見的,欠公允的。因此,在審判實踐中,審判人員依靠經(jīng)驗或常識進行推理尤需慎重。”[29]這一觀點明確指出,推定的不精確性和可能存在的欠公允性會導致推定可以被反駁。[注:當然,如前文所指出的,并非所有推定均可以被反駁,部分法律推定是不可以反駁的,只有事實推定和部分法律推定可以被反駁。]
還有學者主張:“通過被告人的有效反證來推翻控方用間接證據(jù)所作的推定,從而把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果降低到最低限度。質(zhì)言之,如果被告人不進行反證,只要控方用以證明犯罪主觀要件的間接證據(jù)——有關(guān)客觀行為的證據(jù)充足,就當然地推定控方所要證明的主觀要件成立。” [13]35
從推定的結(jié)構(gòu)上看,所有推定均有基礎(chǔ)事實(basic facts)和推定事實(presumed facts)。推定的適用首先必須有基礎(chǔ)事實或一系列的基礎(chǔ)事實。一旦基礎(chǔ)事實被證明為真,基于兩事實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就基本上或完全可以認定推定事實的存在。通常情況下,對于推定的反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質(zhì)疑基礎(chǔ)事實,即質(zhì)疑作為推定的基礎(chǔ)事實的真實性或讓事實裁定者對推定的基礎(chǔ)事實的真實性產(chǎn)生懷疑;二是對基礎(chǔ)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聯(lián)系加以質(zhì)疑,即主張基于經(jīng)驗或常識,從基礎(chǔ)事實無法推定出推定事實。
無論是從哪個方面入手,這都涉及證明責任的分配問題。我國有學者認為:“推定是重要的法律行為,是必然要引起法律效力的。推定的第一種效力就是引發(fā)舉證責任的轉(zhuǎn)移。這是任何一項推定一經(jīng)做出,就一定會產(chǎn)生的一種法律效力。”[30]不過,也有學者認為:“事實推定……對當事人或檢察院來說,可以減輕其舉證責任。……事實推定不能導致舉證責任的轉(zhuǎn)移,因舉證責任是同敗訴風險聯(lián)系在一起的,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如果無法舉證或者舉證不充分將導致敗訴,而事實推定盡管是根據(jù)事物之間的常態(tài)聯(lián)系所為,但畢竟具有相對性、不確定性,而且法律上又無規(guī)定,事實推定與法律推定相比,又是大量的,所以如果導致舉證責任的轉(zhuǎn)移,就很可能使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在不舉證的情況下勝訴。在刑事訴訟中可能導致有罪推定。”[5]176-177而且,即使在認為被告人要提出反駁證據(jù)的情況下,被告人提出證據(jù)是一種義務(wù)還是權(quán)利仍有不同的觀點。如有學者認為:“這樣,被告人的反證就成了他的一種義務(wù),因為他不如此行事,就要承擔不利的后果。可見,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負有證明控方所指控的主觀要件不存在的證明責任”[13]35。另有學者認為:“即使是被告人提出證據(jù)反駁的,這種舉證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也僅是被告人的一種權(quán)利而不是義務(wù),不是被告人的舉證責任。”[21]347
犯意認定中,推定是否會導致證明責任的轉(zhuǎn)移?提出證據(jù)反駁推定是被告人的一種權(quán)利還是義務(wù)?在英美法系國家中,對現(xiàn)代刑事證明責任分配的確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Woolmington v.DPP( ([1935] AC 462(HL).)案。在該案中,英國上議院首席大法官三其(Sankey)伯爵說:“在英格蘭整個刑事法網(wǎng)上總可以看到一根金線,即除了我已經(jīng)說過的精神錯亂辯護和一些法定例外情況,證明被告人有罪是控訴方的責任……無論指控的是什么罪行,也無論是在哪里審判,控訴方必須證明被羈押者有罪的規(guī)則是英格蘭普通法的一部分,任何削弱或損害這一規(guī)則的企圖都是不允許的。”[31]這說明,在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證明責任分配中犯意是由控方加以證明的。由于犯意的特定屬性,控方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只能基于間接證據(jù)推定行為人行為時的犯意。由于推定是可以反駁的,被告方反駁時必然要提出相關(guān)的證據(jù)對推定的基礎(chǔ)事實或推定事實與基礎(chǔ)事實之間的聯(lián)系加以質(zhì)疑,這就必然使被告方承擔一定的證明責任。對于被告方的這一證明責任,英美學者一般認為,被告方只是承擔提出證據(jù)的責任,而不承擔說服責任。正如有學者所言:“僅僅是提出證據(jù)責任的轉(zhuǎn)移,說服責任并不隨之轉(zhuǎn)移,這對被告人和政府實質(zhì)關(guān)系的影響如果有的話也是影響甚微。相反,將提出證據(jù)的責任賦予被告人是我們篩選與案件無關(guān)的爭點的經(jīng)濟方法,而且也能提高訴訟的效率。”[32]在County Court of Ulster Cty. V. Allen(442 U.S 140 (1979).)案中,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只要被證明的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地支持對被告人有罪的推定,這種將證明責任轉(zhuǎn)移給被告人的推定就應(yīng)當?shù)玫椒ㄔ旱闹С?sup>[33]。從英美法系國家關(guān)于證明責任的分配上看,在犯意推定中,控方承擔基礎(chǔ)事實的提出證據(jù)的責任和說服責任;如果被告人反駁推定,就必須就其主張?zhí)岢鱿嚓P(guān)的證據(jù),使事實裁判者對基礎(chǔ)事實或“合理聯(lián)系”產(chǎn)生懷疑;然后,再由控方說服事實裁判者被告人提出的證據(jù)不真實或基礎(chǔ)事實與推定事實間的聯(lián)系是合理的。另外,在英美法系國家證據(jù)法中,證明責任通常表述為burden of proof。顯然,作為一種“負擔”,burden表達的更多的是義務(wù)而不是權(quán)利。
おお
參考文獻:
[1] 何家弘. 證據(jù)學論壇:第3卷[G]. 北京: 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1:164-165.
[2] 王利明,等. 中國民事證據(jù)的立法研究與應(yīng)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815-816.
[3] 沈達明. 英美證據(jù)法[M]. 北京:中信出版社, 1996:71.
[4] 伯特蘭?羅素. 我的哲學的發(fā)展[M]. 溫錫增, 譯. 北京: 商務(wù)印書館, 1996: 174.
[5] 劉金友. 證據(jù)理論與實務(wù)[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2: 176.
[6] 余凌云,曹國媛. 不能以推定的事實作為刑事、行政處罰的依據(jù)[J]. 道路交通管理, 2002 (7): 23.
[7] 李學燈. 證據(jù)法比較研究[M]. 臺北: 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2: 298.
[8] 紀敏. 證據(jù)全書[M].北京: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 2270.
[9] 馮契. 哲學大辭典[M].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1:1816.
[10] 霍涌泉. 意識研究的百年演進及理論反思[J].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 (3): 118.
[11] Jerome Ha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Lexis Law Pub, 1960, p106.
[12] Assaf Hamdani, Mens Rea and the Cost of Ignorance, 93 Va. L. Rev. 415,422 (2007).
[13] 游偉,肖晚祥. 論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J]. 人民司法, 2001 (5): 35.
[14] 韓民青. 意識論[M].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8: 99.
[15] 陳興良. 刑事法判解:第2卷[G].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51.
[16] Mobile, J. & K. C. R. Co. v. Turnipseed, 219 U.S. 35 (1910).,p42; TOT v. United States, 319 U.S. 463 (1943).p467; Barnes v. United States, 412 US 837 (1973)., p 843-844.
[17] P.B.Carter, Cases and Statutes on Evidence.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0.p77.
[18] 譚永多. 刑事證據(jù)規(guī)則理論與適用[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69.
[19] 裴蒼齡. 論推定[J]. 政法論壇,1998 (4): 53.
[20] 何家弘. 證據(jù)學論壇:第六卷[G]. 北京: 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3: 347.
[21] 崔敏. 刑事訴訟與證據(jù)運用:第二卷[G].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6: 487.
[22] Jerome Hal,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Lexis Law Pub,1960, p106.
[23] Joshau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New York: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01.p81.
[24] Nicola Padfield. Criminal Law. Beccles and London: Reed Elsevier(UK) Ltd.2002. p 21.
[25] John Calvin,Jeffries, PaulB.StephanIII, Defenses, Presumptions, and Burden of Proof in the Criminal Law. 88 YaleL.J.1325,1336(1979).
[26] 陳一云. 證據(jù)學[M].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1: 114.
[27] 樊崇義. 客觀真實管見[J]. 中國法學, 2000 (1): 117.
[28] 龍宗智. 相對合理主義[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471.
[29] 葉自強. 刑事上的推定與法律上的推定[N]. 人民法院報,2001-11-23.
[30] 裴蒼齡. 再論推定[J]. 法學研究,2006 (3): 119.
[31] Raymond Emson, Evidence(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424.
[32] JohnCalvinJeffries,PaulB.StephanIII, Defenses, Presumptions, and Burden of Proof in the Criminal Law. 88YaleL.J.1325,1334(1979).
[33] County Court of Ulster Cty. v. Allen, 442 US 140 (1979), p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