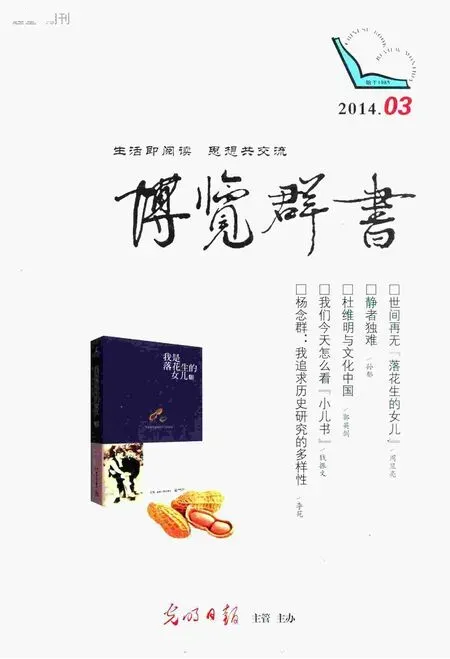精神分析:二十世紀的巫術?
袁 暉
盡管人類變得越來越聰明,但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迷誤。而讓一代人著迷的東西,在下一代人看來往往是可笑的。在20世紀的中國,曾出現(xiàn)過打雞血、喝紅茶菌、氣功療法、《易經(jīng)》預測等運動,直讓廣大人民群眾一陣陣歡欣鼓舞如醉如癡。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來說,20世紀可以說是弗洛伊德的世紀,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精神病學基礎理論和心理疾病治療方法風靡一時。特別是弗洛伊德試圖通過對“夢的科學研究”揭示性的秘密,以治療人的心理疾病和解除人的精神痛苦。這是多么奇妙的事業(yè)呵,誰不想了解性的秘密?!難怪著名的分析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精神分析學說具有神話一樣的誘惑力。
曾經(jīng)壟斷一些國家的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
精神分析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一位奧地利猶太人,他從兩三歲時隨父母遷入維也納直至晚年因納粹迫害出走倫敦,一生幾乎都在維也納度過。弗洛伊德家有兄妹七人,他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呢絨商人,家境并不寬裕。但弗洛伊德自小聰慧過人,學習刻苦用功,他依靠父母的支持和學校的助學金讀完了維也納大學醫(yī)學專業(yè),并于1881年獲醫(yī)學博士學位。
年輕的弗洛伊德非常希望從事專門的醫(yī)學研究工作,將來成為一名神經(jīng)解剖學家或生理學家。但是,經(jīng)濟的窘困使他不得不在離維也納市中心不遠的地方開一家私人神經(jīng)病診所以謀生,他從而成為一名臨床心理治療醫(yī)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西方幾乎沒有私人開業(yè)的精神病醫(yī)生,心理治療屬于神經(jīng)病學的專業(yè)范圍)。然而,弗洛伊德執(zhí)著地把自己的臨床治療與理論研究結合起來。1895年,他與他的好友布洛伊爾合作發(fā)表《癔病研究》一書,奠定了精神分析學說的基礎。此后,《釋夢》(1899)和《性學三論》(1905)兩部著作的發(fā)表使弗洛伊德聲譽鵲起。1908年,第一屆國際精神分析大會在奧地利的薩爾茨堡舉行,此后精神分析學說在西方學術界逐步得到公認。
弗洛伊德的后半生可以說是輝煌的。他本人先后被美國克拉克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和被聘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的作品榮獲歌德文學獎。但是,后者不僅沒有使弗洛伊德感到欣喜反而使他憤怒,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科學研究成果應該獲得諾貝爾醫(yī)學獎,而歌德文學獎好像在表彰他擅長以優(yōu)美的文筆編寫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但是,精神分析在西方心理治療領域成為一種廣泛的運動大約從1950年代才開始。有意思的是,在對歐洲大陸文化一向冷漠的美國,精神分析卻十分流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納粹迫害而移居美國的精神病醫(yī)生中有許多人是精神分析專家。據(jù)說,當時美國的精神病學正教授幾乎都是精神分析專家。
在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中,具有造反精神的醫(yī)學專業(yè)的大學生憤怒地占領了校長辦公室。他們敢于否定醫(yī)學權威。堅決反對剝奪患者自由。他們強烈要求把精神分析學說納入教學大綱,在醫(yī)院中實施精神分析療法,廢除對于精神病患者的電休克療法。此后,精神分析逐步在法國心理治療領域占據(jù)支配地位。
精神分析不僅是一種思想運動,而且擁有自己的組織系統(tǒng)。1910年,弗洛伊德發(fā)起成立了“國際精神分析協(xié)會”,這一協(xié)會慢慢發(fā)展了若干地方性團體,如柏林精神分析協(xié)會、紐約精神分析協(xié)會等等。精神分析協(xié)會的主要任務是傳授精神分析治療技術,培訓未來的開業(yè)醫(yī)生。要取得精神分析醫(yī)生的資格僅有醫(yī)科大學文憑是不行的,還必須接受協(xié)會的培訓并取得資格。這種具有行會性質的組織系統(tǒng)使精神分析成為一種具有宗教派別特征的學派,而精神分析專家則憑借這一組織系統(tǒng)一度壟斷了一些國家的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的權力。
如果要用兩個字來概括精神分析學說,那就是“性欲”。弗洛伊德認為,性欲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原始沖動力(力比多),人以及人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的本原和動力都可以歸結為性欲。開始他只是把這一觀點應用于心理治療的臨床實踐,后來將其廣泛應用于對人類的行為、歷史及文化的研究。總之,弗洛伊德主義就是一種泛性主義。
精神分析的最不可思議之處,在于它認為幼兒即有性欲。弗洛伊德指出,嬰兒通過對母親乳房的吸吮獲得性欲的滿足,兩三歲的孩子通過肛門的排泄獲得性的滿足,三四歲的孩子則通過玩弄和顯露自己的生殖器獲得性滿足。由于幼兒有性欲,所以產(chǎn)生亂倫幻想:男孩喜歡母親而厭惡父親,欲弒父娶母(所謂“俄狄浦斯情結”);女孩親近父親而疏遠母親,欲與父親相戀(所謂“愛列屈拉情結”)。
據(jù)說弗洛伊德通過艱難的自我分析發(fā)現(xiàn),精神病患者的病因與他童年時期的性欲有關。假如一個人童年時期的性欲不能得到滿足而被壓抑在心靈深處(無意識之中),積聚多年之后便會在某種時刻以精神病態(tài)以及夢等形式爆發(fā)出來。如果能通過在喚起回憶時使患者把過去的特別是童年的遭遇“說”出來,那么癥狀就會立即消失并不再復發(fā)。
雖然弗洛伊德提出幼兒性欲的觀點,但他本人幾乎沒有診治兒童心理疾病的經(jīng)歷,在他的著作中唯一被提到的是患有恐馬癥的五歲兒童小漢斯。但是,弗洛伊德只與小漢斯做過一次十分短暫的談話,所謂“治療”是小漢斯的父親在弗洛伊德的授意下進行的。
大約在四五歲時,可憐的小漢斯突然由于害怕街上的馬咬人而不愿出門,后來則發(fā)展到總是為可能出現(xiàn)的裝滿貨物的馬車在轉彎時突然翻倒、馬四蹄朝天亂踢亂咬的場面而恐懼。弗洛伊德由此推斷,小漢斯曾經(jīng)看到過父母性交的場景,正是對這一可怕場景的回憶引發(fā)了小漢斯對于馬和馬車的幻象和恐懼。盡管父親對小漢斯是否看到自己和妻子做愛表示疑惑,弗洛伊德卻對自己的推斷感到“滿意”。
有一天,小漢斯做了一個夢。在他的夢里出現(xiàn)了兩只長頸鹿,一只很大,另一只有皺褶。后來小漢斯帶走了那只有皺褶的長頸鹿,并坐在它身上。于是,弗洛伊德展示了他的拿手好戲——釋夢:“坐在有皺褶的長頸鹿上”說明小漢斯想“占有”母親,有與父親競爭和與母親“同居”的愿望。
弗洛伊德認為,小漢斯這一病例進一步確證了他的幼兒性欲觀點。1908年,弗洛伊德給榮格寫信說,通過精神分析,小漢斯的恐馬癥已經(jīng)治愈。由于保護患者隱私的醫(yī)學原則,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經(jīng)典案例皆不署真實姓名。這當然為弗洛伊德的生花妙筆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用武之地,但卻使后人難以考證弗洛伊德真實的醫(yī)療成就。
讓今天的我們大惑不解的是,弗洛伊德是如何證明幼兒性欲存在的?至少嬰兒是不會說話的。據(jù)弗洛伊德本人說,他是通過“直接的”“沒有成見的”觀察發(fā)現(xiàn)了幼兒的性欲。或許是嬰兒在貪婪地吸吮母乳之后的心滿意足的樣子使弗洛伊德想到,成人只有在完成性行為之后才會如此。正如有學者指出,幼兒性欲是建立在類比推理基礎上的假設,并沒有
獲得任何事實的驗證,把這種天方夜譚般的說法作為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的基礎是荒唐的。
弗洛伊德欺世盜名?
隨著時光的流逝,精神分析的治療效果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精神分析的時代終于在1990年代結束了。目前在北歐和英國,精神分析學說已經(jīng)不再在心理學系講授而是在哲學系講授,而精神分析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方法已被“嗤之以鼻”。在近3億人的美國,只有5000人接受精神分析。據(jù)說,著名的紐約精神分析協(xié)會已難以再發(fā)展新的會員了。如今連許多精神分析醫(yī)生也承認,精神分析的療效十分有限。但他們又說,雖然不能治病,但精神分析“有助于”生活。無論如何,精神分析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治療方法。多少有些心理障礙的人不用擔心被關進可怕的精神病院,只要肯花錢就可以在綠樹成蔭的社區(qū)里向精神分析醫(yī)生“傾訴”,心情愉快地過日子。
據(jù)說,法國和阿根廷是當今世界上最信奉弗洛伊德的國家。目前法國仍有3/4的精神病醫(yī)生參照精神分析方法進行治療,而法國大部分心理學院系只向未來的臨床醫(yī)生講授由弗洛伊德學說派生出的治療方法。根據(jù)國際流行病的資料,有各種精神障礙(抑郁、瘋癲、恐慌、焦慮等)的人在人群總數(shù)中所占比例在各國大致相似(8%~10%)。但是調查證明,法國是消費精神藥物特別是抗抑郁藥和鎮(zhèn)靜藥方面的世界冠軍。有學者指出,精神分析在法國的絕對統(tǒng)治助長了精神藥物的濫用,因為人們難以找到有效的心理治療方法。
2004年2月,法國享有盛名的科學研究機構“國立保健及醫(yī)學研究學院”(INSERM)發(fā)表了一份關于幾種不同的心理治療方法的療效的“評估報告”。此報告宣稱,上萬次的科學研究和分析證明,精神分析沒有重大療效。這份報告使精神分析派學者和醫(yī)生感到無比憤怒,坊間一時議論紛紛。十分有趣的是,2005年2月5日,法國衛(wèi)生部長杜斯拉一布拉齊(P.BOUSTE-BALAZY)向媒體宣布:“人的心理痛苦是無法評估的”。同時他還宣布,那份“評估報告”已從衛(wèi)生部的網(wǎng)站上撤掉,這件事已經(jīng)過去了。衛(wèi)生部長的話不僅沒有使議論平息,反而掀起了軒然大波。有的人認為,衛(wèi)生部長闡明了一種學術寬容的態(tài)度,不同的醫(yī)療觀點和方法都有存在的權利。有的人則認為,衛(wèi)生部長的立場是令人驚訝的,它說明法國的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回到了不接受任何科學檢驗的蒙昧主義。相當多的精神分析醫(yī)生當然十分高興,他們終于松了一口氣,反正心理痛苦是無法評估的,所以人們對于精神分析療效的質疑也就沒有意義了。這一事件被人們稱作“巴黎之爭”。
“巴黎之爭”不禁使我們想到基督教歷史上有名的“巴利阿多里之爭”(con-troverse de Valladolid)。后者發(fā)生在16世紀的羅馬教廷和西班牙教會之間,雙方爭論的不是心理痛苦的問題,而是印第安人有沒有靈魂的問題。眾所周知,當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發(fā)現(xiàn)了并正在征服美洲新大陸。就是在這一曠日持久的爭論中,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以及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文明遭到了滅絕性的殺戮和毀壞。
同樣是在2005年,法國一家出版社推出了《弗洛伊德批判——精神分析黑皮書》(LE LIVRE NOIR DELA PSYCH-ANALYSE),此書成為當年法國的第八大暢銷書。這是一本由歐美10個國家的40位專家學者所撰寫的批判文集。此書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學派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它是對弗洛伊德學說創(chuàng)立及流行的一個世紀的總結。此書的作者們認為,精神分析不是科學的理論,也不是科學的治療方法。弗洛伊德及其后繼者有偽造資料以欺世盜名,貽誤患者而不正當牟利之嫌。此書主編卡特琳·梅耶爾(Catherine MEYER)女士的結論是:如果沒有弗洛伊德,人們可以更好的生活、思維和發(fā)展。給讀者呈上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jù)此書中譯本的部分內容寫出。
(《弗洛伊德批判——精神分析黑皮書》。[法]卡特琳·梅耶爾著。郭慶嵐、唐志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68.00元)
(本文編輯: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