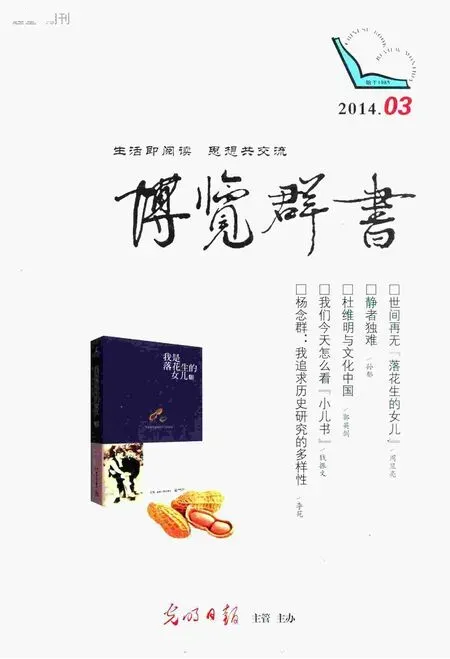如刃發(fā)硎 解剖透骨
張 煒
近些年來,關于民族國家是如何建立的這個問題,一直是中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從近五百年西方歷史發(fā)展經驗來看,只有當出現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形態(tài)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才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與促進,所以民族國家的建立問題同“崛起”與“富強”的世界近現代史主題緊密相關。就這一點而言,近代國家形成問題便具有了較強的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郭方研究員的《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16世紀英國國家機構與職能的變革》一書,以都鐸時期英國的政治制度變革為中心,對近代國家的形成進行了新的詮釋,從而在廣度與深度上推進了國內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在此,筆者愿將幾點閱讀心得與讀者分享。
首先,對于國家的機構與職能由中世紀型向近代型轉變的判斷標準,各國學者先后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觀點,因此,對轉向近代國家的標志問題歷來是較難取得一致意見的。我國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是千差萬別,就英國的情況而言,有學者將資產階級革命等同于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立;也有觀點認為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經過了都鐸王朝的“政府革命”、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9世紀政府革命三個發(fā)展階段,直至工業(yè)革命完成后才最終建成。但是,對于近現代國家應具備哪些條件,卻鮮有明確的論述。
郭方的這本書參考了眾多學者提出的標準,結合16世紀英國與西歐的現實,提出了近現代國家所應具備的八項條件,即:
領域國家、民族國家與政治國家應當達到基本的統(tǒng)一;
各機構及其職能在制度上與實際運作中,既應當是高度整合的,又應當是明確專職分化的;
國家的體制、機構和職能應當具有及時調節(jié)的功能,以使國家的目標和政策與國家經濟的發(fā)展變化相促進和相制約;
具有較為健全而為全國通用公認的法制,這種法制不應以宗教、神學或某種特定意識形態(tài)為準則,不應以統(tǒng)治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不應以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理論為依據;
隨著經濟社會情況的發(fā)展,在國家政治中具有開放的參與性;
在國家中有重大影響或據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應當有利于國家的獨立、團結、強盛,并應當具有隨著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自由開放性,而不應當成為國家民族進步的桎梏;
國家機構與職能的涵蓋面與功能要全社會化,以至達到國家與每一個國民有多方面的直接聯系,并且這種聯系具有互有權利與義務的雙向性;
武裝力量要屬于國家,忠于國家,遵照國家的法制行動。
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概述是否全面、得當,我們暫且不論,但是能夠將歷史學與政治學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喚起學界同仁進行認真思考,這便是極富價值的工作。唯有具備了較為明確的理論出發(fā)點,才有可能展開更深層次的討論,也才能避免無的放矢、自說自話的現象,使研究領域得以廓清,以致得出令人較為信服的論斷。
其次,該書對16世紀英國整體的經濟與社會狀況做了新的深入而細致的評估,對不同觀點進行了辨析,并進一步闡明了作者之所以選擇這一時段進行立論的依據。由于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是一個漫長而錯綜復雜的過程,在具體研究時又缺乏該時代全面而精確的統(tǒng)計資料,更存在著各種不同的估評標準,因此,要進行客觀而準確的論述,一如作者所言,就“必須抓住這類問題的某些要點與特點來分析其實質性的東西”。
對于16世紀英國的經濟狀況,英國幾位重要的經濟史家都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評價,普遍認為這一時期是英國經濟迅速變革的時期,工、農、商業(yè)發(fā)展模式都在發(fā)生深刻的調整。作者據此將16世紀初英國經濟這種顯著的變化進一步歸結為三大方面,即圈地、毛紡織業(yè)和呢絨貿易的迅速發(fā)展。對于這些因素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的規(guī)模,近些年來英美史學界頗有些翻案傾向,國內學界對此也出現了新的論斷。尤其在“圈地運動”方面,有學者依據當時圈地面積的相關統(tǒng)計數字。認為這一運動在英國展開的強度遠比想象的低。但這本書的作者援引英國史學家利普森、瑟斯克所提供的數據,指出雖然圈地面積所占百分比不大,但卻引起了強烈的反應,隱蔽在這個較小數字后面的是一個強大的勢頭,即“圈地運動在慢慢擴展后,已經向最困難的堡壘發(fā)動進攻,這標志著一種革命,新的經濟體制已經越過悄悄萌芽成長的階段,開始以一種可怕的姿態(tài)與舊體制正面交鋒了”,從而對圈地運動的實際影響予以充分肯定。
這個時期的社會和階級結構是一個更難把握的問題。在英美史學界,先后有學者提出“中產階級的出現”和“鄉(xiāng)紳的興起”等觀點,但隨后又遭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國內的相關論著對此也大多語焉不詳,采取了較為模糊籠統(tǒng)的表述方式。有鑒于此,郭方研究員指出,國外學者的上述爭論一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和分析,但在作翻案文章時卻常常混淆了某些個別與一般、量變與質變、現象與本質的區(qū)別,得出了一些更為片面的結論,因此有從根本上澄清某些問題的必要。作者從劃分階級的根本標準出發(fā),以“圈地運動”引發(fā)的“農業(yè)革命”著手,分析了其中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強調這個變革的主要受惠者是鄉(xiāng)紳階層,他們是社會結構變動中關鍵的階層。正是因為有了這支力量的崛起,才導致英國的社會結構出現了“突破封建結構的變化”。
同時,作者在“16世紀英國社會等級狀況例析”一章中,將國家機構與職能問題放在社會史視野中加以全方位檢視,指出16世紀的英國仍是一個貴族等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國家,而這個貴族等級對于在財富積累和參與政治方面的成功者來說基本是開放的,而且始終是流動而有限的,他們并不妨礙資本主義性質企業(yè)的發(fā)展。因而,作者認為了解這種新興的貴族等級制“是理解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這個相當長歷史時期的社會與階級、階層狀況的一個關鍵,也是深入了解一系列號稱‘改革與‘革命的政治斗爭與變革性質的一個要素”。像這樣經過作者審慎思考得出的鮮明觀點,相信會對我們進一步準確把握16世紀英國社會狀況帶來極大助益。正是對16世紀經濟社會結構的較為確切的判斷,為全書對這一時段狀況的把握和論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再次,這本書緊緊圍繞國家機構與職能的變革這一主題,所觸及的問題較為全面系統(tǒng),并可從作者的論述中體會到其獨具匠心的研究方法。關于這一時期英國政治制度的變化,國內學界近年來相繼產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對于開拓這一領域的研究著實具有積極意義,但大都存在敘述簡略之缺憾。相比而言,《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則為讀者提供了一幅關于此問題的較為全面的圖景,從中可以了解到國家財政制度、中央政府制度、司法系統(tǒng)與地方政府、近代議會、國家教會以及王權等多個方面的詳細情況。
讀者在比較全面地了解16世紀英國國家機構與職能變革的同時,還會感受到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別出心裁。這里僅就“英國財政制度的改革”一章略舉一例。16世紀初,鄉(xiāng)紳與工商業(yè)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已經對大部分王室收入具有了決定性影響,因此他們得以與王權進行聯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王權。出于對這一現象的深入觀察,英國財政史專家迪茨就以國王和小鄉(xiāng)紳與工商業(yè)中產階級的聯盟作為分析的出發(fā)點;憲政史專家埃爾頓在其名著《都鐸政府革命》中,也利用大量資料以宗教改革時期的財政制度變革為起點,對“政府革命”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這些研究都在都鐸史學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作者充分借鑒了其中可取之處,從分析王室經常性收入和非經常性收入的來源與消長人手,對王權尋求獲得財源的新方式與新策略進行了全面論述。通過這一分析角度,作者將這一系列財政機構與制度的改革的實質總結為“把作為最高封建領主性質的王室財政收支,轉變?yōu)檫m應于資本主義新經濟發(fā)展的系統(tǒng)管理的國家財政收支”。應該說這是對16世紀英國財政制度變革的深刻概括,同時也充分說明運用正確合理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以上是筆者僅就《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一書中最感興趣的幾個問題所作的簡要分析。總體說來,在從封閉型的自然經濟社會向開放型的商品經濟社會轉變過程中,國家機構與職能的變革情況是世界歷史上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也始終吸引著許多富有時代責任感的歷史學者的目光。郭方研究員從其鉆研多年的都鐸史的具體材料出發(fā),就一系列具體問題作了如刃發(fā)硎、解剖透骨的論述,提出了許多富于啟迪的觀點,《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是一部經過多年不懈努力后寫就的學術質量較高的著作。當然,誠如作者所言,書中許多章節(jié)的論述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由于各種原因的局限,這本書在吸納西方學者最新研究成果及運用第一手資料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充實完善,比如上文提到的對“圈地運動”翻案傾向的駁斥,如有更加具體的材料佐之,將會使立論更為有力。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以欣喜的態(tài)度面對這一關于英國政治制度史的全新力作,并真心希望學界有更多相關的著述問世,以將對上述學術問題的探討繼續(xù)深入下去,使其現實意義得以進一步彰顯。
(《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郭方著,商務印書館2006年9月版,15.00元)
(本文編輯: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