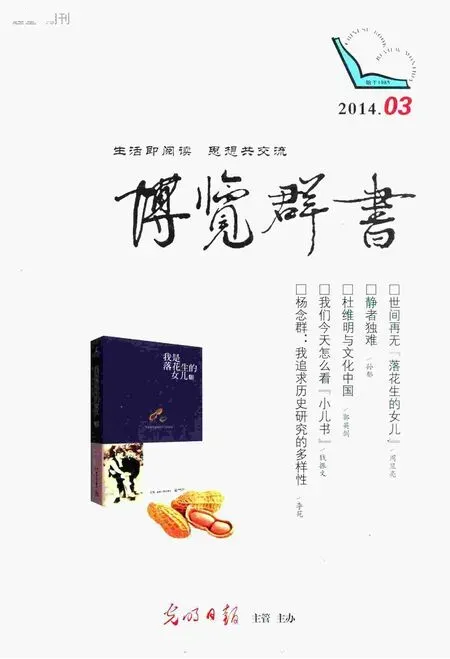子不語書譚
李 喬
怪、力、亂、神,孔子所不語也。即使偶談鬼神,孔子也持一種淡然疏遠的態(tài)度,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魯迅曾贊佩孔子說:“孔夫子生在巫鬼勢力旺盛的時代,卻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不語不談,敬而遠之,這是孔子的理性態(tài)度。后代的讀書人,或不談鬼神,或雖談而存疑,抑或借鬼神而影射人世。袁枚之《子不語》、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張南莊之《何典》,都是此類雖談鬼神而實則輕慢或根本不信鬼神之作。近代科學昌明以來,特別是唯物主義勃興之后,鬼神成了可供隨便研究、質(zhì)疑和指斥的東西。特別是“五四”以來,隨著學術界眼光的愈加往廣處和低處看,談鬼神的著作更是多了起來。我留心搜集過這類著作,得二三十種之多。覽讀之余,略做讀記數(shù)篇。
鬼神的實用性
南開大學教授侯杰與夫人范麗珠合著了一本《中國民眾宗教意識》(以下簡稱《意識》),因知我研究過民間信仰,遂郵賜大著請我“教正”。我認真拜讀了此書,寫了下面一點讀書筆記。
讀此書時,我總是不時地生出慨嘆:誰要是有能耐把紛繁雜亂的中國民眾宗教信仰的史實梳理清楚,再加以理論上的科學解說,那他可真是有本事的人。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向來以源頭眾多、崇拜對象紛繁復雜而著稱,千百年來已積為一筆剪不斷,理還亂的糊涂賬。孔子何以不多談鬼神?宋朝文人周密解釋說,這是因為“有未易語者”。鬼神之事的確不易談,特別是民間的。我想,在這方面,若是能將史料理出頭緒來,已屬不易,而若能加以理論說明,就尤為不易;若是能做專題研究,已屬不易,而若能做綜合研究,就更為不易;若能使讀者獲得民間宗教信仰史的正確知識,已屬不易,而若能將研究這種歷史現(xiàn)象的科學結(jié)論交給讀者,就更加不易。《意識》一書,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這當中的許多難題。
“民眾宗教意識”這個概念用得好。它的涵蓋面極廣,把民眾中一切宗教信仰方面的心理、觀念以及相關行為都概括進去了。本來,中國民間有無宗教,哪些現(xiàn)象算是宗教,那些又算是有宗教意味的信仰,乃是“核心明確而邊圍含混”(《管錐編》引近人論分類語),而這正反映了民間宗教信仰的特點。《意識》的作者看到了這一點,故而有意識地跳出了“非此即彼”(是否宗教擇一)的思維模式,而采取了一種閎通的眼光,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反映事物,從而網(wǎng)羅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宗教性”事象作為認識對象,諸如信灶王、信鐘馗、講禁忌之類,確立了自己的民眾宗教信仰史研究格局。一部學術史其實也就是一部發(fā)明和運用概念的歷史。《意識》一書的成功甚得益于“民眾宗教意識”這一概念。概念是研究的起點,也是研究的結(jié)晶。我猜度,《意識》的著者在研究工作初始時,一定是細細地推敲過“民眾宗教意識”這一概念的,然后又通過對歷史現(xiàn)象的研究,充實和坐實了這一概念。
我一向感到,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根柢,全在“務實”二字,換句話說,就是鬼神是具有實用性的,供他是為了用他。這是一條大經(jīng)絡,以此可以解釋眾多的民間宗教信仰的現(xiàn)象和特性。早年我研究行業(yè)神崇拜時,曾經(jīng)觸及過這條大經(jīng)絡,但僅局限于此一隅,并沒有做過全面性、綜合性的研究。《意識》一書則在此方面下了大氣力,且多有創(chuàng)獲。著者說:“中國民眾宗教意識的中心可謂趨福避禍。”這句明快的斷語,在書中有大量的史證作支持。本來是極端出世型的佛教,何以在民眾信仰中變得富有人間煙火味?著者告訴我們,這是民眾宗教意識的務實特性促使佛教世俗化的。觀音的香火為何盛過釋迦牟尼?因為觀音熱心凡間瑣事,務實的民眾更需要“她”。民眾為何要給灶王娶妻,給神仙過生日?因為在務實的民眾眼里,神靈也是需要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總而言之,對于鬼神完全采取“供之為用之”的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這便是“務實”二字的真諦。對于民眾宗教意識之務實特性的總根源,著者有一句話可謂將其說透:“農(nóng)業(yè)文明成為民眾宗教意識的第一個搖籃。”同時又指出,儒家理性傳統(tǒng)的影響,也是形成這種務實特性的重要原因。這些論述,大大深化了我對“務實”二字的認識。
我讀的《中國民眾宗教意識》是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的第一版,后來又出了修訂本。我沒讀過修訂本,想來修訂本會比初版更好。
義和團從小說里請來了神
朋友向我推薦了一本書,說此書獲得過幾項大獎——費正清獎、列文森獎和加州大學伯克利獎,書名叫《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覓來一看,竟是一位名叫周錫瑞的美國學者寫的。
細讀這本書之前,我猜度這可能又是一本不脫近代史著述老套子的書,所談內(nèi)容大概也就是些義和團如何反帝或排外之類的老話題。讀后方知不然。原來,這是一本視角新,結(jié)論新,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此書所取的新視角,很大程度上是社會風俗史視角、民眾文化史視角,這就涉及很多民間信仰和法術方面的內(nèi)容,所以我把它也看作是一本關于中國民間信仰的著作。這個視角,對于科學地說明義和團的起源等許多問題,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關于《起源》這本書,可說的話很多,我只想根據(jù)自己的興趣說一點——這是一件小說影響歷史的個案。說小說影響了歷史,乍聽起來匪夷所思,其實,這在舊時代實屬平常之事。魯迅先生曾說,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shù)靠著小說和從小說編出的戲文。這也就是說,國民是靠著這種小說所提供的學問去行事,去參與書寫社會歷史的,這不正是小說影響了歷史嗎?張恨水先生還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民間一切秘密結(jié)社,無不受《水滸》之賜。施耐庵一枝筆,支配民間思想四五百年。這話說得很深刻,也很有趣,更反映了事實。這個事實就是《水滸》《三國》等舊小說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民眾,進而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面貌。
關于小說能影響歷史,我在做行業(yè)神崇拜研究時,便有過深切的感受——我國百業(yè)所奉的祖師爺中,很多都是從舊小說中請出的人物。現(xiàn)在讀《起源》這本書,更強化了我原有的認識。從周錫瑞的研究看,義和團運動從起源到許多具體行為,都與舊小說的影響有極深的關系,這無疑說明了小說曾經(jīng)影響了義和團。同為小說影響歷史的個案,祖師崇拜的案例是頗為局狹的,也并不那么重要,而義和團的案例則很宏觀,也很重要,因為這還是一個“小說影響了一場民眾運動”的個案。
周錫瑞舉出的大量史料表明,義和團曾經(jīng)從小說戲曲、民間信仰、武術拳法等民間文化中得到過最初的啟發(fā)。這也就是說,義和團的原始萌芽,是借助過小說和從小說編出的戲文之力的。《三國》《水滸》《西游》《封神》這幾部小說,曾經(jīng)對義和團的信仰及行為方式,發(fā)生過至深至巨的影響。可以說,義和團是充滿了“三國氣”和“水滸氣”,以及“西游氣”和“封神氣”的。對此,《起源》中的論述頗
多,如“義和團所請的神五花八門,均來自戲文小說中的英雄好漢,有孫悟空、豬八戒,《三國演義》里的關公、趙云、周倉,《封神榜》里的毛遂、孫臏、楊戩等等。”周錫瑞認為,這形形色色的小說人物,為拳民們的“降神附體”行為,提供了“敘述背景”。所謂“敘述背景”,也就是拳民們奉神所依據(jù)的“文化材料”。“敘述背景”之說,是支撐周氏義和團起源說的有力證據(jù)之一,同時也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幕小說影響歷史的史劇。
在舊時代,統(tǒng)治者經(jīng)常查禁小說戲曲,他們?yōu)榇税l(fā)布過許多諭旨、法令。北大王利器先生曾搜集有關史料,編過一冊《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究其查禁小說戲曲的原因,除了為防止所謂“有傷風化”以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擔心有些小說具有鼓動民眾騷亂、造反的“煽惑力”。《起源》一書揭破了這一點,論道:“滿清一代統(tǒng)治者鑒于小說與民眾騷亂間的聯(lián)系如此明顯,遂下令查禁這些具有顛覆性的文學作品。”對這個論斷,周先生是以大量的義和團史料做證據(jù)的。我想,若是有誰想了解一下某些舊小說的所謂“煽惑力”和“顛覆性”,義和團這件個案是不可不查的。
梁啟超曾倡言過“小說革命”,因為他覺得舊小說對民眾的不良影響太大。他認為,中國人的江湖盜賊思想、妖巫狐鬼思想、堪輿、相命、卜筮、祈禳、闔族械斗、迎神賽會等等思想和行為都來自小說。關于歷史上小說對于中國民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是好影響多些,還是壞影響多些,我想,還需要經(jīng)過細致的研究才能下結(jié)論。但是,單就影響力或曰煽惑力而言,梁啟超的看法無疑是對的,《起源》一書則更是用大量的史實證明了小說對于民眾的影響力之巨大。
犯人與獄神
我因為研究行業(yè)神,對獄神做過一點研究。某日,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書評,是評論《中國神秘的獄神廟》(以下簡稱《獄神廟》)一書的,頓感興奮而又奇怪:這么一個小小的鮮為人知的神靈,竟有人寫出了一本專著!著者叫張建智,湖州人。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題研究獄神和獄神廟的書。
獄神之引起人們的興趣,大概緣起于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時,研究了有關獄神廟的脂批。《紅樓夢》寫了獄神廟,賈寶玉仿佛也進過獄神廟,這就引得人們非要弄明白獄神和獄神廟是怎么一回事不可。我研究獄神當然不是為了研究《紅樓夢》,而是為了研究行業(yè)神崇拜。我認為在獄吏和犯人這兩類獄神祭拜者當中,獄吏祭獄神是具有行業(yè)神崇拜性質(zhì)的。我僅僅從這個角度研究了獄神。張先生的研究則是一種全面性的研究。
這本《獄神廟》的寫法有些特別。序文作者曾彥修先生介紹說:“全書(或全文)共八十小段,不置章節(jié),全以隨筆方式出之,夾敘夾議,看起來不易枯燥。當然,用此方法,難免就有些離題頗遠的文字。”一分為二。好處還是第一位的。用這種寫法寫,我想,大抵是出于一種無奈,因為獄神廟的材料太少了,寫成長篇大論的章節(jié)體幾乎不可能。我佩服張先生的聰明,他發(fā)明了一種用隨筆體寫作學術著作的方法。我看這是一種創(chuàng)體。古人當然用類似的筆記體寫過學術著作,如顧亭林的《日知錄》之類,但若張先生這種以八十段隨筆體長篇來談一個學術問題的著作,卻似乎從沒有見過。張先生是個老實人,書中在引述拙著《行業(yè)神崇拜》里提供的資料時,特別做了說明,以示不掠美之意。但實際上張先生對獄神的研究,實在是比我深人多了,特別是他對犯人祭獄神的心理的研究,我不僅沒有涉及過,而且了解很少。《獄神廟》給我補了這一課。
古代監(jiān)獄為什么要設置獄神廟?簡而言之:神道設教。獄神廟,并不是宗教界所設置的,也不是犯人要求設置的,而是政府設置的。設置獄神廟,是為了獄政的需要。具體說,就是為了教化犯人和獄吏,教化犯人要認罪服法,教化獄吏要辦好獄事。關于對犯人的教化,《獄神廟》里有一句總結(jié)性的話:“秦漢至清末民初,縣級行政單位監(jiān)獄中構(gòu)建有獄神廟,目的是‘恐嚇和震懾囚犯。”用獄神來恐嚇與震懾犯人,此為古代監(jiān)獄對犯人的“獄神教化法”。
最早的關于犯人祭獄神的記載,見于《后漢書·范滂傳》。記云:漢代名臣范滂被捕入獄后,獄吏下令說:“凡坐系皆祭皋陶。”范滂回答說:“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獄吏只好作罷。可以看出,獄吏本是想行教化之責的,想拿獄神皋陶來震懾范滂,讓范滂認罪服軟,哪知范滂是條硬漢,根本不承認有罪,所以也不想求獄神保佑;而且范滂還認為,即使真有罪,祭神又有什么用?像范滂這樣的不祭拜獄神的犯人,在古代還真是不多見的。
《獄神廟》將犯人大別為死刑犯和徒刑犯兩大類,并總結(jié)了他們各自祭拜獄神的目的和心理:“判了死刑的,怕死后上蒼還要罰他受罪,他們請求獄神在上蒼面前多說好話,下了地獄,不要再懲罰他,也便是說為自己的亡靈超度。”徒刑犯,“在獄神面前表示懺悔,表示認罪,請求對他寬恕,祈告獄神,能賜他們早日出獄,與家人團圓”。這些概括,當然都是言之有據(jù)的,所依據(jù)的歷史資料,主要是取自古代的小說和戲曲。小說、戲曲是有證史的功能的,特別是對于考察古人心理,尤其有參考價值。
關于死刑犯祭拜獄神,《水滸傳》上有這么一段:獄卒把宋江、戴宗二人“驅(qū)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辭了神案,漏轉(zhuǎn)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后,推擁出牢門前來。”這個青面圣者,便是獄神。但這個獄神已不是范滂時代的皋陶,而是漢臣蕭何。
關于非死罪或尚未定罪的犯人祭拜獄神的情況,《獄神廟》提供了不少材料。小說《果報錄》第六十七回有唱詞道:“行來已到蕭王殿,爐內(nèi)香煙淡淡飄。(白):咦!那監(jiān)牢里也有神道個(咯),讓我許個(這)個愿心介(吧)……讓神保佑小姐平安離獄底,愿得香燭殿前燒。”這是一個犯人家屬在祈求獄神保佑犯人早日出獄,平安回家。京劇《玉堂春》里蘇三的唱詞道:“待我拜拜獄神爺爺,才好起身……獄神爺爺聽我言,保佑蘇三得活命。我與你重修廟宇換金身。”這是一個可能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祈求獄神保佑自己活命。
小文寫到這里,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文革”時的秦城監(jiān)獄以及大大小小的大有牢獄之風的牛棚。那些地方,曾經(jīng)關過無數(shù)范滂、蘇三式的所謂“罪犯”和“罪人”,他們每天都要向領袖請罪,認罪,請求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我恍然覺得,這景象與古時的祭拜獄神,不是頗有幾分神似么?那場造神運動的荒唐性,于此可見一斑。談古代獄神,競談到了現(xiàn)代,這是巧合呢,還是歷史邏輯的暗合呢?我想,都有些吧。
旅人的迷信
研究古人的迷信,不能放過研究古代旅行史,因為旅人的迷信較之安守在家者,不知要嚴重多少倍。古代旅人的迷信,乃是古代社會迷信狀況的一個重要個案。
宗教學家、民俗學家江紹原所著的
《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是一本研究古代旅人迷信的專書。這本書原計劃要寫六章,但只寫了第一章,題目是《行途遭逢的神奸(和毒惡生物)》,從這個題目可以看出,作者研究的重點是古代旅人對旅途上神鬼精怪的迷信。此書最早由商務印書館于1937年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于1989年影印了此書。
考察古代旅人的迷信狀況,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材料極少。江紹原解決此問題的辦法是尋覓可以視作“旅行指南”的材料,他認為,古代的“旅行指南”中必包含有不少關于旅人迷信的信息。他認為,古代青銅器上的某些與旅途有關的圖像和上古奇書《山海經(jīng)》,可以視為上古的“旅行指南”。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這類圖像和《山海經(jīng)》的許多內(nèi)容,與地理方物、旅行見聞有關,盡管其中許多圖文看似光怪陸離,荒誕不經(jīng),但實際上卻是古代旅人對于旅途艱險的一種扭曲的和夸張的記述,其中所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實際是旅人因恐懼而想像和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旅人迷信觀念的產(chǎn)物。
關于青銅器上的與旅途有關的神鬼精怪圖像,江紹原說:“行途的,或遠近各方的毒惡生物和鬼神精怪,相傳在很早的時代便不但有,而且有了大規(guī)模(包括多物與多地)的圖畫表現(xiàn)。”可知旅人對于神鬼精怪的迷信,不但起源很早,而且廣泛存在而興盛。據(jù)江紹原推測,古傳說中的“夏鼎”上面,就可能畫有這類圖像。證據(jù)是《左傳》所記王孫滿向楚子說的關于“夏鼎”的話:“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順);螭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xié)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江紹原解釋說,古人認為,進入川澤山林,必會碰到螭魅魍魎等鬼神精怪,而這些鬼神精怪的形狀各不相同,不便記憶,便要畫成圖像,以供觀覽了解,供出入山林之用,于是“夏鼎”之類的器物上便鑄上了這種圖像。他又解釋說,即使“夏鼎”未必真有其物,但《左傳》所記的王孫滿的話,“仍反映了史前和有史、文字前和有文字時代的人們,要求旅途神奸圖或云圖畫式旅行指南之心。”也就是說。關于“夏鼎”的傳說,實際上反映了古代旅人對“旅行指南”的需求。
對于《山海經(jīng)》可以視作“旅行指南”的理由,江紹原從分析《山海經(jīng)》所記的古神話、古異聞人手,將這些古神話異聞分成五大類:1、種種于人有害的動植物和其他神物;2、與風雨有關的山岳和神人;3、神靈的形狀和祭祀神靈的方法;4、有利于人的動植物和異物;5、奇形怪狀的異方之民。然后推斷說,“此五項正是行人所不可不知,旅行指南所不可不載”的。據(jù)此,他認為《山海經(jīng)》也是可以視作“旅行指南”的。作為“旅行指南”,《山海經(jīng)》上所記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和毒惡生物,實際上都是古人認為在旅途上會遇到的,并需要旅人特別加以注意和應付的。
旅人的迷信,何以會比安守在家者要嚴重得多?這源于古人對旅途的深深的恐懼。恐懼生迷信,迷信生(造出,想像出)鬼神。所謂“行途遭逢的神奸”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古代特別是上古,交通極為不便,旅途上艱險甚多,旅行環(huán)境極為惡劣,而旅人對于這種艱險環(huán)境的抗御能力又極弱,這便使旅人產(chǎn)生了深深的恐懼,進而造出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對于古代旅途之艱險,江紹原這樣描述道:“言語風尚族類異于我,故對我必懷有異心的人們而外,蟲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谷、大河急流,暴風狂雨、烈日嚴霜、社壇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遠人。”其中,除了“神鬼妖魔”,都是旅途上會經(jīng)常遇到的艱險,而“神鬼妖魔”則是這些艱險給旅人帶來的恐懼和迷信心理的產(chǎn)物。《西游記》里寫了許多妖魔鬼怪,實際也都是旅人的恐懼和迷信心理的產(chǎn)物。
一位研究宗教史的法國學者說過一句精辟的話:“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夠幫助解放人的心靈。”江紹原對于古代旅行迷信的研究,就具有破除迷信、解放迷信者心靈的作用。這其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就像猜謎語,謎面雖然總讓人覺得不易捉摸,甚至有點神秘,而一旦弄清謎語是怎么造出的,謎底又是什么,那種神秘感也就蕩然無存了。
(《世俗與神圣——中國民眾宗教意識》(修訂版),侯杰、范麗珠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26.80元;《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美]周錫瑞著,張俊義、王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5.00元;《中國神秘的獄神廟》,張建智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10.00元;《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影印本),江紹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