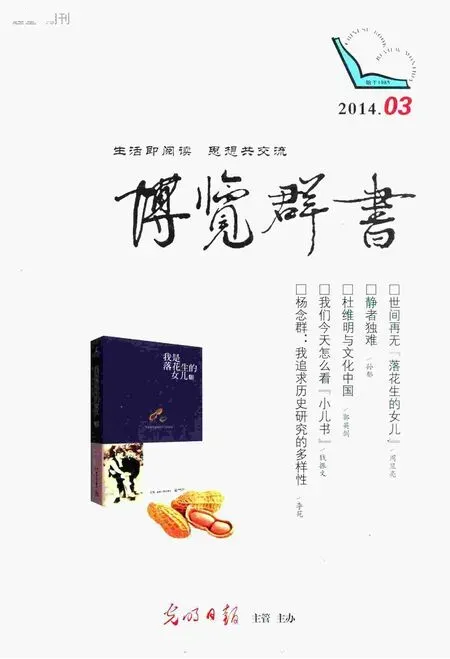讀《一個人的吶喊》札記
周楠本
2006年我寫過一篇關于左翼文學的文章,涉及到“左聯”五作家遇難事件,當時所見材料有限,認識水平也有限,無法進行更深透一些的探討。不久前讀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朱正先生的《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當時即感到這是一本在學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的著作。這本書充分運用了近年來新出現的有關魯迅及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同時又征引了從舊籍典藏里發掘出來的一些前所未見的珍貴史料,解決了許多學術上遺存的疑點、難點問題,特別是澄明了一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實。“左聯”五作家遇難事件就是其中的一個顯例。作者在序言里說:“我寫的魯迅單獨一人的傳記,算來已有四本了。可是沒有一本是能夠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現在寫的這一本能夠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寫的各本,進步是很明顯的。這進步首先要歸功于時代的進步。只說書中所用的資料,許多都是近年才出現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沒有這些……而我的主觀條件也可以說有了一些改善,在這些年里,又多讀了一點書,增加了一些閱歷。對魯迅的一生事跡,自以為大體弄清楚了。拿這本書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對照來看,有些說法是完全不同了。”我想我這篇閱讀札記就按照作者說的,采用對讀的方法,這樣既可以看到書的進步、時代的進步,又可以看到一種治學的方法和精神。
一、關于“左聯”五作家遇難事件
五十年前作者寫出了他的第一本魯迅傳,即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傳略》。這本書關于“左聯”五作家遇難事件是這樣寫的:
反動派像害怕革命人民一樣害怕革命文藝……為了想消滅革命文藝。反動派不惜用了最末的卑劣的手段,動手來殺害革命作家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作家、共產黨員柔石、胡也頻、白莽(殷夫)、李偉森、馮鏗等五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了。經過多方營救,但是沒有效果,二月七日深夜,這五位作家和另外十八位革命者一道,在上海龍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里被秘密槍殺或者活埋了。(第145~146頁)
二十六年后,作者于1982年又出版了修訂本《魯迅傳略》(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修訂本對“左聯”五作家遇難事件的論述與五十年代的說法就很不同了:
為了堅持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反對王明集團,同時為了使黨的工作不陷于內部辯論之中而將革命繼續向前推進,反對四中全會的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羅章龍等人于一月十七日在上海東方飯店召開一次黨內會議。當時李求實負責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請了持有相同觀點的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到會。當會議開到一半時,工部局就突然包圍會場把所有與會者逮捕了。除了在東方飯店一地外,搜捕還在其他幾個地方持續進行了兩三天。(第268頁)
書中在這段論述之后還加了一個注釋,引用了四中全會參加者、中共六屆中央委員羅章龍的《上海東方飯店會議前后》一文,指出這次慘案與王明集團有關系。修訂本披露了此案涉及到黨內斗爭,應該說這是一個大的突破。
從1931年到1982年過去了五十年。人們對于這一段歷史已經開始有了新的認識,但徹底澄清史實,還需時日,還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資料公之于世。
2007年新版魯迅傳《一個人的吶喊》,是作者又經過了二十五年長時間的思考、研究之后的收獲。關于“左聯”五作家遇難案,新版本已經拿出了足以使事情真相能夠大白于天下的資料了。1982年本《魯迅傳略》只能用很短的一段文字將事情作一交待,而《一個人的吶喊》則用了“柔石之死”一個章節來講述,并且語必證實,完全依靠史料進行闡釋。書中引用了羅章龍回憶錄中的最新資料,此案的禍根確為共產國際操縱的四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王明甚至還成為了政治局委員。出席會議的許多中央委員當時即表示抗議,群起集體退席。會后,羅章龍、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聯名致信米夫,再次聲明會議非法,應宣布會議所有決議及選舉結果無效,強烈要求采納多數中央委員的意見,重新召開緊急會議,或召開中共七大,解決黨內分歧。米夫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邀約反對四中全會的人在上海靜安寺路地區的一所花園洋房里開會,企圖將事情壓制下來。在這個后來稱為“花園會議”的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沒有達成妥協,“最后,隨同米夫前來的一個外國人說:‘我們對于今日會議完全感到失望,這證明你們是有組織、有綱領地來反對四中全會,已經走向反國際反黨的道路。你們反對四中全會領導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務,一律開除中央委員和黨籍!說罷,米夫等三個外國人就怒氣沖沖地踉蹌下樓而去”(第262頁)。
書中還寫到散會以后的一個重要細節:三個國際代表走之后,顧順章在會場出現了,他要求大家在會場里再住一夜,說外面有警情,如果走難保安全,并且將門上鎖,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覺他不懷好意,就沖破他的阻攔,分批離去。事后了解,顧順章是奉命留難,這說明當時米夫就已經計劃消滅這些反對派了,如果反對分子不就范的話。
“花園會議”在整個事件中比四中全會更為嚴重,它已經顯露了殺機。這個會議在1982年版《魯迅傳略》里沒有提到,當然是由于資料缺乏。
“花園會議”清除異己的計劃未能得逞,那是1月10日的事情。可是一個星期以后,1931年1月17日,“非委”(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在三馬路東方飯店原蘇準會所租的房間里舉行擴大會議,整個會場已經被大隊英租界工部局老閘捕房巡捕及中國政府便衣警察五十余名包圍,參加會議的人全部被捕,計二十九人。當晚和第二天又在別的地方抓了李求實等十二人。(第263頁)這里新版本訂正了1982年版《魯迅傳略》里寫得不準確的一個地方,即羅章龍和史文彬臨時有事并沒有出席此次會議,因而死里逃生;李求實當時也沒有在場,他是在別處被捕的。
地下黨如此重要的一次重要干部會議,不是內部人出賣,國民黨當局不可能這樣穩準狠地進行連續打擊。也許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國民黨當局的這種“鼎力相助”,四中全會所產生的臨時中央能否控制全黨,尚是個未知數。現在只有一個疑問:誰是告密者?當年的幸存者羅章龍提供了當時就已經引起人們注意了的重要線索:“對此一般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顧順章打電話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種說法是一個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學生與龍華慘案有關。此人叫唐虞,他與王明很要好”(第263頁)。這兩種說法都與王明集團直接有關。羅章龍的這個重要回憶,1982年版《魯迅傳略》也寫進注釋文字里了。
書中還披露了一個至今不大為人所知的事情,就是“左聯”五作家在當時已經是羅章龍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簡稱“非委”)所屬的“中國革
命文藝聯盟”(簡稱“革文聯”)的成員;并且,馮鏗還是“非委”候補委員。(第263頁)這說明“左聯”五作家是以“非委”組織成員的身份參加上海東方飯店秘密會議的;“左聯五烈士”,實際上應該是“革文聯”五烈士。但1982年作者在修訂《魯迅傳略》時,尚未掌握這個資料,所以那時這樣寫道:“當時李求實負責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請了持有相同觀點的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到會。”
關于這一慘案作者最后總結說:
1月17日在東方飯店被捕的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秘密處死了。他們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領導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還有非委革文聯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頻,還有非委候補中委、非委婦女部的馮鏗。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頻、馮鏗和李求實(又名李偉森)原是“左聯”的成員,他們就被稱為“左聯五烈士”。事實上,他們并不是在“左聯”的活動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殺的。他們其實是中共一場黨內斗爭的犧牲者。據羅章龍的回憶錄中說,“后來臨中(臨時中央,指六屆四中全會所產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認何(孟雄)等二十三人為反黨,為叛徒,公然宣稱他們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才作了這樣的結論:
至于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干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并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這里把馮鏗、柔石、殷夫、胡也頻也都算在“黨的重要干部”之中。求仁得仁,他們可以死而無憾吧。(第268頁)
關于營救被捕人員問題,第一本《魯迅傳略》沒有寫。1982年本也只是寫到丁玲和魯迅的營救。《一個人的吶喊》不僅寫了丁玲和魯迅進行營救,而且首先寫到了“非委”進行了營救。正當臨時中央宣布被捕的共產黨人為叛徒之時,“非委”中央卻積極進行營救,責成史文彬等人籌措營救款項,并且先通過關系給被捕者送去了食品和衣物。
此時非左翼人士對被捕的共產黨人也給予了熱心關愛。胡適1931年1月20日的日記說:
沈從文來談甚久……其中有一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第266頁)
胡適感到為難是實情,但他還是致信蔡元培,請他設法。2月20日蔡給胡回信說:
適之先生大鑒:
自京回滬,大駕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囑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岳軍設法,然至今尚未開釋也……(第267頁)實際上丁玲、魯迅在營救力度上也不可能超過沈從文和胡適,他們也只能做到此種程度了。丁玲去找過邵力子,邵即去信張岳軍請其設法;魯迅去找過蔡元培,卻未遇見。
雖然事實證明所有的營救都無濟于事,然而即使營救成功,等待“叛徒”的下場又會是什么呢?事實上“叛徒”們未入獄時,他們的結局就已經被注定了。
在四中全會上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的瞿秋白。由于接受批判,承認錯誤,并且違心地發表聲明與羅章龍等劃清界限,因而當時沒有受到進一步制裁。他的最后命運《一個人的吶喊》中寫到了,這是在四年之后的事情:
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10日晚,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率領紅軍主力及后方機關八萬六千余人向西突圍,開始了歷史上所說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瞿秋白可是沒有能夠獲準隨隊突圍。1943年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寫的筆記《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說:
關于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我記得他們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干部數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單交他們批準。至于高級干部,則一律由最高“三人團”決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第320頁)
正如書中所說,紅軍大隊撤出江西蘇區的時候,瞿秋白沒有能夠獲準隨隊突圍,留在原地堅持游擊戰爭,這對于一個文弱書生、嚴重的肺癆患者來說,他最后的結局是已經決定了。此時瞿秋白內心是明白的。他終于與因反四中全會而殉難的烈士們殊途同歸了。
不過,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在極其險惡的形勢之下從上海調到江西蘇區去,并非王明集團所為。《一個人的吶喊》中引用了陳瓊芝訪問馮雪峰的談話記錄,馮雪峰說:
一九三三年末,我擔任中央蘇區黨校教務主任,黨校校長是張聞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幾位中央領導閑談,談到一些干部的人選,當時我也在場,他們談到有人反映蘇區教育部門的工作有點事務主義。張聞天想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問我他能不能來。我說他是黨員,讓他來一定會來的。后來由我起草了電報拍到上海,秋白就服從黨的決定到蘇區來了。議論中,博古認為也可以讓魯迅來擔任這個職務,說魯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經驗。后來我向毛主席講起,毛主席是反對這種意見的,他說:“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第319頁)
顯然,當時博古認為這個職位安排魯迅更為理想,尤其是當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剛剛作出《中央關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1933.9.22)的時候,那時王明集團宣稱開展對瞿秋白的批判是取得反五次“圍剿”戰爭勝利的一個保證;在這個節骨眼上啟用瞿秋白,博古不會是很情愿的。可惜歷史是無法改寫的,如果當時博古執意反對瞿秋白赴江西蘇區就任教育人民委員一職,那么瞿秋白可能就會與魯迅一樣,“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了。
二、關于“兩個口號”論爭
馮雪峰參加了長征到達陜北,之后奉中央命令回到上海工作,附帶還管一管文藝界的事情。他到上海不久即引發了著名的兩個口號之爭。
關于此事,1956年本《魯迅傳略》是如何闡釋的呢?下面摘錄幾段話就可以看出它的時代局限了:
暗藏在左聯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風利用革命文藝界工作中的缺點鉆空子,進行破壞活動。(第173頁)
由于胡風的興風作浪,一時革命文藝界內部發生了一些問題。本來毫不沖突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這兩個口號竟引起了爭論。(第174頁)
八月間,魯迅發表了長篇論文“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篇論文中間雖然有因為胡風的蒙蔽而對某些情況的誤會,但是總的精神是完全正確的。(第174頁)
這里當然不會有任何事實來說明問題,一切罪責都加在了已經成為反革命分子的胡風身上。不過有一點可以注意,
就是這本書出版時(1956年底),反右派運動還沒有開始,所以由馮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這篇文章還能夠說它“總的精神是完全正確的”,即使有點瑕疵,也是“因為胡風的蒙蔽”所致。這比1957年版《魯迅全集》的注解還接近事實一點。
關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新口號的提出,1982年本《魯迅傳略》是這樣寫的:
魯迅在馮雪峰和胡風的參預討論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作為當前文學運動的口號。(第351頁)
因為病,當時魯迅沒有能夠自己寫文章。直到后來發表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才第一次用他自己的名義提出這個口號來。(第353頁)
這其實基本上是依照《答徐懋庸》這篇文章以及馮雪峰的回憶文章的口徑。對于新口號提出的過程,則是依據茅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記錄稿進行闡述的。實際上茅盾并不是當事人。
《一個人的吶喊》也引用了茅盾的回憶,但此處僅引了他談“國防文學”來源的一段話:
我曾聽到夏衍講,“國防文學”的口號是根據當時黨駐第三國際的代表王明在《救國時報》上寫的一篇文章和第三國際出版的《國際時事通訊》上的文章而提出的。我問周揚是不是這樣,周揚說是的……(第345頁)
“國防文學”的提出者王明本人證實了這一點。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說:
周揚以及中國共產黨左翼作家聯盟黨團中的其他一些人,1936年初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的根據,是1935年8月1日為進一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發表的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其中宣布了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的口號。(第346頁)
“國防文學”口號的來源是沒有爭議的,而關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問題就要復雜一些。在1982年本《魯迅傳略》出版多年之后,胡風的回憶文字陸續發表出版了,新的著作有條件采用更可信的第一手資料了。1991年《上海魯迅研究》(5)發表了胡風于1977年在監獄里寫的《關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魯迅有關的二十二條提問》一文。(此文刊登后還有一點曲折,這一期《上海魯迅研究》印成后當時卻禁止發行銷售,因為九十年代初還有人不愿意真相大白。)胡風在這篇材料里說明:馮雪峰到上海后,認為“國防文學”不好,于是授意他寫文章,這樣新口號就通過他所寫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一文提出來了。
胡風這篇材料還說明了《答徐懋庸》一文其實是魯迅為顧全大局而作:
后來問題鬧大了,周揚夏衍們組織大圍剿,馮雪峰才請魯迅公開答復徐懋庸,并請魯迅聲明是魯迅提的,請我寫了文章。這是為了抵抗周揚夏衍們的攻勢,好像為我解脫,其實是為他自己在“上海文藝界地下黨組織”即周揚夏衍們里面受到的圍攻解圍。為顧全大局,魯迅只好承擔了這個責任。(第356頁)
原來,新口號本來與魯迅關系并不太大。胡風的材料既糾正了茅盾所說,同時也訂正了馮雪峰所說,包括《答徐懋庸》一文中的說法。
由于魯迅逝世及后來形勢的發展,這場論爭不了了之。但是,二十年之后,1957年反右派時,周揚等人已經飛揚跋扈,他們無所顧忌地干脆否定了魯迅的《答徐懋庸》這篇文章,讓馮雪峰承擔欺騙魯迅的責任。已被打成右派的馮雪峰,只能私下與友人訴說委屈。吐出了實情。《一個人的吶喊》(第346頁)引了“文革”時樓適夷寫給黃源的信:
馮雪峰對我說過,“民族解放戰爭文學”這個口號,實際是馮從陜北帶來的,魯迅先生接受了這個口號,加上了“大眾”的字樣。這件事還是在反右以后私下說的,他一直不敢公開說這個話。(見《黃源樓適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上冊,第3l頁)
現在事實已經清楚,馮雪峰執行的是遵命文學,他只聽從來自陜北中央的命令,并不直接奉行共產國際的旨意。馮雪峰私下與友人吐露真情的話與胡風所寫的材料得到了互相印證,證明了胡風和魯迅只是站在臺前的人物,幕后指揮者是陜北來的特派員馮雪峰。
盡管魯迅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作了合理的解釋,但其理論根源與“國防文學”一樣,同是出自第三國際。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說:
事實上這兩個口號都是根據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
魯迅等人于1936年5月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時,所依據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日軍9月18日侵占沈陽而發表的宣言。宣言提出了武裝民眾進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
周揚和魯迅據以提出各自的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口號的上述兩個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由王明撰寫的;其中的兩個口號,也都是由王明提出的。(第346頁)
讀了《一個人的吶喊》才知道原來這兩個如此對立的口號卻有著這樣的親緣關系,這恐怕不單是現在的研究者,就是馮雪峰、胡風、魯迅他們本人當年都未必意識到這一點吧。對王明的話,作者分析說:
看一看王明所說的他撰寫的兩個中共中央文件的歷史背景就明白了:《九一九宣言》是共產國際執行“第三時期”理論時候的文件,反映的是“第三時期”的理論;而《八一宣言》已經是由“第三時期”轉變為“人民陣線”時期了。這兩個時期對于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的提法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從這個大的背景來看,兩個口號之爭可以看作是由“第三時期”轉入“人民陣線”時所引起的一點新舊之爭。周揚、夏衍這些黨的干部,當然緊跟著共產國際路線的轉變而轉變,而魯迅,卻仍然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立場,有點跟不上路線的轉變了。(第346~347頁)
可以說,不僅是魯迅有點跟不上這種新舊路線的變化——這在他對待解散“左聯”的態度上早就表現出來了,就是陜北的中共中央,在接受和執行國際路線時至少也存在一個時差的問題。《八一宣言》傳到陜北之后,紅軍仍東渡黃河討伐閻錫山,發動東征之戰;而且發動宣傳攻勢。東征結束,紅軍撤回黃河西岸之后,中共于5月5日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在此種態勢之下,作為中共特派員,馮雪峰確實不能自作主張唯共產國際之馬首是瞻,他只能聽從陜北中央的指令。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1956年版和1982年版《魯迅傳略》雖然已經完全被2007年《一個人的吶喊》取代,沒有什么可讀性了,但是它們仍然各具其研究價值,因為它們都顯示了自己的時代特征,反映了不同的學術氛圍、歷史環境。這三本書可以說是作者學術道路上的三個里程碑,我以為都能夠保存下去,只要記住它們各自的年代。
這篇札記僅僅就左翼文學方面的部分內容進行了對讀,而魯迅的生平包括其身后,值得關注的事情實在太多。如關于《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對于新月派文人的再認識,關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問題,魯迅與胡適的異同,魯迅與“左聯”的關系,“假如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等等,這些都是上個世紀值得人們思考的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我們認真細讀的內容。但是這些留待以后再記吧。
(《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朱正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11月版,29.80元)
(本文編輯: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