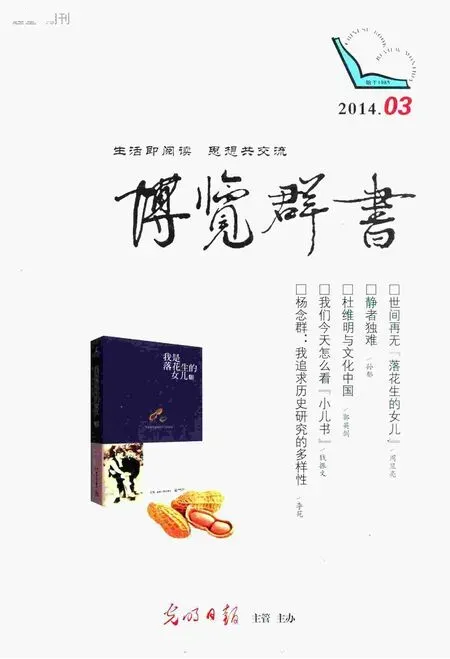一朵在雪中盛開的玫瑰
河 西
女人的美麗有不同的類型:標致之美,銷魂之美,低俗之美,自然之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美并不在于容貌。她臨終前面容非常憔悴,原先標志性的蓬勃的頭發無力地垂在肩上,像剛剛被雨淋過。臉部的肌肉再也無法克服地心引力的作用,松弛、蒼白,一臉病容,口紅也掩飾不了惘然若失的神態。
照片中三十多歲時的蘇珊·桑塔格,顯得桀驁不馴;她算不上迷人,卻活力四射,和她的文字一樣透露著一股子蠻勁,絲毫沒有傳統女性的那種溫順之美。
疾病擊垮了蘇珊·桑塔格的面容和身體,可也正是疾病哺育了她的批評之路。這位“思想和藝術領域的漫游者”43歲時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2003年3月份,又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隨后進行了骨髓移植手術。在持續半年的乳腺癌治療中,蘇珊·桑塔格敏銳地意識到,疾病并不僅僅是一種生理現象,它的背后隱藏著一套社會上通用的語法規范。正如我們在《作為疾病的隱喻》中所看到的,她將疾病的神話一一擊破,那些神話在文學作品中屢見不鮮,為讀者設下了一個又一個圈套,如今它們被甄別出來,成了“可視的奧秘”。
蘇珊·桑塔格的精神導師福柯死于艾滋病。在《作為疾病的隱喻》發表(1978年)10年之后,桑塔格單獨將艾滋病列出來研究,也許是因為福柯的關系。從發現并命名艾滋病,到死亡人數和感染人數呈現幾何級數增長只經過了短短幾年的時間,還從來沒有一種疾病能像艾滋病一樣成為人類的“天敵”,這令桑塔格感到震驚。福柯說“懷疑整個世界是莫大的光榮”,桑塔格實踐著他的忠告,并且,她用一部艾滋病的精神小史為這位哲學家寫下了最好的悼詞。
上世紀70年代,蘇珊·桑塔格曾經兩次訪問中國。1973年,蘇珊·桑塔格初次訪問中國前夕,在興奮之余,寫了一篇散文,在頭腦中先完成了一次中國之旅。不過,當時她并沒有給中國人留下多少印象,人們對這個美國女人疑慮重重,或許還會懷疑她是不是又一個安東尼奧尼式的“敵對分子”吧?
在寫作《中國旅行計劃》之前,桑塔格還沒有到過中國,但是這并不妨礙她對“中國”這個地理名詞產生一些遐想:“中國,一個玉器、柚木家具、竹子和狗肉裝點的山水大地”。桑塔格的中國情結和她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她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經濟頭腦的猶太人傳教士,長期在天津經營皮毛生意。不知道是在天津。還是在茫茫的戈壁灘上,她的母親懷上了她。不過,這位喜歡吃皮蛋的女士最終卻出生在了紐約,她自己對此耿耿于懷。
1963年2月1日,年輕的蘇珊·桑塔格第一次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自己的評論。在此之前,理查德·里茲將西蒙娜·薇依一些并不太受當時學界關注的文論翻譯成英文,交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再次引發了對西蒙娜·薇依的閱讀熱潮。這位只活到34歲的法國女人生前幾乎是默默無聞,盡管她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卻將受難看作是一種幸福,甚至情愿去體驗重體力勞動對她的身體所造成的重負。西蒙娜·薇依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她去世之后被出版的,其思想的尖銳廣博,在基督教神秘主義思想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她身后為她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理查德·里茲翻譯的文論,是薇依寫于1934至1943年的作品。正是這9年時間孕育了一位在感知、精神、語言、推理、社會倫理和政治等各個領域都成績斐然的思想大師,一位終其一生都傾近天主教信仰卻拒絕受洗入會的“編制外”圣徒。可惜,就是這樣一位哲學家卻沒有得到桑塔格的同情。雖然蘇珊·桑塔格對薇依顯然有一份熱愛,但她冷靜地洞見到,薇依、卡夫卡、蘭波、熱內……正以他們非理性、反文明的姿態而廣受好評。在追隨這批作家的讀者中隱含著一套大眾文化心理,即他們其實是在敬畏一種痛苦的經驗。
蘇珊·桑塔格對大眾的熱情持一種悲觀主義的態度。她寫道:
“因而。我在這里并不想批駁一種流行的觀念,而是意欲從當代的藝術和思潮中揭示出隱藏于極端趣味背后的內部動因。拋開一些表面的現象,認識到我們為什么會去閱讀和贊美像西蒙娜·薇依這樣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依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隨筆短章而贏得了成千上萬讀者的擁躉,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沒有必要去分擔西蒙娜·薇依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實現的愛,或是去接受她關于上帝的缺席的諾斯替派神學,贊成她棄絕肉身的宗教理想,認同她對羅馬文明和猶太人極端不公正的憎恨。類似的狀況在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的身上同樣存在,他們大多數的追隨者并沒有理解他們,更不會把他們的思想當作信條。我們讀著這些尖銳而怪異的言論,是因為他們個人具有權威性,他們堪稱嚴肅的典范,他們獻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強烈意愿,還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為他們的‘觀點。正如背德者亞西比德追隨著蘇格拉底的腳步,盡管他既不能夠也不愿意改變他的個人命運,但卻使他的意識深處喚起了一種感動和滿足,心中充滿著愛;正是以這種方式,敏感的現代讀者對某個不為他所有、也不可能為他所有的精神層面致以他的敬意。”
蘇珊·桑塔格還毫不留情地批評了薇依的反猶太主義傾向。作為桑塔格的早期作品,這篇文章已經顯示出桑塔格的某些文體風格:犀利、角度新奇,對權威和主流觀念嗤之以鼻。
薇依和桑塔格近乎兩個極端。薇依躲在馬賽多明我會的修道院里,熱衷于從純粹形而上的角度探討愛、友情、上帝、語言等問題;而桑塔格則喜歡拋頭露面,為政治界和文藝界的新聞寫些時評,為抗議各種不公正待遇奔走呼號,這恐怕是她受福柯影響的結果。不過兩人也有相似之處:都在病痛中承受著命運所給予的“恩賜”。值得一提的是,完成《反對闡釋》所有文章時的桑塔格正好34歲,也即薇依離開人世的年齡。
作為一位以激進著稱的批評家,蘇珊·桑塔格的批判文章充滿機警和火藥味,這和上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不無瓜葛。她在那個知識分子熱衷于激進實驗的年代考入芝加哥大學。有人也許會說,身為一名在美國頗負盛名的批評家。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她在巴黎的那段時光,因為歐洲的文學和批評景觀基本已經成形。西蒙娜·薇依、加繆、薩特、娜塔麗·薩洛特以及其他歐洲作家是蘇珊·桑塔格在《黨派評論》上發表的早期批評文章中的主角(確實,桑塔格沒有怎么涉及霍桑、梅爾維爾、愛默生和福克納這些美國人的英雄)。而中國,則是歐洲青年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西蒙·德·波伏瓦的小冊子《在中國的每一天》也曾經讓桑塔格激動不已。那一時期,風頭正健的桑塔格恐怕對自己的階級出身多少有些不滿,她原本可以輕松地獲得一個中國戶口,成為名正言順的知識左派,如今卻只能遙望古國山河,作種種華麗的妄想。這讓她迫不及待地要到中國看看,在這個烏托邦式的國度正在發生些
什么驚天動地的事。然而兩次造訪中國的結果卻讓她失望和沮喪,中國人對她的招待是禮節性的(不可謂不熱情),但她并沒有在這些官員身上看到她想像中的那個“最純真、最虔誠、最不受消費主義侵蝕的時代”。她想和大多數旅行者一樣尋找理想的家園,一個孕育了她的肉身,也孕育了她的思想路徑的精神家園,但現實顯然并不能讓她滿意,也許正因如此,她才寄希望于小說,做一次又一次頭腦中的旅行。她說:“我將穿過深圳河,一來一去。然后呢?自然而然的,接著是文學創作。”
蘇珊·桑塔格的一些文章和小說得到過恰當的評價,但可惜未被太多的人重視。比如《熾烈的女人》,杰克·史密斯就將其稱之為“令人震驚的詩學電影”,而有些人則對此表現出了道德上的憤怒。她臨終前收錄在集子中的幾篇小說也大多有著類似的遭遇。桑塔格的直接和銳利有時讓自詡開放的美國人也受不了。《寶貝》所表現出的美國社會中價值觀的混亂可謂一針見血;《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則讓人聯想起她著名的評論《坎普札記》。
《坎普札記》也許是過去十年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文學批評作品。坎普是一種難以理解的表演理念或行為方式,桑塔格將其讀解為歷史現象,就和拉斐爾前派式的穿著打扮以及各種時尚觀念差不多。她認為,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弗大街有許多游手好閑的年輕人,他們的姿態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恰恰相反,它們是舊貨店中的貨色,是對那些我們早就“習以為常”的行為的效仿。
“17世紀末和18世紀是坎普的黃金時代:蒲柏、康格里夫、沃爾浦爾,但不包括斯威夫特……慕尼黑的洛可可教堂和佩爾戈萊西是坎普當之無愧的代表。稍后,則是莫扎特的眾多作品……《泰特斯·安德洛米克斯》和《不同尋常的幕間短劇》也可以算是坎普的,或者可以視作坎普來演出。而戴高樂在公眾場合的舉止行為以及雄辯的演說純粹就是坎普。”很少有讀者能通過那些定義坎普的歷史和藝術理解她的激烈情緒。無論如何,讀這篇評論就像乘氣球在空中旅行,熾熱的陽光讓我們目眩神迷。“坎普就是一個閑逛的女子,穿著一件由300萬根羽毛做成的衣服。”她的警句帶有奧斯卡·王爾德的風格,是典型的坎普式趣味。
除非是在極度無助的處境中,否則沒有人愿意去死。藥物、醫院等救死扶傷的醫療設施被用來盡可能地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最終死神還是要降臨。蘇珊·桑塔格和死神搏斗,向它發起挑戰。2004年12月,她去世了,這令那些熱愛她的讀者,那些將其輝煌的作家生涯視作珍寶的讀者們傷心欲絕。幾十年前,她就遭受了人生的巨大打擊。一種疾病迫使她來到巴黎求醫,她學究氣地認為,在那兒她能找到一種最有希望的治療方法j在去世前的一年中,她有幾個月是在西雅圖的醫院度過的,因為她的白血病又復發了。治療失敗之后,她回到了她在紐約的家,在那里她忍受了更多的治療,更多的折磨,終于病重不治。令人感到寬慰的是,她的生命歷程連同她那些“頭腦中的旅行”并未就此落幕,一個閱讀她的人將再一次將思緒投向桑塔格所在的時空。這是一次對話,也是一次旅行。
蘇珊·桑塔格不僅是出色的批評家,也是位出色的小說家。在中國讀者的印象中,蘇珊·桑塔格的小說應該是她文論寫作之余的一種補償性手段。很多人的思維模式是這樣的:一個學者去寫小說,不是玩票,利用讀者的好奇心理大打擦邊球,就是把小說看作是文論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他們寫出來的小說晦澀程度絕不亞于一部高深莫測的學術著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艾柯的《傅柯擺》)。但蘇珊·桑塔格在這方面顯示出了一名純粹的小說家所應具有的稟賦。或許是因為女性特有的敏感思緒和文字把握能力,又或許是出于《反對闡釋》中所強調的觀念:現代文學和現代哲學具有同樣的發展必要性,蘇珊·桑塔格才在文論研究之外如此熱衷于寫作真正意義上的小說。
1963年,蘇珊·桑塔格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恩主》,其中充滿了夢囈。主人公希波萊特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夢的世界,這里有木偶之夢、鏡子之夢、鋼琴課之夢、非常派對之夢、老資助人之夢……可以說是五花八門。這是一個神經衰弱者的內心獨白。面對夢境,他并沒有表現出布勒東式的狂喜,恰恰相反,對夢或現實的恐懼讓整部小說都呈現出黯淡色調的效果。在此書的扉頁上,桑塔格引用了波德萊爾的一段文字,可以視作作品的主題:“談到睡覺、每晚可怕的歷險,可以說,人們每天大膽地去睡覺,完全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睡覺有什么危險。不明白這一點,我們便無法理解他們的大膽”。
蘇珊·桑塔格說“我夢故我在”。一個夢就是一個陌生的國度,希波萊特在幻想中活著,他在夢和日常工作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這讓他體味到生活內在的滋味。他也許會感到訝異,這些形形色色的夢中的人物,就像泛黃的舊照片那樣。如果說回憶等同于夢境,那么我們的生活豈非通過虛構也能夠獲得?
雖然在序言中,蘇珊·桑塔格否認這部小說是一部自傳體的作品,但是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希波萊特的焦慮也是桑塔格的焦慮,我懷疑她寫作這本書時正被噩夢所困擾,因為她在小說開場時對希波萊特童年的描述和桑塔格本人多有相似之處。此外,對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熱愛也部分表現了蘇珊·桑塔格對法國哲學的著迷,在桑塔格的心目中,她更認同法國身份。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會是一個法國男人。男性代表強勢,這和桑塔格批評家的身份又相吻合。不像小說家所從事的是反觀內心的工作,批評家則是攻擊性的職業。而且,這部小說和她的唯一一部劇作《床上的愛麗斯》在風格上非常接近。而《床上的愛麗斯》要表現的是女性的痛苦。也許,1991年時的桑塔格已經能夠正視自己的疾病,而在30年前,她似乎更愿意躲在面具背后,以一個與自己年齡相差近40歲的異國男性的面目出現,來掩飾她內心的不安。
和她之前創作的《恩主》《死匣》《火山情人》略有不同的是,《在美國》是蘇珊·桑塔格的第一部歷史傳記,女主人公的原型是波蘭裔著名演員海倫娜·莫德耶斯卡。通過記述波蘭女演員瑪琳娜在波蘭的精神沉淪和在美國加州定居后的“自我變革”和“精神復蘇”,蘇珊·桑塔格以其細致入微的筆觸,為讀者再現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其中充滿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細節和歷史知識”(多蘭語)。從描寫的細膩程度來看,蘇珊·桑塔格絕對不會比以“文學顯微鏡”著稱的女作家凱·安·波特遜色多少。然而,這還只是一些無關大局的表面現象,這位被驕傲的布羅茨基贊譽為“大西洋兩側最具智慧的人物”顯然不怎么安分,盡管蘇珊·桑塔格冷靜地控制著小說推進的速度,《在美國》中仍然流露出許多具有女性主義傾向的言辭,激烈地抨擊美國社會制度中的性別歧視。同時,《在美國》還有一種不同于米蘭·昆德拉的思辨氣質,作者深深迷戀于由無數個哲學命題所構成的小說哲學:在美國和波蘭之間的人文地理學比照、倫理道德的二元消解、關于演員的面具理論、人生虛無的存在主義式理解,使這部小說在歷史事實之外獲得了獨立存在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和《恩主》一樣,所要解讀的是人的存在的無力感。
豐富甚至有些狂亂的寫作為她贏得了廣泛的聲譽,桑塔格于1987年擔任國際作家、翻譯家和編輯筆會美國分會主席;她的作品曾榮獲美國藝術院英格拉姆·梅里爾基金獎(1976)、全國批評家協會獎(1977)、科學和文學院獎(德國,1979)和全國圖書獎(2000)。2001年4月,她又獲得耶路撒冷獎的桂冠,是繼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后獲此殊榮的唯一女作家。
蘇珊·桑塔格的人生豐富而坎坷。在疾病的折磨下,2004年12月28日早晨7點10分,她終止了人生亮麗而又無奈的演出。我還記得她為毛澤東寫過的一段話,用在她身上也恰如其分:“毛就這樣去了,人們依然匆匆忙忙地在紐約的地鐵口進進出出,有人在讀報,有人去買漢堡包,沒有人意識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不知道大洋彼岸紐約的墓地上是否也已白雪皚皚。但愿我的這篇短文能化為一朵在雪中盛開的玫瑰,奉獻在她的墓碑前。
(《恩主》,蘇珊·桑塔格著,姚君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9月版,27.00元)
(本文編輯: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