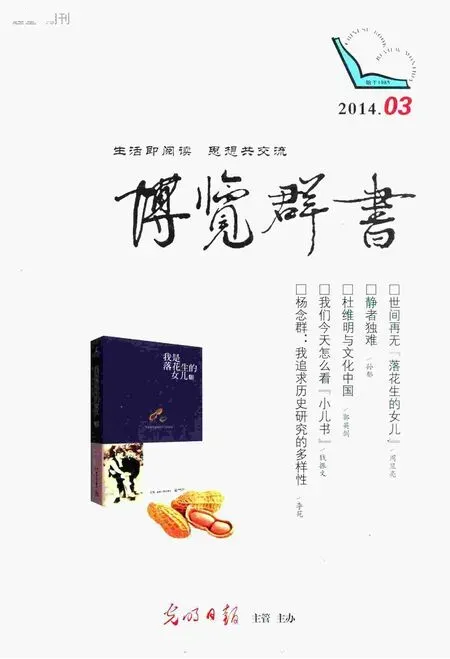山外青山:韓國學術會議印象
黃樸民
唐代大詩人王維有詩云:“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我雖然還未到晚年,但是生性好靜,現在越來越不耐紅塵擾攘,頗思慕“今夜月明清似水,悄無人處上高臺”(郁達夫詩句)的境界。即便是對于賴以安身立命的教書治學,也早不復“百年事業歸經濟”的豪情雄心。一句話,混唄!
以這樣的心態到韓國訪學,自然不會有什么作為。所以,在韓國這一年期間,我很少參與各類學術活動,更難得在學術會議上趕場湊趣了。
不過,“難得”并不意味著“絕跡”。或因為同事們的“煽動”,或由于主事者的“錯愛”,也偶爾參加過幾場學術會議,算是霧里看花、隔靴搔癢式的了解了韓國學術會議的一般情況,用旁觀者的心態觀察韓國學術會議的形式和特點,簡單記上一筆,對于韓國學術界的印象。
我孤陋寡聞,不知道韓國是否有所謂的“社團法”,規定學術團體必須向民政部門注冊登記。韓國的學術社團多如牛毛,有大有小,組織相關專業的學者從事學術研究與討論,而召開各類學術會議,就是它們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體現其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
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學術團體大多是韓國學者自發的松散組合。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由于其研究的性質或任務之重要性(如歷史學有關高句麗問題的研究),某些學術團體的背后有大財團乃至政府文化權力部門支持、推動的影子(像“東北亞歷史財團”之類)。但是,韓國的學術團體既然以“民間”形式出現,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它們都得按照“民間”學術自由活動的一般規律辦事,更多的反映了學術研究的自身特點,學術氣息相對比較濃厚,而其主辦的學術會議也更像純粹的學術會議。
受制于專業的局限與語言的隔膜,我在韓國所接觸的學術團體,基本上都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機構,所參加的學術活動,也局限于專門討論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會議。在韓國,歷史學科同樣被邊緣化,專門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隊伍也勢單力薄,加上學緣、地緣、人緣等各種因素的制約,這樣的學術團體一般規模都很小,其中正兒八經的學術骨干不過寥寥幾人,就像京劇《沙家浜》中胡傳魁司令唱的“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而已。
這個特點,決定了韓國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團體少官僚氣而多“草根氣”。我所接觸過的“韓國秦漢史學會”、“韓國現代中國哲學學會”等,構成都非常單純,每個學會也就十多位教授(分別來自韓國各地高校)充當骨干,再吸收一些已畢業或正在讀的博士、碩士生參加,以壯聲勢。一般每個學會有一位會長,由學會成員公推學問較好且做事熱心的教授擔任,起一個召集人的作用。此外,大家都是平等的會員。
這一點,似乎與中國的一些學術團體大相徑庭,中國的學術團體往往是以“官本位”精神組建的,一個學會,有顧問(有時還加一層次,日:高級顧問),有名譽會長,有會長,有副會長若干,下面又有秘書長、若干副秘書長,再加上常務理事、理事等等,疊床架屋,人浮于事,目的是讓一些未能“學而優則仕”的學者,在自己小小的學術圈子里,效法有司衙門,過一把小小的“官癮”。如我參加的中國先秦史研究會,理事多達七八十人;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更夸張,理事早已過了百數;中國秦漢史學會的情況稍好一些,但理事之數也在四十左右(敝人未能免俗,在這三家學會中都忝列理事,慚愧慚愧)。這樣的狀況在韓國的學術團體里基本不存在。
韓國的學術會議也比較簡單,毫無我們國家學術會議的規模與氣魄。往往是一二十個人參加,沒有領導蒞臨后繁文縟節的禮數,沒有節外生枝的內容,一開會就直奔主題,進行認真的學術討論。
反觀我們,學術會議一樣體現出國民文化心理:求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場會議,必有隆重的開幕式,主席致開幕詞,領導蒞臨發表講話,名人與團體致賀電賀辭,再加上合影留念……所有程序一個也不能少,否則就不足以體現其重要!做會務的,忙得焦頭爛額、昏天黑地;與會的,聽得云山霧罩、昏昏欲睡。至于會議的真正主旨——學術交流與探討,往往被置于次要的位置。
我們這種學術會議的開法,韓國學者無法想象。他們開會通常也是就半天、一天時間,與會者圍桌而坐,沒有主席臺與聽眾席之分,沒有特殊嘉賓與普通人士之別,少了許多虛與委蛇的故事,多了不少自由討論的時間。正因為韓國的學術會議簡單化、小型化、專業化,所以操作起來也相對容易,開會的頻率也就比較緊密。像“韓國秦漢史學會”、“韓國現代中國哲學學會”等團體,一般每個月都舉辦一次會議,可以稱為“學術月會”了。時間大多定在周六的下午,為的是不影響大家正常工作日的教學。2點開會,6點結束,大家一道下館子聚餐,酒足飯飽,各奔東西。既切磋了學術,又增進了感情,與會者都覺得物有所值,這恐怕是這種沙龍式的學術月會活動能夠長期堅持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韓國,學術會議的開會方式也很有特點。每次通常有一兩個人作主題發言(他們習慣于稱作“發表”),專門介紹他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一般用時半個小時左右。“發表”完畢,由一人作詳細點評,分析發表者學術觀點的得失,提出自己贊同或商榷的意見。然后是全體與會者圍繞發表者的文章及其觀點進行自由發言,或修正,或質疑,或補充,總之,共同深化有關討論主題的認識。在此過程中,發表者可以隨時插話,進行答疑或說明。這種方式,頗類似于讀書討論會,形式單純而實質內容豐富,往往能碰撞激發出學術思想上的火花,主講者和其他與會者都有收獲。學術會議能開到這個地步,應該說是相當成功了。
這一點,真的值得我們中國學術界學習和效法,開會、治學,少一點追求面子的虛招,多一點講究里子的實干,比什么都強!
(本文編輯: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