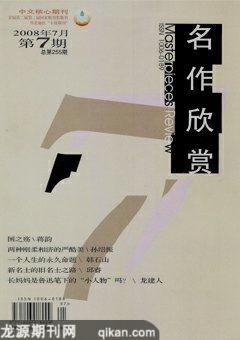浪漫中的現(xiàn)代:未完成的詩學(xué)過渡
陳芝國
文學(xué)史家在書寫中國新詩史時(shí),聞一多與其他新月詩人往往一起被歸入浪漫主義的歷史譜系,同時(shí)他們又從詩歌形式方面的格律追求和精神層面的感時(shí)憂國對(duì)他進(jìn)行平面化的坐標(biāo)定位。此種描述的合理性自然毋庸置疑,也早已成為我們討論聞一多新詩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的出發(fā)點(diǎn),然而,如果我們返回歷史的場(chǎng)景,以一種共時(shí)性的文學(xué)眼光重新審視聞一多的某些詩歌文本,不難發(fā)現(xiàn)歷史本身其實(shí)遠(yuǎn)比文學(xué)史家的書寫要更為豐富。學(xué)界一直爭(zhēng)論不休的《奇跡》,在浪漫主義的外衣下已潛藏著豐富的現(xiàn)代主義氣息,為我們撬開文學(xué)史家鎖定的歷史提供了絕佳的著力點(diǎn)。
1928年1月詩集《死水》出版以后,聞一多只在同年的四五月間發(fā)表過《答辯》與《回來》兩首短詩和譯自英美現(xiàn)代詩人的抒情詩,此后他埋首于“故紙堆”中,直到1930年12月他才詩興重發(fā),寫出了被徐志摩譽(yù)之為“一鳴驚人”的《奇跡》。梁實(shí)秋認(rèn)為:“一多在這個(gè)時(shí)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點(diǎn)漣漪,情形并不太重,因?yàn)樵谇楦袆倓偵鲆粋€(gè)蓓蕾的時(shí)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內(nèi)心里當(dāng)然是有一番折騰,寫出詩來仍然是那樣的回腸蕩氣。”①隨后,聞黎明以聞一多與方令孺的關(guān)系對(duì)梁氏之言予以印證。圍繞《奇跡》題旨的爭(zhēng)論終于塵埃落定,諸多研究者遂將《奇跡》認(rèn)定為愛情詩。姑且不論偉大的文學(xué)作品與它的本事相距有多么遙遠(yuǎn),即使就主張超越性的詩人聞一多而言,個(gè)人經(jīng)驗(yàn)也往往只是寫作的起點(diǎn),而不是寫作的終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