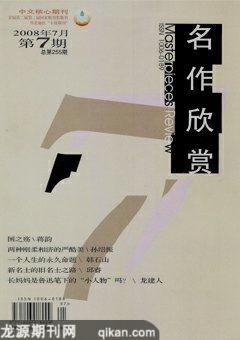兇案的文學預謀
林超然
在中國,兇案與小說合謀其實也算是并不少見的文學事件,不過這時的小說常常倒向通俗,它能引發復雜心理中的一種好奇,并成為大眾的一個日常化的重要談資,作品母題大致不出善與惡的二元判斷,其社會價值往往大過文學價值。而兇案題材中只有一小部分屬于雅文學旗下的小說,才一方面充分考慮到兇案在民族心理上的特別投影,不在物質層面上過多渲染,變現實中的丑陋為藝術維度上的審美;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對傳統敘事方法有意克服,慣于以一種平靜、客觀的態度陳述,兇案本身不再是重要的寫作目的,而只是小說走向美學歸宿一個環節、一個手段,作家真正的用意有時干脆與暴力無關。如今這類小說數量不多,卻彌足珍貴,它們成為中國當代作家有能力深刻洞悉人生、世界秘密的重要文本,成為漢語寫作進行現代小說文體革命已然步入成功的典型物證。
變亂中的文化喘息
——讀汪曾祺《陳小手》
汪曾祺的小說大都是對舊時歲月的悠然遠望,更確切地說是他的眼神總少不得對自己童年枝葉的百般纏繞,篇幅可大可小,情節可繁可簡,主旨可喜可悲,卻都有著相類似的時空畫框。比之當前生活,那些前塵往事更像是他創作的恒產,每一次輕輕觸碰,都會獲得響亮的回應。“小說是回憶”①為他的創作律條,這也就難怪他會那么專注地凝視從前,在他人屬于泛黃、滯重的那些底色,在汪曾祺卻是惹人憐愛的新綠。《陳小手》是汪曾祺《故里三陳》中的一篇,全文1500字許,是一篇小小說,是一篇放棄了技巧卻不缺少經營的獲勝的小小說,是一篇文字平靜卻暗含焦慮的小小說。作品借結尾處突然出現的一樁兇案,來寫儒家剛健有為思想的一次遇挫,寫進步文化一路行來的艱難步履。
《陳小手》所展示的時代極少有產科醫生,因為其時學醫的大都是男人,他們又對“產科”不屑為之,都覺得這是一樁丟人沒出息的事,陳小手自是鳳毛麟角難得一見的一個了。他的得名是因為手特別小,比女人的手還小,還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軟細嫩。“因為他的手小,動作細膩,可以減少產婦很多痛苦”,他特別適合做產醫;女人生產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陳小手為趕時間,常騎著白馬飛奔,到各處去接生,他對生命充分尊崇與敬重,所以不在乎他人的譏諷,他熱愛自己的本職;“正在呻吟慘叫的產婦聽到他的馬脖子上的鑾鈴的聲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專能治難產的他“活人多矣”,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他甚至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急需品”,他的作為有著一種難以替代的重要價值。
可是命運沒有給正處于人生上升期、對自己的事業豪情萬丈的他更多的機會。最后一次行醫,他救的是一個團長太太的命。“母子平安”后,團長設了酒宴,還賞20塊大洋,卻在他跨上馬背的一瞬一槍把他擊落。
對于這一件事,若只看出“揭示了反動軍閥的兇殘和霸道,控訴了他們滅絕人性、天良的罪行”是遠遠不夠的。舉起那把槍的是一種社會制度,是從遠古走來的陳腐觀念。
可能一心救死扶傷的陳小手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職業選擇不過是社會變亂中曇花一現的文化喘息,他的行動一旦被權力階層認清就會被扼殺的,因為他無意間成了一個舊體制的沖決、挑釁者。他的最終被殺就是一次文化突圍的失敗,就是一種進步傾向遭遇了斷然的否定。
對于那個時代來說,出現帶有濃重象征意味的男性產醫,是一樁敏感的文化事件,是一種過早到來的先進思想,它的聲音很微弱,力量很單薄,社會禁忌會讓它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們注意到,每次陳小手接生已畢轉身離開前總要向主人道句“得罪”,當然“得罪”可以看作是陳小手的謙敬之辭,但其中確有一種道歉的底色,他并不能夠真正挺起脊梁。
陳小手是一個人在戰斗,而一個人是斗不過一個時代的。陳小手知道自己的工作重要,也對自己的醫道有著充分的自信,但是“主流社會”“正統文化”是讓他緊張而又無可奈何的。我們還注意到,“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請他的。中小戶人家,忌諱較少,遇到產婦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會建議:‘去請陳小手吧。”大戶、中小戶人家態度的分別,其實是正統文化與民間文化在立場上的本質對壘。
汪曾祺慣于用文字搭建一個藝術民間,《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皮鳳三楦房子》《職業》等等都是這方面的經典例證,他總是對下層百姓的生活樣式鄭重端詳,而對“大戶人家”會流露出諸多不屑。生活在“民間”的人們自然也會受到社會、時代的影響,他們沒有生存于真空中,但是他們還保留了另外一種本色、率性的生活,甚至是時代文明之外的一種模式,有時這種模式與正統文化水乳交融,有時卻又是對立的,這種“民間的文明”常常更尊重人的生命、權利、情感,更接近人的淳樸天性,所以《陳小手》里的“中小戶人家,忌諱較少”一句,貌似極不經意的提及,其實是意味深長的。
作為一篇小小說,表面上看,《陳小手》的形式給人的感覺是非常樸素的,就那么娓娓道來,似乎沒用到太多的技巧,只讓事件自己說話。小小說的結尾該是奇峰奮起、波瀾陡轉,正好趕在沖突頂點“駿馬收韁,寸步不移”才好。《陳小手》偏偏在該結的時候卻沒結,而是又輕描淡寫地添了幾個字:“團長覺得怪委屈。”其實正是這幾個字,使一個血淋淋的故事成為一場兩種文化大打爭奪戰的文本。
團長的殺人舉動固然是流氓加屠夫的行徑,但這件事并不單純,因為“團長覺得怪委屈”并不是矯情,并不是惺惺作態,而是真相。我們不要忘了,他同樣也是一個受害者,與他在戰場上殺人不同,這次他成了一個罪犯,惡魔一樣的罪犯,被一種陳規陋習障目的罪犯。他內心的矛盾、掙扎實際上是兩種文化的角斗。團長置酒賞錢,是因為得子后一個父親的欣喜;開槍殺人,是因為一個丈夫的面子遭受重創。換句話也可以說,團長置酒賞錢,是答謝恩人;送上一顆子彈,是懲治男性尊嚴的那個嚴重冒犯者。“剔除、驅逐、毀滅、絕滅等都是破壞的同義詞。這些文明人的語言實際代表了‘殺害的愿望——其意義是原始的自我防衛,不是虐待癥的愉快感覺。”②團長的兇殘舉動為的是掩飾、遮羞,是離本能不遠的防衛,是既蠻橫霸道又脆弱無助的防衛。汪曾祺的文字里有一絲讓人難以察覺的諒解。
這樣的結尾,意在言外而不在言中,作品留給人巨大的想象空間,掩卷瞑目,余音仍在耳際縈繞不去。汪曾祺關心的是人,人的變化,人類的前途,在這篇小說里,陳小手是被一種守舊思想的大力所扭曲、壓扁的,但作家還是沒有劍拔弩張,而是盡量克制。“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于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地想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樸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③
汪曾祺曾對自己的小說作過劃分:一部分作品感情是憂傷的,比如《職業》《幽冥鐘》等;一部分則有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等;另一部分常有苦味的嘲謔,比如《云致秋行狀》《異秉》等。《陳小手》應是三者混雜一起,使人在憤懣中仍有所期待。
《陳小手》陌生化的敘事策略是備受推崇的,它不聲不響地演繹民俗原貌,心平氣和道出兇案始末,近于談往的語調,近于客觀的文風,實際上是以舒緩寫憤慨,以溫和寫嘲謔,以寧靜寫蒼涼。作家更要以此來引發一種深刻的反省,這種反省在我們走向現代化的時候依然同樣不可或缺,甚至更為重要。
寫兇案絕不是作家的真正用意。新生事物的艱難喘息,讓我們看到了正統文化的固步自封;儒家剛健有為、急公好義思想的落敗,讓我們看到了進步文化執著向前時的巨大阻礙,看到了我們投奔現代文明時路遇的幾絲尷尬。這些都不要緊,汪曾祺有足夠的耐心,他也提醒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因為他堅信一切都會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