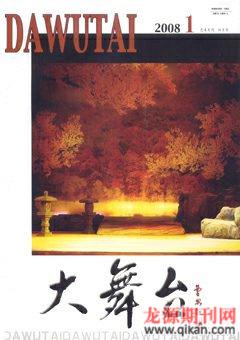淺析五代、北宋山水畫中的現實主義精神
【內容摘要】隨著“中國百家金陵畫展”連續三年來在江蘇省的開展,“現實主義”的繪畫品格開始受到了不少畫家的重新關注。在其中的中國畫展覽中,不乏有人抱怨山水畫不適合表現重大題材和現實主義精神,筆者在思考之余,認為中國古典山水畫其實并不缺乏現實主義精神,在此以最典型的五代、北宋時期的山水畫為例,從其藝術觀念、觀察自然的方式、創作手法等幾個角度,對中國古典山水畫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加以分析。
【關鍵詞】藝術觀念 觀察方式 創作手法
美術史上的現實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源于法國的一種美術思潮和美術流派。但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指的不是某個具體思潮或流派的“現實主義”,而是具有一定客觀再現功能的創作手法。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早已體現在中國古代的繪畫創作之中。中國古代畫論的“師造化”就是指從現實主義角度理解繪畫與現實的關系,認為客觀世界是藝術創造的根源,強調畫家要向自然造化學習,從而真實地反映現實世界。縱觀五代、北宋時期的山水畫,畫家在藝術觀念、觀察方式和創作手法上,無不是為了真實再現自然世界之美。以下將加以具體分析。
一、五代、北宋時期山水畫家的藝術觀念
唐末的社會戰亂和五代時期政權的頻繁更替,導致了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遷和宗教意識的淡薄。五代、北宋初期的山水畫家為逃避戰亂而隱逸山林,逐漸增加了對山水的認識觀察,在藝術觀念上也開始由以往的求仙訪道轉到真實再現自然之美的山水畫本體上來。“世俗地主士大夫越來越多的取代了門閥貴族的社會地位,與以往少數門閥貴族的世襲地位不同,世俗地主士大夫階層大多由考試而入仕,由野而朝,由農(富農、地主)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鄉村而城市。這樣,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們的榮華富貴、樓臺亭閣生活的一種心理需要的補充和替換,一種情感上的回憶和追求,從而對這個階級具有某種普遍意義。”[1]郭熙在《林泉高致》中道出了這一時期士大夫們寄情于山水畫的本意:“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煙霞先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見也。……然則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黃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2]
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山水畫家的生活、理想和審美觀念是一種人與自然共處時的愉悅和牧歌式的寧靜。同時,對于山水畫的鐘情,也逐漸從以往求仙訪道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日漸獲得了自己的現實性格。五代、北宋初期具有寫實主義精神的山水畫家主要有荊浩、關仝、李成、范寬、董源、巨然、郭熙等,其中以關仝、李成、范寬為代表形成的三種風格后人分別以“峭拔、曠遠、和雄杰”[3]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不同風格主要來自對自己熟悉的自然環境的真實描繪,以致他們的追隨者們也多以地區為特色,“齊魯之士唯摹營丘,關陜之士唯摹范寬。”總之在這一時期的山水畫中無不體現了對自然山水的真實描摹的藝術觀念。
這種寫實精神鮮明的藝術觀不僅體現在士大夫畫家們的山水畫作品中,同時也體現在他們的論著中。首先是荊浩在《筆法記》中提出了“圖真”論的觀點,這也是荊浩論著中最基本的觀點,它發揮了荊浩對于繪畫與現實關系的看法。唐張璪曾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觀點,而由于技法的不成熟,未能真正實施于山水畫中,到了荊浩這里便用“度物象而取其真”、“搜妙創真”結合繪畫創作實際經驗,把“外師造化”和“中得心源”統一起來,較深入地回答了山水畫與現實的關系。“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若不知術,茍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曰:“何以為似?何以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4]并以此把“真”與“似”區別開來,“似”為有形而無神,“真”則形神兼具。不僅把握了物像的外形特征,而且抓了它的內在氣質,從而使物像更加生動傳神,而又不失其寫實性。
其次,是郭熙、郭思父子的《林泉高致》,從山水畫的本體意義出發詳細闡述了山水畫的審美需求、構圖布置、作畫步驟和觀察方法等。(其觀察方法下文將進一步論述)《林泉高致》提出畫山水要有“林泉之心”,這與郭熙長期對山水畫的觀察與學習造就的山林情節有密切關系,并以此強調了山水畫的“寫實”性即要求所畫自然對象的山水是畫家目睹體察的真實地方。對山水畫之形態本體的研究必然觸及到對山與水二者相互關系的探討,這是從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向自然山水本身的體悟的微妙轉變。郭熙對山水關系的總結是“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這是中國古代山水畫論中對山水最深刻的總結。這種對山水的深入探討強化了畫家寫實的藝術觀念,更進一步地推動了山水畫的寫實主義精神。
二、觀察感悟自然的方法
對于自然山水的觀察和感悟,五代、北宋初期的山水畫家在自身實踐的基礎上總結了規律和方法。荊浩“圖真”論不僅道出了山水畫寫實主義的藝術觀,也道出了對自然萬物理性、客觀的觀察方法,雖然《筆法記》中也提出了“氣、韻、思、景、筆、墨”六要,但這一切又都是圍繞“圖真”為理想的,從留存下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種理想的樸實與濃厚的感情成份是不可以被簡單視為幼稚的。他還提出了山水畫中具體松、柏、屋、雜樹、山、水等形態表現,并寫道:“子既好云林山水,須明物象之源。”以及畫面中易出現的“有形病”與“無形病”的區別。從而論述了季節與花草,房屋與人、樹、山的大小比例關系的適當。荊浩在《筆法記》開頭就記述了自己在太行山中發現古松樹林“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真。”[5]對事物反復地寫生與觀察,使畫家積淀了豐富的自然范本。
對山水本體意義的觀察方法,郭熙還提出了著名的“三遠說”。郭熙云:“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后山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這種移動的曲折的視線,由高轉深、由深轉近,再橫向于平遠,形成一個節奏化的行動。與西方的焦點透視大不相同,雖然沒有去追尋自然的遠近在一個平面上得到三維的視錯覺規律,但這種對“三遠”的描述也是力圖對真實空間的再現,只是有了時間的先后而已。
另外,郭熙對山水畫的寫實主義精神更重要的理論是提出:“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和“四時之景不同”的觀察方法。甚至提示說現實中山在陽光照射的地方就是明朗的,而沒有陽光的地方就是陰暗的,山就是這樣因為陽光的原因表現出它的形狀。通過這種觀察而畫出的山水是那樣真實,以至“見青煙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游。”山水畫達到這樣的境地,足以證明郭熙對山水的觀察和終極審美目標也是以寫實精神為中心而展開的。
綜上所述,五代、北宋初期山水畫家對自然山水的觀察和體悟是屬于純客觀地力圖追求自然之理的,同時也與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的重理思想有關。與郭熙同時期的理學家邵雍,在其《觀物篇》中提出了“觀物”的思想。《觀物內篇》之十二說:“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圣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由安有我于其間哉!”[6]“以物觀物”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命題,既是方法論,又是世界觀。五代、北宋初期的山水畫正暗含了這種純客觀之法。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論述了詩詞中所表達的“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而這一時期山水畫正是以純粹客觀的觀照方法構建了一個山水本體世界——無我之境,從而將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推向了高峰。
三、創作手法
人類本能地有探詢現實問題的欲望,這就構成了探詢問題的方法與實踐。前面已探討了五代北宋時期的藝術觀和觀察自然的方法,那么如何在實踐中去應用和表現從客觀中觀察到的山水呢?荊浩在《筆法記》中強調了筆墨的重要性,筆墨的運用在《匡廬圖》中通過皴、擦、點、染塑造山體的真實效果——體積、結構、空氣、距離等,墨的重要性在這里被得到進一步地發揮,并通過墨色渲染以云煙的形式拉開中景與遠景的空間距離。畫家這種尋求真實的動機與西方早期畫家對真實的理解非常地接近,即將客觀的自然與圖像再現的相似性進行盡可能接近的類比。在南方,董源的山水畫如《瀟湘圖》也以披麻皴和密集的墨點真實的表現江南的山水。其中對于江南生活場景和煙雨朦朧的景色描繪也為后世創造了一種經典的筆墨表現方法。
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以批評的角度論述了李成山水畫中“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檐,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屋檐間榱角。”[7]從而提出了山水畫“以大觀小”之法。而李成對于自然的看法卻非常突出的表現出適合視覺習慣的透視效果,如《喬松平遠圖》、《讀碑窠石圖》等通過前方占構圖三分之二的樹木枝椏,使我們能夠看到符合錯覺習慣的真實風景,遠山盡管在樹木腰間但又不失其高,李成如此熱衷于視覺觀察到的自然景觀,使他的作品構圖以平遠為主,形成了他的風格——顯然這一時期的山水畫家是津津樂道于表現真實效果的技法的。而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也在力圖表達觀者站在一定點所看到的山水形象,中景陡立的絕壁畫于中央,使人為之仰望為之贊嘆、為之產生崇高肅穆的感受,以至于有學者說:“如果將上部絕壁舍去,構圖幾乎是一幅完全的寫實主義風景畫”。[8]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他的書中Symbols of Eternity: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China中說道:“范寬的意圖很清楚,他要讓觀者感到自己不是在看畫,而是真實地站在峭壁之下凝神注視著大自然,直到塵世的喧囂在身邊消逝,耳旁響起林間的風聲、落瀑的轟鳴聲和山徑上嗒嗒而來的馬蹄聲為止。”
四、結語
五代、北宋初期山水畫所具有的這種“搜妙創真”的藝術觀念和“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的觀察方法以及在筆墨變化中所追求的空間、體量和視覺的真實感共同打造了這一時期山水畫的寫實主義精神,在客觀整體地描繪自然山水方面,達到了歷代山水畫上的高峰。這種客觀的、全景整體性地描繪,使五代、北宋初期山水畫富有一種深厚的意味和崇高的感受,使人清晰地感受到那完整的大自然與人類牧歌式的親切關系。這種統一的大山大水式的寫實性山水在如今的山水畫中已不多見,在我們現代的山水畫中還有多少作品能讓人產生這種崇高的理想呢?我們真誠期待下一個山水畫高峰的到來。
注釋:
[1]李澤厚.《美學三書》.第166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2]、[4]、[5]俞劍華編著. 《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部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修訂本
[3]童書業. 《唐宋繪畫叢談》.第48頁,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版
[6]《中國哲學史資料選集——宋元明之部》.第42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主編.中華書局,1982年版
[7]俞劍華.編著《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部.第652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修訂本
[8]呂澎著. 《溪山清遠——兩宋時期山水畫的歷史與趣味轉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簡介:
鄭瑞利,女,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2006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美術史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