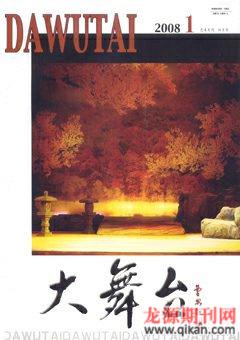觀演距離與戲劇藝術審美活動研究
戲劇是一門綜合的文化藝術,是一種由演員直接面對觀眾表演,從而引起某種戲劇美感的內容的藝術。戲劇藝術的本質,就是“觀”與“演”的交流關系。一出戲,當它在舞臺上演出的時候,觀眾會有“真感人”、“演得真棒”等諸多現場感受,但離開劇院后,這出戲在觀眾心中將會發生質的變化,這種“質”的變化,就是觀眾在劇場當中實際體驗到的思想感情。演出結束后,觀眾離開劇院,會回到家中或工作環境當中,此時再通過對演員表演技藝及故事情節內容的回憶,重新會對這出戲產生新的實際生命的體驗,這種體驗,會被觀眾帶到現實生活當中來。這樣一個觀眾“眼淚及笑聲、感動與興奮”并沒有結束的過程,是由戲劇審美時“觀”與“演”之間的距離產生的。
審美是需要距離的。戲劇的誕生是從觀眾跟演員的分離開始,戲劇有許多種起源的說法,但無論是祭祀儀式說、游戲說、巫覡說、樂舞說還是俳優說等,都有人物的角色扮演,而這種扮演,則必然會有“觀眾”出現。由此看來,“觀”與“演”之間的距離是戲劇藝術與生俱來的特點。這種“距離”將觀眾與演員分開的同時,也把舞臺上正在表演的內容和觀眾的現實生活分開了,一個劇場的最低要求就是有一個演出的地方和一個觀看的地方。“演出”和“觀看”使得表演者和觀看者之間有了空間距離,這種空間距離的產生,能使演員找到一種“進入演出”的感覺,而不再是生活中的人了;空間距離還能使得觀眾在“身臨其境”的同時,感受到舞臺上一切發生的都是假設的,觀眾觀看的“一致性”,加重了戲劇演出被“觀看”的份量。觀眾在觀看時“一會兒在戲里,一會兒在戲外”的感受,就是戲劇欣賞,這種戲劇欣賞的過程,就是一種審美活動,而這種審美活動的完成,需要距離,這種距離,就是“觀”與“演”的空間距離和由此帶來的心理距離。
一、“觀”與“演”的空間距離
戲劇藝術有五大要素:觀眾、導演、劇本、劇場和演員。沒有觀眾與劇場,就沒有戲劇。德國人史雷格爾曾經說過:劇場是多種藝術結合起來以產生奇妙效果的地方,是崇高、最深奧的詩不時借著千錘百煉的演技來解釋的地方,這些演技同時表現滔滔的辯才和活生生的圖景;在劇場里,建筑師貢獻出最壯麗的裝飾,繪畫家貢獻出按照透視法配置的幻景,音樂的幫助用來配合心境,曲調用來加強已經使心境激動的情緒。最后,劇場是這樣一種場所,它把一個民族所擁有的全部社會和藝術的文明、千百年不斷努力而獲得的成就,在幾小時的演出中表現出來,它對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種非常的吸引力,它一向是富于聰明才智的民族所喜愛的娛樂。[1]
從這段“劇場”的文字定義來看,我們可以將劇場理解為兩個方面,一、劇場是演員演戲和觀眾看戲的地方,它主要由舞臺和觀眾席組成。在劇場里,“觀眾”成了一個整體,有別于舞臺上的“演員”。劇場結構決定了這種“觀”與“演”的方式。二、劇場是觀眾進行“集體審美體驗”的場所。觀眾進入了劇場,就意味著進入了該戲的“規定情境”。此時,觀眾也作為一種特殊的角色參與到戲劇活動當中,好像舞臺上發生的一切就發生在自己身邊,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觀眾與演員之間的交流,觀眾與觀眾之間的交流,一切都是以“身臨其境”為前提。
美國戲劇家杰·威廉斯曾說:“在劇院里,我卻變成了一個返樸歸真的人……劇作家無論對我的理智施加什么影響,均必須經過我的情感反應而進入我的思想,如果它確能進入得如此深的話。”[2]杰·威廉斯的這句話說明了觀眾在劇場進行戲劇欣賞時,由于舞臺空間距離分離了“觀”與“演”的關系,觀眾個人的情感介入導致其幻覺的產生。比如在戲劇演出時,如果現實生活中是冬天,而舞臺上是夏季,那么,演員在寒冷的冬季穿著單薄的衣服在舞臺上翩翩起舞時,觀眾就不會感到驚訝;如果舞臺是一個古老的宮殿,演員在古老的宮殿中議事,觀眾不會認為自己可以湊上前去與他共商國事;演員們在舞臺上熱情地揮舞著馬鞭,觀眾會認為他是在縱馬疾行或是征戰沙場……劇場的空間距離,使得觀眾明白了自己在劇場中的身份。
劇場的空間距離劃分了觀眾與演員的界線,使得觀眾辨別了生活與虛構之間的區別,明白了現實與假扮的尺度規則,區別了“真人”和他所扮演的“角色”,知道“演員”與“角色”共存一體,這“莊嚴的距離”,使得每一出風格迥異的戲劇演出都可以潛移默化地在觀眾與演員之間達成相應的默契與共識,戲劇演出由此得以正常的進行而不會被觀眾的參與來打斷,當然也有部分戲劇導演和戲劇流派打破這種空間距離,使觀眾和角色共同參加表演,但演出成功與否,作品流傳與否,另當別論。
二、“觀”與“演”的心理距離
舞臺上的戲劇演出能引起觀眾的共鳴。觀眾是各種各樣的,他們的職業背景不同,年齡不同,性格不同,種族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有些觀眾剛接觸到戲劇,有些觀眾卻在戲劇藝術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興趣。但這些人一旦進入劇場,就變成了一個統一的“觀眾”。“劇場的特點在于轉變,使舞臺轉變為戲劇空間,使演員轉變為角色,使來賓轉變為觀眾。”[3]舞臺消解了不同觀眾的社會等級,當這些不同身份的人在席上就座的時候,劇院大燈一黑,變成了完全意義上的“觀眾”,沒有身份地位、民族年齡等諸多差別。使得觀眾和演員之間在劇場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中進行了精神的交流,演員將劇本中“最戲劇”的一面通過表演的方式表現給觀眾,觀眾在進行戲劇欣賞時的劇場反應,又影響了演員的表演。
一出戲,只有上臺演出同觀眾見面以后,觀眾才能對其進行揣摩,干預。一出戲的劇本并不就是這出戲,戲劇藝術的完整生命存在于戲劇舞臺的演出當中。戲劇藝術本身有雙重性,一個存在于文學中,另一個存在于舞臺上。文學和舞臺上的戲劇藝術共同追求的是“戲劇性”。“戲劇性”是戲劇藝術審美特性的集中表現,案頭劇可以讓讀者在頭腦中想像出人物的音容笑貌,推斷出故事的前因后果,一次讀不完可以再次讀,一次讀完后也可以再次讀,而在劇場觀看戲則不同。在劇場中,觀眾所面對的是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必須一次看完。劇本只勾勒出了戲劇演出的基本特征,而并非是一個復雜的具有氣息、精神等的演員。戲劇的力量就在于演員同觀眾之間進行生動而直接的相互感染,觀眾可以在戲的進行之中影響演員。優秀的演員能用心靈去接受觀眾傳遞過來的消息,達到自己與觀眾之間在精神上的融合。戲劇理論家阿·波波夫說:“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天才的演員,能夠在空空蕩蕩的劇場里靈感充沛地進行創造。”由此可見,觀眾和演員在劇場這樣一個有機的整體當中是既相對獨立又互相影響的。在觀看演出的過程當中,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演員在每一個晚上的演出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現場演出中差錯隨時可能發生,每一個演員都試圖演得比上次更好,不斷追求自我超越。觀眾深知這一點,也在期待著演員能有卓越杰作,這種意識帶來的興奮和激動是在影視劇銀幕上的演出所不具備的,這給戲劇帶來了一種特別的生命力。
觀眾看戲時有時會被深深地吸引到戲里,幾乎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及自己的存在,在情感上與角色發生共鳴,仿佛自己就是舞臺上的一個角色。“觀眾在觀看展示在他們面前的一切,他們對舞臺上所發生的一切就了一個默不作聲的參與者。在某種意義上說,觀眾就變成了那出戲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4]觀眾在看戲的過程當中,不會大聲喧嘩或介入舞臺上的演員表演當中,因此,此時的觀眾就像一個“偷窺者”,根據所看到的,觀眾會哭泣,會大笑,會生氣,會嫉妒……據說,美國某劇團公演《奧賽羅》時,突然一聲槍響,扮演依阿古的演員倒在了舞臺上;在中國三年內戰期間,解放軍同志在演出歌劇《白毛女》時,也有觀看的戰士舉槍差一點兒將惡霸黃世仁打死。這些例子都說明了觀眾在看戲時,會被舞臺上的人或事所打動,這個時候,他們會情不自禁地完全將自己當成是舞臺上的一個角色,或者感到整個戲正好表達了自己的生命體驗,于是便沉浸在戲里,忘乎所以,“發現自我”,于是有些觀眾就將這種審美活動變為了實際行動,“世界上最好的觀眾與最好的演員”的例子其實就是觀眾自己的思想感情及心理活動跟著劇情和人物起伏跌蕩后所進行的審美活動,而這種活動,其實就是觀眾與演員之間精神交流的產物。
觀眾通過看戲及對演員的角色理解,不但參與了“劇場演出”,還影響了演員,影響了劇本創作。從表演的角度看,戲劇演員面對的是觀眾,舞臺;演員是以角色和個人的雙重身份與觀眾進行交流,他們可以感受到觀眾精神的緊張與松弛;從欣賞的角度來看,觀眾面對的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因此他們可以將自己的感受反饋給演員。不同于電視和電影,戲劇是個“此時此刻”發生的現場事件,演員和觀眾相互作用,各自都完全意識到對方的近距離存在。演員和觀眾二者在劇場中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中牽掛著舞臺上同樣的戲劇事件。觀眾的每一個反應都會直接影響每個演員的表演。而電影、電視演員面對的是攝影機鏡頭,觀眾的反應他們不可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觀眾觀看影視劇的感受也無法傳遞給演員。
戲劇的觀眾兩、三個人結伴或一人來看演出,都可以在劇場中很快地和其它陌生觀眾融入共同的經歷中,悲同一件事,喜同一句話,了解同樣的秘密,別人鼓掌時自己也鼓掌,離開時可以興致勃勃地談論著才結束的演出……而影視劇的觀眾基本上是單個地與銀幕建立關系,極少會做出集體的反應,更不會鼓掌,而且,頻繁出現的廣告會使屏幕前的觀眾不能全神貫注地欣賞。銀幕雖然使得觀眾與演員之間有了空間距離,但心理距離卻淡化了,因為銀幕切斷了觀眾與演員的交流。電影電視的欣賞者們只能被動接受。
巴贊說:我們不得不承認,當幕布落下之后,戲劇給我們留下愉悅,比起看完一部好影片獲得的滿足有一種難以言傳的更令人振奮,更高雅的東西,也許,還應該說,更有首先教益。似乎我們會因此而變得情操高尚。……從這一觀點看問題,我們可以說,即使最優秀的影片也有“某些缺憾”。猶如有一種不可避免的降壓作用,有一種神秘的美學上的短路現象使電影缺乏戲劇所特有的某種張力。這些差別固然細微,卻是實際存在,即使在拙劣的說教式的演出和勞倫斯·奧立弗改編的精彩絕倫的影片之間,也有這種差異。這種現象不足為奇。戲劇在電影問世五十年后,仍有生命力,從而打破了馬賽爾·帕涅爾的預言,就是最具體的證明。[5]
戲劇演出就是在“劇場”這樣一個現實的直觀的世界里,再現了藝術家虛構的并且由觀眾的想象力加以完成的一個非現實的世界。演員和觀眾之間的“觀”與“演”這樣一個必要的距離使得演員能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內去向觀眾展示無限的空間和時間。使得不同的觀眾都能在劇場中看到了自己想看的東西,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正是“觀”與“演”之間這適當的距離才使觀眾對演出的戲劇有了美的認識與體驗。
注釋:
〔1〕《戲劇性與其它》,奧·維·史雷格爾《古典文藝理論譯從》(11)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240頁。
〔2〕杰·威廉斯《作家創造觀眾》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頁。
〔3〕《戲劇藝術》2003年第2期,約瑟夫·斯沃博達《論舞臺美術》第64頁。
〔4〕《讓觀眾像知心朋友那樣了解你自己》懷特,李醒編《論觀眾》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頁。
〔5〕安德烈·巴贊著《戲劇美學與電影美學》《世界藝術與美學》(3)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頁。
參考文獻:
〔1〕《論觀眾》李醒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版
〔2〕《論演出的藝術完整性》阿·波波夫著,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版
〔3〕《清代以來的北京劇場》李暢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4〕《古典文藝理論譯從》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
〔5〕《戲劇美學》朱棟霖,王文英著,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6〕《西方戲劇·劇場史》李道增著,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7〕《戲劇藝術十五講》董健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8〕《美學十五講》凌繼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9〕《中國美學十五講》朱良志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簡介:
韓蕓霞,藝術學院影視戲劇學院1978年4月,蒙古族,中國傳媒大學戲劇戲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從事少數民族戲曲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