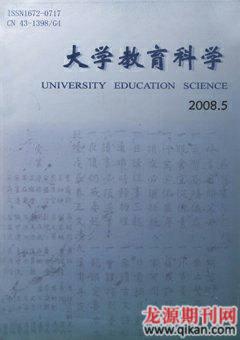外在規約:鄉村教師公共性旁落的根源
張儒輝
鄉村教師公共性旁落的根源主要在于鄉村教師發展方法上的失誤,這種方法失誤不是來自鄉 村教師本身,而是來自鄉村教師以外的“他者”,或者說是一種“外在規約”。
一
“外在規約”的第一個表現是,鄉村教師在遵循“科學”邏輯的教師專業化過程中,在提升 自己專業素質的同時,也逐漸被淪為教育學客觀知識的奴隸。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 落研究》一書中,把公共知識分子日益衰退的原因歸之于知識的過于專業化和職業化,學科 之間難于溝通,任何個人僅是本專業的權威,從而導致了自身公共性質的衰退。與 其它知識分子公共性質日益衰退的原因不同,鄉村教師不僅公共性質與社會責任日漸失去, 而且 其專業化水平與生存狀態相對于城市教師來說總是讓他們自慚形穢。雖然鄉村教師勤奮刻苦 ,孜孜不倦,但他們一直處在一種盲目追趕城市教師、自我貶抑和經常受到“教育專家”的 種種指責、批評的怪圈之中。他們既沒有走進學院的象牙塔,蟄居在幽靜的書齋里,具有像 波斯納 所描述的人文知識分子內心的自私;也沒有把社會責任感和社會良知提高到意識層面,而是 規范于現代教師知識體制的專業化軌道中,成了一個教書、組織考試和應付考試的機器。他 們所 持有的教學思想與大學教育學專家所要求的教學思想難免存在較大差異,其后果是鄉村教師 的主體意識缺失及自我選擇意識薄弱,這是獨特的中國鄉村教師公共性表達的主體邊緣或主 體抑制的問題。
假如一個大學專家在書房里產生的思想是有價值的,那么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中小學教師在 教學實踐中產生的思想具有同樣的價值,雖然兩者可能有一些“英雄所見略同”的東西 ,一旦教師發現大學專家的東西無用時,難免發展為互相欺騙,因為他們都無條件地要求他 人相信某種東西,兩者的意見沖突總是容易導致難以合作的局面。學校內部的知識可以停留 在 個體層面上,也可以為本機構的成員分享。個體知識乃是個體“擁有”的知識“庫存”,可 以獨立地用之于完成特定的任務、解決特定的問題。它也可以流通,隨個人而動,成為學校 集體知識;學校集體知識意味著知識如何在教師群體之間傳布和分享。學校的規章 、程序、 慣例和共享的準則中儲存著它所積累的知識,而引導學校教師解決問題的行為,決定其行為 的互動模式。它既可以是作為實實在在的數據儲存起來的“存貨”,也可以是通過交互作用 而處于“流通”狀態的知識[1]。
目前鄉村教師發展的任務是,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其行為方式,尊重鄉村教師的公共性 質及其與鄉村教師專業化的統一性,對片面的鄉村教師專業化發展模式進行反思、 批判,并提出建設性意見。我們必須認識到,鄉村教師的勞動價值主要通過自主的勞動選擇 及通過培養的勞 動者素質體現出來;通過在農村傳播、接受、運用與轉化人類先進科學技術成果體現出來; 通過自己與學生的共同發現、建構、理解和創造科學技術成果體現出來,等等。從這個意義 上 講,鄉村教師之于農村不只是一個教育者,更是名副其實的農村經濟社會的建設者,它在農 村承擔的未來責任的意義是明顯的。
二
“外在規約”的第二個表現是,擬像時代虛假的公共生活繁榮與遵循商業邏輯的擬像媒介, 使鄉村教師失去了表達空間。擬像時代是指1970年代以來的,以計算機網絡與賽博空間為主 要生產工具的擬像生產時代。計算機信息處理、媒體和自動控制系統,已經取代了機器的生 產地位而成為社會的組織原則;模型、符碼和控制論所支配的信息與符號成為社會最重要的 組成部分。擬像時代帶來了“公眾消費文化的膨脹和以技術專家面貌出現的專業知識分子為 主宰的媒體盛況”[2]。就傳統強調的傳遞確定的知識而言,鄉村教師并不比存 儲網絡更有能力。由于電腦功能越來越全,教學可以由機器和網絡來代替,接受知識成 為與機器 打交道。因此,文化的繼承與傳播已經難以通過感情對話和交流的方式在課堂中進行。正如 利奧塔寫道:“教授們的教學仍然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教學已經減少到只教給學生如何使用 終端機的地步。如果不具備合法的‘堂皇敘述,就不需要教授們去教育學生,人們可以依 靠機器教給學生在被表現行為所驅動的社會里所需要的知識”[3]。
可見,鄉村教師在當代面臨的重要挑戰是其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空間發生了質的變化。正如許 紀霖在 談到專業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時所說,在現代化社會的早期,作為國家體制一部分的大學 還 沒有像今天這樣擴張無邊,文化也遠遠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商業機制壟斷,因而社會的公共文 化生活還是完整的,知識分子可以以自由職業者如自由作家、自由藝術家的身份生存和活動 ,他們的心靈是自由的,可以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2]。這一論述也適合 當前鄉村 教師的生存處境。目前的鄉村教師,除了依賴機器對知識的生產以外,已經無法為教學提供 新的血液,他們正在成為機器的附庸和他者的奴隸,逐漸失去創造力和想象力 。與此相 應,農民遠離鄉村教師也是理所當然,他們為一種自發的經濟興趣所左右,追求著官能的滿 足,拒絕了鄉村教師的諄諄教誨,“下課的鐘聲已經敲響,知識分子的‘導師身份已經 自行消解”[2]。由此,與那些過去在“象牙塔”里追求學問的知識分子有區別 ,鄉村教師拚命地學習,提升自己的專業素質,但是他們因為脫離了平民語言 ,遠離了自我 生存土壤,而終究難以達到現代化要求的教師水平,結果諸如知識恐慌、職業生存恐慌、角 色恐慌在他們中彌漫開來。隨著鄉村教師公共性質的消彌,農村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 衰落了。
三
“外在規約”的第三個表現是,技術官僚過度的人為性行為,使鄉村教師成了一個“教學 機器”,無法有自己的生活。對教學改革與創新而言,鄉村教師遠不如技術官僚有號召力。 技 術官僚由于其政治地位與話語權力,頻頻被邀在媒體亮相,發表所謂的大家關心的問題。在 鄉 村教師的管理方式上,逐漸采用企業化的科層管理模式,教師被按照嚴格的學校類別與縣級 管 理進行培訓和流通,并且以一套嚴格的行政規范對其教學成果進行業績評估。縣級教育 體制與學校內部的激勵措施和利益誘惑,吸引了一大批鄉村教師進入體制軌道內部尋求歸宿 。但在教育生活內部,他們不再可能像過去那樣可以按照自身的興趣愛好思考、寫作和游說 ,只能在教師專業標準的規訓之下,為高一級學校提供高質量的學生產品,并且按照教師技 術職稱等級評價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資本和職業權威[2]。
鄉村教師除了按部就班地執行教育行政命令與復制城市教師的教學模式以外,很難有創造性 思考與行為。這種現代性管理方式,形成了鄉村教師之間,以及鄉村教師與農村社會的雙重 斷裂。一方面,原先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一個個單位學科,知識者之間不再有共同的 語 言、共同的論域和共同的知識旨趣。另一方面,他們面向考試,追求升學率給他們帶來的績 效,背對農村社會,他們與“田園牧歌”的有機聯系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一個封閉的、 孤芳自賞的階層[2]。這樣就導致鄉村教師的公共性質與社會責任的缺失,甚至這 種缺失一直在理所當然中不被查知,在潛移默化中被現代性合法化。同時,也使鄉村教師個 體產生一種孤獨感、邊緣感與軟弱無力感。
上述三種趨向,表面看來是鄉村教師被客觀知識、教育學專家、技術官僚與媒體 明星的話語霸權壟斷,導致其公共獨立意識喪失,但其深層原因,在于它們同被一個現代理 性 法則所支配。由于現代性制度造成的知識體制的專業化和文化生產的商業化,使大學教育學 專家、教育技術官僚及相應的教育技術組織措施等,對鄉村教師形成了話語的多重權威,使 鄉村教師失去了自我選擇、自我行動與自我創造的可能性。在知識生產領域,知識本來所具 有的實踐性與體驗性被切斷了,它們不再向整個世界和社會提供意義,因而也就失去了鄉村 教師之于農村的價值關聯。技術專家、行政官員與媒體明星的三重唱,形成了以技術化 和商業化為主調的世俗意識形態,使鄉村教師失去了獨立意識。 他們不得不放棄田園牧歌,在城鄉生活的時空背景中艱難地追趕著城市教師或教育學專家 興起的接二連三的教育改革浪潮。這也是鄉村教師的悲劇所在。充滿生氣和機遇的城市生活 對于身處封閉和貧困環境的鄉 村教 師,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構成了一種雙重刺激,使他們完全失去了與城市平等對話 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阿麗絲?拉姆.知識經濟中學習和創新的其他模型[J].國際社會科學雜 志,2003,(2):68.
[2]許紀霖.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EB/OL]. http://philosophyol.com,2004-07-07.
[3]賀旭輝.利奧塔后現代思想闡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6,(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