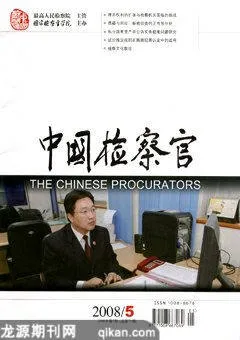檢察文化散論
筆者作為一名檢察官,對“檢察文化”一詞并不陌生。對檢察文化耳熟能詳的同時又誠惶誠恐:到底什么是檢察文化?檢察文化和法律文化究竟是什么關系?檢察文化的特質是什么?這一系列基本問題的回答,是我們打造檢察文化,弘揚檢察文化的前提。
筆者查閱了一些關于檢察文化的探討和論述,遺憾的是對檢察文化的內涵均語焉不詳。這種混沌的情況對于提高檢察文化品位,促進檢察事業發展顯然是十分不利的:概念不清必然導致思路混亂,思路混亂必然導致行為迷失。
從廣義上講,檢察文化是指檢察官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的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道德準則、精神風范等一系列抽象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的總和。它包括檢察制度文化、檢察精神文化、檢察物質文化3個方面。檢察文化不是從來就有,也不是憑空產生,而是隨著檢察事業的茁壯成長而逐步形成的。這種文化的發生、發展和發揚,對于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都有巨大的激勵、約束、引導、塑造、滲透等功能。
檢察文化如此重要,這已經是業內人士的共識。如何對檢察文化的內涵有深刻而正確的認識,以便打造更高水準的檢察文化,則是很多人面臨的困惑。筆者斗膽一試,對檢察文化進行層層解剖,追根溯源,通過分析檢察相關概念,最終達到認識檢察文化的目的。本文中,筆者分析但并未窮盡所有檢察相關概念:主要有檢察、文化、檢察院、檢察官、檢察職業群體、檢察業務等等。
單就“檢察”而論,只是一個普通動詞,并無重大討論價值。檢察職業、檢察官、檢察機關、檢察業務等等都是由“檢察”派生而來,含義也變得頗具討論價值了。所有這些檢察相關詞,在學界,有人把它叫做檢察學,以圖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來研究。經過理論爭鳴和實踐探索,檢察學的學科地位似乎還未有定論。爭論的焦點在于:檢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專門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它的研究方法有何特點?這是任何一門學科得以確立的基本標尺。一些學者認為,檢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被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等法律所涵蓋,沒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也沒有成為獨立學科的必要,設立檢察學有因事設學科的嫌疑。不過力主派也是言之鑿鑿的:檢察工作是專門工作,任何機關都不能代為行使,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因而有成立專門學科研究的必要。
檢察學的獨立學科地位能否得以確立,不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筆者之所以要對此進行簡單涉及,主要想說明人們對檢察職業的認識還遠未達成共識,只有對檢察相關概念有了清晰的認識,才談得上建設檢察學科抑或檢察文化。
文化,按照通常的理解,主要包含3層含義:
一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二是考古學用語,指同一個歷史時期不依分布地點為轉移的遺跡、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同樣的制造技術等,就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
三是運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識,如文化水平。
而在不同的語境下,文化的具體含義并不一致。檢察文化中的文化含義,應該理解為文化含義中的第一層含義為宜,也是人們對文化的通常而廣泛的理解。當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對象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又客觀存在,這給嚴格定義研究對象帶來了不小的難度,對文化進行定義亦然。文化大師可能對文化的內涵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在這里不再進行逐一的介紹,本文對文化的理解只選取多數人的共識。
檢察文化,很顯然是一個合成詞。檢察原本是個動詞,可是被賦予了機關名稱以后,名詞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其本身所蘊含的意義也是十分豐富的。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種概念,可以產生出很多分支來,檢察院、檢察官、檢察職業共同體、檢察業務等等都是很好的研究分支,可以作為一個博士論文標題了。
把檢察和文化聯系在一起,給檢察冠以文化的光環,這既是后人的智慧,也是檢察職業自身發展的需要。古人曾經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即指立言立文,如果沒有文采的話,不會流傳久遠,也很難產生良好的藝術感染力。一個機關、一個團隊、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如果沒有文化支撐,也很難形成自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基本目標的企業,之所以要耗費巨資去打造自己的企業文化,也正是看重文化在企業發展中的長遠價值。由此觀之,檢察文化這個提法,不但是沒有錯的,而且是必須的。有怎樣的檢察文化,就會產生怎樣的檢察職業和檢察隊伍。如果沒有理性的、科學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檢察文化被檢察職業群體內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就很難對檢察事業的發展提供明確的指引,這是筆者要探討檢察文化的最根本的緣由。
人民檢察院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這是憲法等多部法律對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界定。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檢察院主要有偵查監督、決定公訴或者不起訴、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監所檢察、民事行政檢察等等法定權力。在以上所列的主要權力子系中,除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司法實踐中稱為職務犯罪偵查權)少見法律監督的品質外,其他的權力體現了一定的監督制約性,這是職務犯罪偵查權受到詬病的重要原因。民行監督、事后書面審查的偵查監督等在實踐中也運行得十分艱難,與監督者的名稱相去甚遠。
更為嚴重的是,理論上的法律監督權,在事實上成為了脆弱的案件監督權,把法律監督局限于案件監督,這是對法律監督權的重大誤讀。須知法律于社會生活的介入程度,遠遠超越了案件的范圍,轉為案件的,是法律問題尖銳化不可調和的產物,公民守法、機關立法、政府執法等等都是法律調整社會的范疇。
在現代社會中,法律是必不可少的“調節器”。法律監督也非我國所獨有,在西方發達國家,法律監督的成果或許在某些方面已然走在我國的前面,但檢察院并不一定是每個國家都設立。典型的如美國,沒有檢察院,但有出色的、精英的職業檢察官,斯塔爾對克林頓的發難就可以看出檢察官的巨大威力。獨立檢察官制度雖然在美國已經壽終正寢,可是檢察官的聲音并沒有消失。在我國歷史上有一段歷史,檢察院被撤銷,雖然后又恢復,但學界和實務界對檢察院的定位還存在重大分歧,法律定位為司法機關,運作上的行政色彩十分濃厚,很難歸入某一簡單類別。
檢察官,在中國的法律語境里,出現的頻率遠遠不及“檢察干警”。除了非常專業的人士,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用到“檢察官”一詞。這種漠視,并不是人們無知,而是反映了人們對檢察官這一特定稱謂缺乏理解和認同。不但如此,很多身為檢察官的人士也沒有多少身份意識:雖為檢察官,很多人并不知道檢察官任職的條件、檢察官的等級、甚至連自己屬于幾等幾級都不知道。在專業化如此淡化的職業里,人們為之奮斗的,也許不是高級檢察官或者大檢察官的榮譽,看重的乃是其行政級別。同時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只有行政級別“上了”,檢察官級別才會如影隨形,所以人們對檢察官的級別也就泰然處之。有人曾經戲言:如果要想迅速成長為檢察長,那么,最好初次就業別去檢察院,最好也別學法律。大量非法律人士因為成功的“曲線救國”,在擔任檢察機關領導的同時獲得了比高級檢察官更高級的檢察官稱號,事實上他們并沒有經過嚴格的法律專業訓練,也沒有升任助理檢察員那樣參加統一司法考試,綜合素質好或者政治素質好這才是他們最為耀眼的光環。這是對法律職業專業化、檢察官職業專業化的巨大嘲笑。當然,這樣的現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尤其是成長時期的職業里是難以避免的,比之以往,進步不可謂不大,并可望得到進一步矯正。
檢察職業群體,這是比檢察官更廣泛的一個范疇。所謂檢察職業群體,是指在檢察院內部,為了檢察事業而工作的人。很多法學家,為了檢察改革奔走呼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但他不在檢察院工作,而是在大學工作,只是他的視線看到了檢察院里這樣那樣的東西而盡的一份良心或者學術責任,不能算是檢察職業群體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譬如檢察院的專職書記員、事業編制的職工、法醫等工作人員,他們不是檢察官,但是對檢察業務的順利開展,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他們也以檢察工作作為職業選擇。事實上,專職書記員等在檢察院內部承擔了大量基礎性和繁瑣的工作,尤其是不在編制、從社會聘請的書記員,酬薪偏低,工作辛苦,職業不穩定,這已經成為制約檢察院穩步發展的因素之一。
檢察職業群體雖然在檢察院工作,但不具備檢察官的身份,給檢察職業群體的個人發展帶來了一個難以制約的瓶頸。在一些單位,為了讓檢察職業群體也看到前途,對書記員也可以提干,也讓書記員獨立承辦案件,當主辦官或者案件負責人等表示重用,在對外簽名的時候作出技術處理,體現內外有別。實踐中的靈活變通并非絕對不可,在實踐中,有不少年紀稍長但學歷偏低的人,雖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辦案經驗,可是苦于未能通過統一司法考試而不具備檢察官資格。司法考試的內容是精細而廣泛的,而每項司法實務是具體的,對知識的要求也是具體的,這就給這樣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平臺和展示機會,實踐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總體而論,受過嚴格法律專業訓練,通過統一司法考試的檢察官,其專業水準肯定比檢察職業群體高。也許是人生經驗還不夠豐富,理論和實踐的對接還有待磨合,新的環境需要他們去適應,照顧檢察職業群體的感受,資格不夠老等等,一些檢察官們長期從事瑣碎的、與業務不掛鉤的輔助工作。長此以往,必將在專業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檢察業務,一向被視為檢察學科探討的重點和歸宿。成立檢察科學,打造檢察文化,引進高素質的法律專業人才,都是為了促進檢察業務走上科學、理性和規范的專業化道路。如果把檢察業務看成一個子系統,下面又可以細分偵查監督業務、公訴業務、職務犯罪偵查業務、民行業務等子系。通常地,人們根據檢察業務的性質,把檢察業務主要分為刑檢業務和職務犯罪偵查業務。這兩種業務的工作特點是大相徑庭的,對從業者的素質要求也存在很大差異。從事偵監、公訴等刑檢工作的人,要求具備非常專業的法律訓練,對法律知識有系統而精確的把握;從事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人,則一定是頭腦靈活,知識面廣,善于揣摩和把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