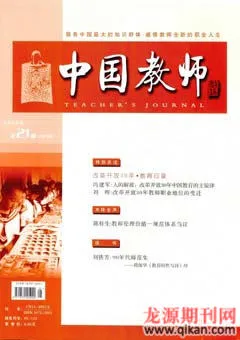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芻議
從教育組織與授業職能發生開始,教師的品性與授業行為正當性就受到人們的關注。這是由于教師的品性與行為對學生可能產生直接的影響。唯從“學無常師”時代到師生關系定型的業師出現,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師數量的增多,教師的價值傾向與職業行為規范才作為帶有普遍性的課題,引起越來越深入的思考。
無論在東方社會文化中,還是在西方社會文化中,關于教師價值傾向與職業行為規范的思考,都經歷了從張揚這個那個信條與戒律,到形成一定范疇的過程。
中國古代率先形成“師道”觀念,西方近代教師職業化以后,逐步形成了“師德”概念和師德規范。到了現代,又提出“教師專業倫理規范”和“現代教師的職業精神”之說。所謂“現代教師的職業精神”,并不是取代“師德”的概念,實際上是超越“師德規范”的“現代師道”觀念。所以,“師道”“師德”“教師專業倫理”和“現代教師的職業精神”,并非同義語。它們各有專門的含義,分別是教師演變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產物,又各有局限性。
惟其如此,現在的問題是在歷史地、具體地考察相關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
一
“師道”一詞,據先師蕭承慎教授考證,出自西漢蕭望之和東漢桓榮的奏折。[1]原非通行的概念。從唐代韓愈《師說》開始,以“師道”為主題的“師說”層出不窮。除柳宗元答韋中立、答嚴厚輿“論師道書”以外,尚有:宋代柳開《續師說》、王令《師說》,明代王世貞《師說》、李贄《真師二首》、張自烈《續師說》,明清之際黃宗羲《續師說》與《廣師說》,清代翁方綱《擬師說》、章學誠《師說》、姚瑩《師說》,以及胡薇元《師說》等。表明在中國古代,“師道”已成為通用概念。唯不僅從魏晉至唐代“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從唐代至有清一代,各家“師說”仍因師道失傳有感而發。故都屬針砭時弊之作。惟其如此,所論“師道”的含義也就失之寬泛。
韓愈《師說》為“師道”的代表作,也是傳世之作。后來各代師說都是從韓文談起。至今仍然間或如此。韓文中“師道”的含義似乎很明確,如他所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也。”表明“師道”主要是指教師在授業過程中傳道與解惑。唯此文中,并未討論教師傳什么道,如何傳道,如何解惑,而針對“士大夫之族”恥于相師,強調“古之學者必有師”,又道“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表明其中所論,主要為學子的“為學之道”,“為師之道”反在其次。不僅如此,其中所謂“師”,亦不限于身份固定的業師,還屬“學無常師”之師。頗有“師道”“學道”混淆之嫌。
如果說韓愈把師道失傳歸咎于世人恥于相師,那么后來的師說,越來越把鋒芒指向徒有師名的所謂“名師”。宋代年輕學者王令痛心疾首地指出:“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門,徒教粗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明清之際,黃宗羲更“反昌黎意”,作《續師說》反問:“師道之不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他在《廣師說》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的流俗,除句讀之師以外,更有舉業之師、主考之師、分房之師、薦舉之師、投拜之師。這類植根于應試的當紅之師,其實同傳道、授業、解惑并不相干。名氣雖很響,反而不如普普通通的句讀之師名副其實,因為一般童子之師畢竟還在授業。
盡管世事如此,古代畢竟還是涌現出一批善待弟子的教師楷模和尊師重道的弟子典范(黃宗羲在《廣師說》中多有羅列)。關于應試傾向導致學風淪喪、師道變質的揭發,至今仍不失警示價值。更重要的是,在條件成熟時,“師道”將成為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價值層面。
二
教師的品性與態度,比其他職業從業人員的品性與態度,更容易受到公眾關注。這不僅由于教師以未成年的學生為教育對象,其品性和態度可能對學生產生直接影響,而且由于公眾中有過受教育經歷的成年人,對教師的品性與職業態度能夠作出比較,也就對在職教師的品德比較敏感。
不過“師德”是個晚出的概念。在比較完備的教師道德規范形成以前,近代早期學校的章程中即包括規范教師行為的條款。個別嘗試建立國家教育管理體制的國家,學校主管當局頒發的學校規程中,更對教師的職業行為加以規范。隨著獨立的教師組織的產生,更把厘定教師道德規范,作為專業自律的必要措施。
關于學校章程中的教師道德規范,以18世紀“基督教兄弟會”(由拉?薩爾于1720年擬訂)的學規《學校指南》為例。其中關于教師的規定有:“每天要教半小時的《教義問答》”“無論何時都不得接受學生或家長的錢財或其他饋贈”“要對所有貧苦學生一視同仁,要愛窮人事業更甚于愛富人事業”“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和舉止,以便在謙虛和一切其他應教給學生并身體力行的美德上,永遠成為學生的榜樣”“要極其謹慎小心,極少懲罰學生”“不論何時,他們都不要給學生起任何侮辱人格的渾名、綽號”……[2]此學規至少沿用至19世紀初期。
普魯士腓特烈國王于1763年頒布的《全國學校規程》。其中的教師規范如下。
對教師的要求:……“教師不僅要具備必要的教學能力和技巧,他還應當是兒童的表率,不可將自己每日教導的結果,毀于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壞榜樣”;
對教師行為的管理:盡管我們認為貴族和其他資助人,擁有招聘教師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我們的有關負責人、視察員以及教士,必須監督他們,“不得將任何不稱職的、不適當的或放蕩的和邪惡的人,聘為教師,或保留在職”“所有教師都不得開設酒菜館、出售烈酒或啤酒,或從事任何妨礙其工作的職業”“不得有任何以其榜樣引誘兒童養成疏懶或放縱之惡習的行為。如閑散游蕩、在晚宴或舞會上演奏音樂等”。[3]
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教師數量增加,教師成為社會分工中的職業,遂有獨立的教師組織產生。從19世紀開始,美國陸續建立的教師組織,如:全國教育協會(原為1857年建立的全國教師協會,于1870年更名,縮寫為NEA)、全國天主教教育協會(成立于1903年)、美國教師工會(1918年建立),以及教育研究機構。
教師組織旨在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建立教師道德規約,規范教師的職業行為,并把履行這種規約,作為自愿參加教師組織的教師對該組織承擔的義務,以保證教師職業的聲望。其中影響較大的,為全國教育協會厘定的《教育專業倫理典章》(1929年提出,現行倫理規范于1975年修訂)。
近代師道與我國傳統的師道區別在于:我國古代雖有官學、私學的設置,以教師為謀生手段的人越來越多,而對于為數最多的蒙學教師的職業行為,主要按照習俗行事,并受輿論調節,其規范隱含于習俗之中。當時的“師道”之說,其鋒芒主要指向“士大夫之族”對設學授徒的偏見與漠視,同為數最多的一般教師并無多大干系;近代師德則是在教師趨于職業化的背景下,規范一般教師的職業行為。主要為戒律,禁止有礙本職的行為與反教育的行為。教師組織約定的師德規范,則是職業自律題中應有之義。如果說我國傳統的師道,主要著眼于教師本職(授業)以外的需要,尤其是傳承儒學道統的需要,或針對教師職能以外的傾向,主要是恥于從師的傾向,那么,師德則是關于教師職能活動本身的規范。
三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教育事業日趨制度化,傳統教育價值觀念在變化中。由于師德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規范教師的職業行為,而不足以影響教師的就業動機與教師價值取向,故有重新張揚“師道”的必要。
日本學者小原國芳,針對近代以來教師重術輕道、重利輕道的傾向,在日本12世紀教育家山鹿高祐的師道學說啟發下,重新提出“師道”問題。
山鹿高祐,字子敬,號素行,世稱山鹿素行,為日本師道學說的先驅。他只比黃宗羲小六歲,比黃宗羲早死十年。可算是黃宗羲的同齡人。他雖崇尚孔子儒學,卻與程朱陸王的理學異趣。其師道學說與中國的師說亦大相徑庭。
他認為“師者,志也”,而“志者,盡人之道也”。其“師道”的要義為:[4]
1.人之范,行之則,乃為師。
2.為有志于為人之道者,乃為師。
3.眾望所歸,而不得不為人師者,可謂真正之師。
4.教育終以道德教育為中心,故而恪守師道。
小原國芳作《師道論》,對于“師道”的本義、內容重新加以解釋。他旁征博引,反復舉例,說明“道”與“術”的區別和重道的意義。
他認定“師道就是斯賓諾莎所教導的‘在永恒世界中’,追求永遠之道的意思。就是以堅定不移之心,遵從理性的啟示”。[5]
“術”就是技術,是技巧,“道”就是“宇宙的大法”。[6]
以奧林匹克競賽為例,光比紀錄,比速度,比獎章,“只教以取勝而忘掉了道,可哀可悲。”[7]
“教師的工作也不可墮落到光傳授知識。還必須像耶穌所說的‘我就是道’那樣,有扎根于堅定信念的道。”[8]
小原國芳扎根于其堅定信念的“道”,便是所謂“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價值框架[9]如表1。

上述師道論同中國傳統師說的區別在于,我國古代師說,多為針砭世事、矯正時弊之作。唐宋師說主要針對士大夫之族,不僅恥于從師,而且以師為笑談。明清師說的鋒芒則指向謬托師名的偽師,而對于為師之道,反而甚少論及。鄭曉滄在其《廣師說》中(原載1938年6月4日的《教育通訊》第11期)評論韓愈《師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韓氏所謂‘受業’云云,殆為‘授業’之意”。唯“韓氏對于此點,未加發揮,其文之后段,且敝棄之(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欲不言受業或授業)。韓氏因著重于‘傳道’云云,于‘業’則非所重,殆猶是吾國士大夫之素習”。[10]相比之下,日本學者從山鹿素行到小原國芳的師道之論,則屬為師之道。客觀上由于中國古代師說以“非師者”中的“反師道現象”為批判對象,而小原國芳則針對教師中的“重術輕道、重利輕道現象”。倒是黃宗羲的《續師說》與《廣師說》,對于“應試教育”風潮中的某種“名師現象”,至今仍不失警示的價值。
小原國芳的《師道論》,旁征博引,反復舉例,卻缺乏謹嚴的論征,以致其“師道”概念并未展開,但其精神還可以領會。說得明白一些,便是以教師職業為自己的事業,對教師職業有敬畏之心,立志為教師職業的完善而堅持不懈的努力。這不是“師德規范”所能解決的問題。
四
如上所述,小原國芳的師道論,其“師道”概念并未展開,也就沒有形成思路。他所提出的教師的信念和“師道”的內容,是他所倡導的“全人教育”,從而把“師道論”折入“教育論”。好在同時期杜威提出的“教師的職業精神”,倒有助于打開“師道”的思路。
“師道”,原是植根于東方社會文化中的概念,萌生于西方社會文化中的杜威學說中提出的“教師的職業精神”,實相當于“師道”。
杜威于1919—1921年間在華講學中,多次作過以“教育者的天職”“教育者的責任”為專題的演講。其中提出了“教師的職業精神”概念。
他提出教育者的責任如下。
1.對于知識應負的責任:教師不是把自己頭腦中的知識“搬出來”教給學生,就算了事,“必定要培養一種興趣,對于學問上有很大的熱忱,有繼續研究的精神,時時在知識改造中”“這種研究精神,是學生的精神,也是教育者應有的精神”。[11]
2.對于學生應負的責任:“做教育者,如能對于學生有一致進行共同利益的觀念,視學生的快樂就是自己的快樂,學生的進步就是自己的進步,那么,不但不以為苦惱,轉覺得很快樂的了。”[12]
3.對于社會應負的責任:教師“不但注意于學校以內,更當注意于社會。不但做學校的教師,更當做社會上一般人的教師、學生家屬的教師。個個教員有這種意思,繼續地做去,那么,中國前途很有希望”。[13]
由于教師的本職為教學,并在教學過程中教育學生,故每個時代都不致忽視教師掌握所教學科的知識。近代教育趨向發展學生的個性,相應地要求教師尊重學生個性,并為發展學生個性奠定基礎;到了現代,逐漸意識到學生的個性,其實是個體社會化過程中顯示出來的差異。學校教育旨在促進個體社會化。為此,就有必要溝通學校與社會之間的聯系。相應地要求教師具有社會責任感。不僅使學校教育適應社會需要,而且主動為社會服務,以促進社會進步。
在這里,不僅反映時代潮流,賦予教師以社會責任,而且使教師對知識的責任與對學生的責任獲得新意。
杜威把上述教師應有的責任,作為現代“教師職業精神”的三要素。其實也可把它視為“現代師道”的三要素。
從杜威倡導的“教師的職業精神”到在實踐中建立教師職業的價值標準與行為規范,經歷了長期探索過程。前面提到的全美教育協會1975年厘定的《教師專業倫理典章》(見表2),堪稱現代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的雛形。
在這個文本中,“導言”為教師應有的價值觀念,即教師的倫理價值標準。相當于“師道”;“典章I”的小序,為教師應有的學生觀念(屬“師道”),“教師對學生的義務”,為教師對待學生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屬“師德規范”,基本上為戒律);“典章Ⅱ”的小序,為教師應有的職業—專業觀念(屬“師道”),“教師對教育專業的義務”,為教師對教師職業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屬“師德規范”)。從而形成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的雛形。

在此典章的序言中,宣稱“教師無不認為其責任蘊涵在教學過程之中”。即認定教師的本職為教學。主要在教學過程中教育學生,以本職工作盡社會義務。這是由于在現代社會中,已經形成發達的社會教育系統及其他公共服務事業。教師參與學校以外的公共事業或公益活動,屬于個人自愿的事情。教師組織不宜就此對其成員作出強制性的規定。
五
綜上所述,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的形成,經歷了長期摸索過程,才算有了一些頭緒。如果以史為鑒,從中便不難看出我國在建構教師倫理價值—規范歷程中有待解決的問題。
單從表面現象看來,我國古代主要關注“師道”,當時關注師道,是由于普遍忽視師道,如今通行“師德”,以致迄今尚未萌發構建包括師道、師德在內的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的念頭,這且不談。真正的問題或許倒在于我們所謂的“師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國,“師德”是教師教育中的必修課。可惜本人以往沒有機會修習這種課程。也就不知道這門課程的老師究竟講些什么,更不了解這種課程起了什么作用。好在從我國教育行政當局會同教育工會于1997年修訂的《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見表3)中可以知道一些線索。
這個文件所列“師德規范”,共8條43款。實際上是8類43條規范。按理作為普通教師,只能把明文規定的道德規范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嚴格遵循,不得說三道四。好在近據報載,教育主管當局正在就進一步修訂這個文本征求意見,也就不妨說一些看法。
1.這個稱之為“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文本中的條款,雖然條條都對,問題在于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為“道德的”規范,調節教師的職業行為。
道德,據《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版)解釋,其含義為“以善惡評價為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的力量,來調整人們相互關系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的總和”。依照這種解釋,只有符合公認的善惡標準的規范,才稱得上“道德的”規范。違背這種規范的行為,才可能受到社會輿論或個人良心的譴責。那么這究竟是怎樣的道德規范呢?一般說來,主要是針對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失德”行為的規范。即以戒律表示的規范。它屬于道德的底線。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從前述18世紀學校規程到20世紀全美教育協會《教育專業倫理典章》的教師道德規范,大都屬于戒律。這些規范對所禁止的行為的表述,都比較具體,并不含糊,以防止規避這種戒律。而在我國現行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中,只有5條戒律,占規范總數(43條)的11.6%。

惟其如此,近年來我國教師中發生的一些突出的涉德事件,如尹健庭解聘事件、“范跑跑事件”“楊不管事件”等,當事人都曾受到公眾輿論的譴責,而一旦對當事人作出嚴格處理,當事人反而受到輿論同情,或許同我國師德規范較為含糊不無關系。
2.以上是就習俗道德意義上的師德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的師德是歷史地形成的。它是所有教師都不可違背、多數教師不致違背的行為準則。惟其如此,觸犯這種戒律的行為才可能受到公眾輿論與個人良心的譴責。然而,這種習俗意義上的行為準則,畢竟只是師德的底線。隨著時代變遷、社會進步,局限于習俗道德,也就不足以反映社會對教師的普遍要求和變化了的教育狀況,故在不同社會—文化中,又提倡反映該社會—文化中核心價值的倫理道德與教育價值取向,相應地提倡教師倫理道德。
倫理道德與習俗道德的區別,在于它是提倡的行為準則。主要訴諸人們的信仰,尤其是訴諸理性。所以它首先是先進分子的行為準則。倫理道德的規范一旦成為人們普遍認同和習慣了的行為準則,它便成為較高水平的習俗道德。
隱含在教師倫理中的價值觀念,可視為現代意義的“師道”。小原國芳正是把“師道”作為教師價值追求的東方文化的表達。杜威所提倡的“教師的職業精神”,用東方簡明的語言表達,便是現代的“師道”。這種“師道”,正是“教師倫理道德”的精義所在。
我國現行“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中,除少數戒律外,多數規范都屬于(或近于)倫理道德。如把它同全美教育協會《教師專業倫理典章》對照,那就不難發現,由于我國長期囿于“師德”視野,又忽視“習俗道德”與“倫理道德”之分、“師德”與“師道”之分、“道德規范”與“行政規范”(紀律)之分,尚未形成構建教師倫理價值—規范體系的自覺,故所列教師道德規范不得要領。
注釋:
[1]蕭承慎.師道征故[M].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06:3.
[2][3]克伯雷.外國教育史料[C].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313-315、516-517.
[4][5][6][7][8][9]小原國芳教育論著選(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64-365、323、324、325、326、340.
[10]王承緒,趙端英.鄭曉滄教育論著選[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29.
[11][12][13]袁剛,等.杜威在華演講集[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568、569、570.
[14]斯特賴克,等.教學倫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1-2.
[15]教育部政策研究與法制建設司.現行教育法規與政策選編[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209.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
(責任編輯:王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