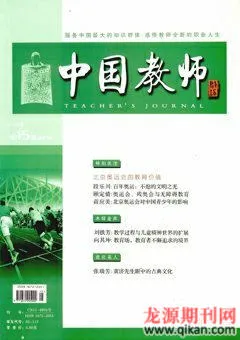黃濟先生眼中的古典文化
黃濟,原名于鴻德,我國著名老一輩教育學者,新中國教育哲學學科的主要奠基人。1921年7月20日生,山東即墨人。北平師范學院肄業。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員,北京師范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教育學研究會第二屆副理事長。
引言:黃濟先生與《中國教師》的《古典文化專欄》
2005年秋,《中國教師》意欲開辟一些增強人文性的欄目,主編勞凱聲老師向黃濟先生約稿,先生欣然應允。
我們原欲請先生將其舊作《詩詞學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部分內容修改并重新編輯后刊發,但先生并未走此“捷徑”。在答應撰稿之后,先生開始認真準備。2006年2月25日,先生提交了一份《古典詩文選讀》的提綱,并請“凱聲同志指正”。先生時年85歲,《中國教師》主編勞凱聲是他的學生、晚輩,但先生極盡謙和,這是他嚴謹學術態度的體現,是對《中國教師》廣大讀者的認真負責。先生的這種嚴謹、認真、謙和的態度在接下來的兩年里《中國教師》的編輯感受至深。
經過幾次溝通,《中國教師》于2006年第5期(總第24期)開辟《古典文化專欄》刊登先生撰寫的古典詩文選介,至2008年第15期(總第68期)刊登完畢,共27期,用時兩年多。
兩年多來,先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把親手寫好的稿件親自送到編輯部,在我們錄入之后再進行仔細校對。[1]而且,先生幾乎每次都要與我們討論稿件的內容,但討論又不限于稿件內容本身。先生給我們講解《三字經》《周易》《紅樓夢》,也和我們談“于丹現象”、“紅樓選秀”、“尊孔祭孔”,等等。更讓我們感動的是,每次先生離開時,總是會說:“要是別人給我提了什么意見,你們告訴我。”有時候他忘了講,還會返身回來叮囑我們。
兩年的時間也許不長,《古典文化專欄》的內容也不是宏篇巨著,但先生卻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僅僅是所選用的內容,都需要先生一條條地翻閱資料,確認出處。而先生既沒有助手,也沒有借助于網絡等工具,用先生的話來說,“(我)是刻苦的”。
更令人佩服的是,如今先生在《中國教師》所刊文章的基礎上正在撰寫《國學十講》。雖然早前先生流露過他的這一想法,但是收到先生已經完成的《國學十講》的前言與第一講的內容時,我還是一驚,畢竟先生已經87歲高齡。
2008年6月18日,我來到黃濟先生的家里,再次聆聽先生對于《古典文化專欄》以及古典文化的人生感悟。以下內容根據黃濟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
我要感謝《中國教師》雜志,專欄的設置給了我一個重新學習和應用古典詩文的機會、一個服務社會的機會。
我讀了八九年的私塾,有一定的國學基礎,但自我認為是很淺的。這一次我系統地走了一遍我們國家的古典文化知識,兩年的時間,我覺得我學了很多的東西。過去學過的,這一次我又認真地學習了一遍,有些過去我沒學過的東西,比如說《易經》,這一次我也補上了這一塊兒。這為我寫《國學十講》打下了一個基礎。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一、關于《古典文化專欄》
關于這個專欄,我再談幾點自己的看法。這個欄目開設兩年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從幾個方面講一講。
1.從欄目的內容上來看,擴寬了古典詩文的范圍
過去詩文都有專門的“選”。“詩”有《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文”有《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文選》等。這次我們將古文和詩詞統一在了一起。而且從時間上講,我們將上限延伸到諸經和諸子,下限延伸到小說與雜劇以及楹聯和謎語,主要是想擴大讀者的知識領域。
過去文選都很少涉及諸經和諸子,一般選文是從《左傳》開始的,主要內容是唐宋以后的。而下限一般到明清就沒有了,清代的內容都很少。這次我們照顧到經史子集的不同方面,解決過去文集不選經、子的問題。我們還增加了《讀史》一講,講了《史記》《資治通鑒》。此外,我們還選了小說、雜劇。因為我覺得這些內容在今天的影響還是很大的。比如,現在昆曲很受重視,昆曲就是由雜劇而來的。
2.從撰寫的態度上來講,有繼承,也有批判分析
這恐怕是我一直所堅持的,在繼承的同時要有分析。別人說我“自以為非”,而不是“自以為是”,我確實感覺我還是很“自以為非”的。我常常是來回顧自己的。我讓你們給我提意見,我不是客氣,誰的意見我都可以聽。但不是誰的意見我都要接受,我會分析的,要經過我的思想,我接受了,然后才會來轉變自己。但是對于別人的意見我是不會拒絕的,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的。
我沒什么學歷,就是大學二年級肄業,沒有學士學位,但我是博導(博士生導師),而且還拿到了“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導師的獎。為什么我能夠承擔這個任務,我覺得我是刻苦的,到現在我也沒有閑著,而且我有批判分析精神。
我選這些內容是有分析的。比如,現在一講“中庸”,就是好得不得了的東西了。但是我自己要寫個東西,我還是要按我自己的觀點來寫的。這一點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就是私塾后期的三二年時間里的那個老師。
我的老師是個秀才,他給我們上課就是采取批判態度的。他是個老秀才,有很多的古東西,但是他不迷信、不盲從,而且還會改造。他把五言律詩改成四言,很有意思的。當時我們講藺相如完璧歸趙,一般都是歌頌藺相如的,但是我們的老師是批判的。他認為藺相如的這一行為給他的國家帶來災難,他做的是反面文章。我的老師具有批判精神,和他的個人經歷有關,他給我的影響是很深的。
3.從選取篇目上看,力求做到典型性、思想性、藝術性和科學性
選材要從典型性、思想性、藝術性和科學性幾個方面來全面考慮。可能不是每一篇都具備這幾個條件,但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個條件。比如,李清照后期的詞,主要寫家庭生活的,思想性較少,主要是考慮到它的藝術性,畢竟是婉約派的代表。
此外呢,還要講到科學性。主要是指我們的選讀、分析力求要科學注釋,不要有“硬傷”。比如,把“唯女子與小人”的“小人”講成是“小孩”,這就是硬傷了。對于經典,當然有“我注六經,六經注我”,個人有個人的見解,但是個人見解不是隨便的注解。又如,《三字經》中“我教子,唯一經”,把這個“一經”理解成“一本三字經”,這恐怕就是錯誤的了。
4.存在的問題
雖然上面我講了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覺得這個內容還存在很多問題。總的來說,我們所涉及的范圍太大。范圍太大就使得有些地方講得不深不透。所以我希望在《國學十講》的時候盡量地講得深透些。
這兩年來寫這個東西,很苦、很累,但是苦中有樂。學到東西、發現新問題,是很高興的,但是有很多東西,以前并不是很熟,要重新學習,就很累。我覺得現在這個內容在專業的人員看來,顯淺,如果是一般的讀者看來,又顯得深。我用“上不著天、下不入地”來概括。我想在《國學十講》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國學十講》我要加強學術性,當然也要照顧到讀者的閱讀。此外,《國學十講》還要補充一些這次遺漏了的問題。比如《讀史》部分,我們沒有談《紀事本末》。紀事本末體,不同于編年體以紀年為主,也不同于紀傳體以傳人為主,而是以故事為主,把歷史上的大事,詳其首尾,集中表述其過程。在《國學十講》中,我打算把這部分的內容補充進來。同時,還要加入一些少數民族的史,我想這對民族的團結是有好處的。
二、談國學熱
對于古典文化來說,一方面我們這個專欄要宣揚一些東西,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分析,我們不是把學國學變成一個盲從的事情。我寫這個東西,一直堅持有繼承,也要有分析、批判,希望使“國學熱”有個度,不至于到“發燒”的地步。
對于國學熱呢,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我現在也還在買一些這方面的書。但是熱呢,絕不能“發高燒”的。現在的國學熱就缺乏“分析”,這里面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國學不是萬能的。
另外,對于國學的態度要慎重。拿修訂《三字經》來說,不否認修訂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我覺得沒必要修訂,而且也修訂不了。比如說,“養不教,父之過”,這一次有人提出要修訂為“養不教,父母過”。實際上,“父之過”有時代意義,在當時就是這個意思,當時就是“嚴父慈母”,母親一般是沒有知識的,教育的責任就是父親的。雖然也出過幾個母親,孟母、岳母,但是,這都是在孩子的父親不在的時候。當時更多的教育責任是父親的,“父之過”,是強調“父權”的,這是時代的特征,改變了就不一樣了。而真正需要修訂的,比如,“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卻沒有太多的人注意。[2]
此外,國學不能盲從,更不能搞形式主義,現在這個問題也很嚴重。特別是學古文化的就要穿大褂,這是沒必要的。大褂是清代的,也不是孔子穿的,你穿大褂在孔子看來,和穿西服是一樣的。所以,學國學但不要復古。我很反感這些。還有,孩子的成年禮要在孔子面前磕頭,這是不行的。孔子再偉大也不用你在他面前磕頭。
我的第一個頭是給孔子磕的,我6歲的時候,父親把我送進了私塾,就給孔子磕頭了。我是尊敬孔子的,過去“批孔”的時候,我的思想上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我并不盲從于孔子。孔子毫無疑問是偉大的,但并不是每句話都是對的,這是有時代特征的。當時可能是對的,但現在不一定能用,有些內容那個時候是有利于文化的發展的,但現在卻不一定也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此外,孔子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被承認,貶低和過多的批判也沒有必要。
所以我覺得,繼承的時候一定要分析,批判,這是我一直堅持的態度。對于古典文化或者說國學我們一定要全面、要實際、要實事求是、要古為今用。
在采訪中,黃濟先生一直惦念他的《國學十講》,他說:“如果能完成了,我就能夠老有所為,再作出一點貢獻。”而先生的書房中滿滿的是他做了標記的書籍。《中國教師》很有幸約請到黃濟先生兩年多來一直為我們撰稿,我們祝愿先生的《國學十講》早日完成,盡快與廣大讀者見面。
注釋:
[1]因2006年5月開始,黃濟先生負責中國教育學會“十一五”重點課題——“中國傳統文化與青少年素質教育研究”,《中國教師》古典文化專欄刊登的內容為課題成果之一,所以黃先生的部分手稿由《中國教育學刊》完成錄入。
[2]黃濟先生認為,為了保證知識的完整性與客觀性,此句可修改為“諸子者,有老莊。有墨荀,有韓揚。”
(責任編輯:朱珊)
災后青少年“課后睡前”心理援助熱線開通
課后睡前是災后青少年尋求心理援助的黃金時段。為了幫助災區青少年撫平心理創傷,重建心靈家園,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開通災后青少年“課后睡前”心理援助熱線。心理援助熱線于2008年6月6日——12月31日提供電話咨詢服務,熱線號碼010-68438711。該熱線面向全國受地震等災害影響的青少年,周一到周五服務時間為17:00~21:00,周六和周日服務時間為9:00~21:00。
專家組名單
孫云曉: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王艷:北京科技大學心理咨詢與發展中心心理咨詢師
王晶晶:北京理工大學心理咨詢師、心理學碩士
鄧麗芳: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所副所長、應用心理學博士
葉冬梅:中央音樂學院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
孫宏艷: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朱松: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心理學碩士
劉秀英:《少年兒童研究》雜志社社長、副編審、教育學碩士
張小菊: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心理發展中心副主任、心理學碩士
李梅:北京建筑工程學院心理素質中心教師、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首都醫科大學精神衛生專業碩士
張黎黎: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
李楊: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
官銳園:北京大學醫學部學生心理咨詢中心副主任
房超:北京科技大學心理咨詢與發展中心主任
趙霞: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心理學博士生
高翔: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博士、心理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