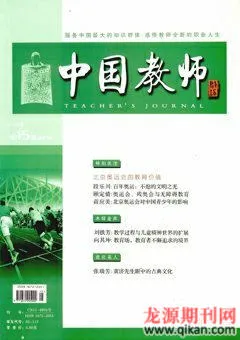“語文味”:愿你再濃香一些
語文課的內涵到底是什么?高質量的語文課究竟是什么樣子?這個答案可能很復雜,但“語文味”應該是最基本的尺碼。為什么有人說當今有些語文課不是語文課,而是思品課、歷史課、音樂課?為什么有人竟說有的語文教師不會教語文?一個主要原因是語文教師對“語文味”的認識還不夠,還不明白怎樣在一堂課上盡可能多地“煮”出語文的濃香。本文僅舉幾例,以試圖解說偏淡的“語文味”是什么樣子。
一位教師教學寓言故事《白兔與月亮》,設計了兩個問題:①這則寓言的寓意是什么?②讀了這則寓言后你有什么收獲?由于寓言故事簡單,寓意淺顯,學生在短短5分鐘內就徹底弄清楚了這兩個問題,但教師還是不厭其煩地讓學生反復談對寓言的感受。這是地道的語文課嗎?應該說更像思想品德課,因為這位教師把一堂語文課的教學目標僅僅定位在“情感態度價值觀”上。本來,教師要借這兩個問題來指導學生讀課文是不錯的設想,但在引導學生理解這兩個問題時必須要充分地關注另兩個維度的目標,在達成另兩個維度目標的基礎上使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理解中心思想”要做,但那不是語文課的根本目的,思想品德、歷史、生物等課程都有“歸納中心”這類相似的環節,都有“理解中心思想”的變異形式。這堂課的“語文味”肯定嚴重不足,是典型的以人文素養代替語文素養。一位教師說:“語文教學就是要從一個個標點、一個個詞語、一個個句子開始構建或更新言語世界,與此同時構建或更新學生的人文世界。”朱自清在《文心序》里講:“讀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匯的擴展,字句的修飾……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為思想也就存在于語匯、字句、篇章、聲調里;中學生讀書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里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匯等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
教學《白兔與月亮》,引導學生感悟這則寓言的內涵并受到啟迪是一定要做的,但更應該做的是對學生進行言語技能訓練。教師不妨設計三個問題:①憑什么說白兔的賞月之才舉世無雙?②白兔無窮的得失之患表現在哪些方面?③白兔的心情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變化?學生要回答這三個問題,就必須尋著文中的優美詞句,特別是文中那些表現白兔心理變化的詞句去品味它們的內涵及表達效果。在品味和賞析中感受語言的魅力,得到語言的熏陶。
語文課把思維能力訓練作為語文能力訓練的重點。一位教師教學《晏子使楚》,在師生疏通文意后,教師問學生“晏子憑什么說得楚國君臣啞口無言”,學生一番討論,教師拋出了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推理,并引導學生理解“三段論”這種推理方式的構成及作用。接著,教師又投影了兩個“三段論”的推理題,請學生根據前后文補出“大前提”或“小前提”。在教師的幫助下,學生做得非常好。到此,教師仍不罷休,還讓學生自己編一個“三段論”的推理句子。這樣,一節課就差不多了。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是語文課的專門任務嗎?從某種程度講,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程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還強于語文。把《晏子使楚》的教學目標定為訓練思維能力,特別是“三段論”這類形式邏輯的推理能力,恰當嗎?
就《晏子使楚》而言,更應該細細品味的是晏子在與楚國君臣對話中所表現出的神態、心理、動作、語言,藉此去感悟晏子的機智和聰穎。雖然文中并沒有直接寫晏子的神態、心理、動作,但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角色對話等方式,經過學生的創造性閱讀,鮮活的晏子一定會站在我們的面前。而該教師整堂課根本沒有引導學生學習語言并進行語言訓練,“語文味”明顯不足。葉圣陶說:“在講解的時候,一定要靠講明語言的運用和作者的思路——思維的發展來講內容。要知道為什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為什么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為什么用這種口氣而不用那種口氣,所有這些都跟文章表達的內容密切相關。不能把兩者分開來講,這一堂講思想內容,另一堂專門講語言;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這堂課才算成功。”
語文課把抓準景物(事物)的特點作為閱讀教學的根本任務。在語文教學中,面對一些寫景寫物的文章,教師引導學生抓準景物(事物)的特點,是必須要做的。但有的教師在反復引導學生抓準了景物(事物)的特點之后,就此打住了,導致“語文味”根本出不來。我曾聽一位教師就《濟南的冬天》上公開課,教師先引導學生整體感知了濟南冬天的“天氣”“地勢”“山”“水”四個方面的內容。然后教師問:“濟南冬天的四個方面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嗎?”學生分組討論后指出了濟南冬天的獨特之處:“天氣溫晴”、“地勢慈祥”、“小山秀氣”“池水清亮”。應該講,教師的思路非常明晰,順此下去課堂非常精彩。可教師接下去話鋒一轉:“作者是怎樣把文章寫得如此生動的”,很明顯,教師已轉到分析文章的寫作手法了。試問:“如此生動”從何說起?教師引導學生賞析“如此生動”了嗎?
作為一篇寫景散文,教師引導學生分析景物的特點是正確的,讓學生反復討論,以求抓準景物(事物)的特點,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教師要指導學生欣賞散文所描之美景,涵詠散文所繪之意境,從而披文入情。而該教師恰恰忽略了“披文入情”這個最重要的環節,比如,濟南冬天雪后的小山是“秀氣”之美,那作者為了突出小山的“秀氣”之美,是通過哪些詞語、句子、修辭、寫法來達到的?這樣的“披文入情”過程,就是引導學生品味詞語和句子、探究修辭和寫法的過程,也是引導學生欣賞美、品味美、鑒別美的過程,而“語文味”的濃香恰恰就在這里。
語文課把概括文段段意作為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重要方法。新課標推行七年來,語文課堂上那種逐段概括段意的做法已很少見了,但換一種方式歸納段意的做法并不少。有的教師把語文教學等同于讓學生讀懂文段的意思,以為只要讀懂了文段就是培養了學生的閱讀能力。假如是這樣,在思品、歷史、生物等課堂上,教師都在問“這段講的是什么”或“這段告訴了我們什么”,那語文課與它們的區別在哪里呢?
一位教師教學朱自清的《春》,在教師范讀、學生齊讀和朗誦之后,教師問“朱自清用他的生花妙筆給我們描繪了哪些美好的畫面呢”,師生討論后明確:“春草圖”、“春花圖”、“春風圖”、“春雨圖”、“迎春圖”。之后,教師又問“課文第一段寫的是什么呢”,學生回答是“盼春”。教師接著又問“那第二段是不是寫的‘盼春’呢”,學生回答“不是,是對春天的總寫”。學生剛回答完,教師又追問“那最后三段又分別寫了些什么呢”。這不是換著花樣問段意又是干什么?教學一篇文章,干嘛非要想方設法把課文每個段落的段意問個遍呢!更令人深思的是,這位教師引導學生欣賞這幾幅畫面的做法。比如,在指導學生欣賞“春草圖”時,教師問“春草圖里寫了些什么呀”,學生七嘴八舌討論后說“有小草、園子、人、風”,教師問“這段用了哪些修辭手法呢”,學生回答“擬人、排比”。以下四幅圖畫全是這種做法,一篇美文被教得索然寡味,味同嚼蠟。散文傳神的景物,優美的意境,抒情的語言,濃烈的情感,教師未作任何引導,學生一點美文的味道都沒有嘗到。
語文課把揪準人物性格作為培養學生鑒賞能力的標志。對于寫人類的文章,引導學生分析并揪準人物性格是教學的必要環節,是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歸納概括能力的重要步驟,是理解文章內涵和作者意圖的一個重要抓手。但是,揪準人物性格是為了什么,揪準人物性格這個過程可以產生哪些附加值,往往是一些教師容易忽略的。
一位教師教學魯迅的《故鄉》,先讓學生在熟悉課文的基礎上復述故事情節,然后就讓學生歸納閏土、楊二嫂、“我”的性格特點,學生討論歸納后,教師再讓學生回答“作者描寫刻畫人物用了哪些方法”,而學生只是籠統地指出了語言、動作、外貌、心理、細節等描寫方法。之后,教師就轉入了對小說環境描寫的分析。很顯然,教師已陷入了“只圖揪準人物性格”的怪圈,把揪準了人物性格作為根本目的。實際上,閏土、楊二嫂都是非常傳神的人物,教師只有引導學生走進文本,走進作者,抓準那些描寫人物的詞語句子,咀嚼這些詞語句子所飽含的豐富情感,賦予這些詞語句子以生命,讓學生頭腦中的閏土、楊二嫂有血有肉地站立起來,讓學生與自己心中的閏土、楊二嫂息息相通,互相感染,才能理解作者塑造人物的美學價值,從而受到情感的熏陶。如果僅為了揪準人物性格,大有抓了芝麻而丟西瓜之嫌。“揪準人物性格”是目的,但不是根本目的。以“揪準人物性格”為平臺,通過品析傳神的人物描寫,領悟語言運用的精妙,“激活”文中的人物,走進人物豐富的精神世界,才是“揪準人物性格”的要旨。
說到這里,我們是否可以說有“濃香”語文味的語文課至少應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必須有最基本的語文教學“點”,諸如:字詞句教學、修辭教學、情感感悟體驗、語言咀嚼品味、文章寫法借鑒,以及聽、說、讀、寫、思(思維)、想(想象)等等;這些“點”須是語文課關注的重點,整堂課必須圍繞這些方面有所側重地去開展教學活動。二是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和能力,在語文課堂上更多地從語言運用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交際能力、審美鑒賞能力、運用工具書的能力等方面去設計自己的課堂教學內容,多從“語”“言”兩個角度去設計自己課堂教學的每一個環節。三是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語文教學過程,從而使之得到情感體驗和能力訓練,學生在積極主動參與過程中,在教師的引導下,利用自己已有的語文認知結構去分析解決學習中的語文問題,而不是非語文問題;把理解中心思想、訓練思維能力、抓準景物特點、概括文段意思、揪準人物性格作為達成學生語文素養和語文能力的過程和途徑,而不是最終目的。
當然,教師如何使自己的語文課飄出芳香的“語文味”,如何恰如其分地做到工具性與人文性的完美統一,如何避免耕了人家的田而荒了自己的地,可以說是很難用量來表述的,關鍵的問題是教師自己要明白什么是“語文味”,怎樣“煮”出“濃香”的“語文味”。
(作者單位:重慶市涪陵區第十四中學)
(責任編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