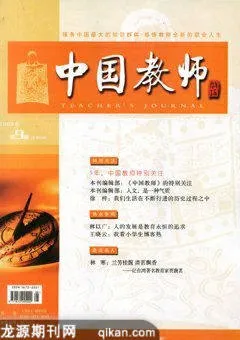“文學不死”的基本原理
“文學死了”,這是近年文壇的炸彈式命題,也是已經過去的2007年文壇的關鍵詞之一。網上查閱“文學死了”,居然有1114000條之多。初聞此言,讓我這個以教授文學謀生的人莫名驚慌。文學死了,那大學還辦什么中文系、文學院?以教授文學養(yǎng)家糊口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統(tǒng)統(tǒng)都得下崗待業(yè)。出于“失業(yè)”的恐懼,于是趕快找出有關論述“文學死了”的宏文細細拜讀。這一讀,先是釋然,繼而安然,最后是坦然——“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之坦然。因為我在拜讀這些宏文的字里行間讀出了門道——原來這是舶來品。
所謂“文學死了”,具體地說是“文學的終結”“小說的終結”“詩歌的終結”“經典的終結”“批評的終結”,此并非中國本土原創(chuàng),而是從域外販運而來,確切地說是近年西方學者米勒?德里達等人所持的一家之說。苦于找不到“創(chuàng)新”語題的本土文論家,于是欣喜若狂,趕快把它搬來,如此這般,這般如此,一經登陸中國文壇,自然吸人眼球,產生炸彈效應,一下子激活了僵硬的文論,而論者也由此揚了名。中國文論界向來以制造話題為能事,一忽兒這個主義,一忽兒那個話語,不說遠的,光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多得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正所謂你方唱罷我登場,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如今又出來一個“終結論”,公說公理,婆說婆理,文論界于是變得熱鬧起來,同時又順便發(fā)表了“科研成果”,豈非一舉兩得。但恕我直言,所謂“文學死了”,就像以往許多轟動一時的時髦批評一樣,這不過是又一次“偽命題”的誕生,與真正的文學批評無關。
拜讀標榜“文學死了”的宏文,使我最感釋然、安然、坦然的是,我在這些宏文的字里行間,看到的“文學死了”乃是指“成人文學死了”而已。原來,凡是所有驚呼“文學死了”的論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眼中所謂的“文學”,其實只是文學的一半,就如同身體的一半,而非文學之全身。
稍具文學常識者都知道,文學是一種精神產品,既是產品,就有其接受者即消費者。按照文學產品主體接受對象、消費對象的不同,人類將服務服從于成年人的文學稱之“成人文學”,與之相對應,在人類文學大系統(tǒng)中還有另一類服務服從于18歲以下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文學”。就在文壇驚呼“文學死了”的這些年,另一種類型的文學卻在蓬蓬勃勃地生長著、繁榮著,這就是未成年人文學。它包括兩大類:一類是“未成年人自己寫的文學”,如郭敬明、韓寒、張悅然、春樹,等等,他們的作品動輒就是十萬、數十萬冊的發(fā)行量。有好事者根據發(fā)行量的版稅率,計算出了當今作家的富豪排行榜,郭敬明等都名列前茅。另一類是“寫給未成年人看的文學”,也就是兒童文學。這方面的作家作品更是風起云涌,鋪天蓋地。最“狂”者,國外要數英國女作家J?K?羅琳,她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發(fā)行量已直追《圣經》,全世界不同膚色、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億萬青少年都因《哈利?波特》而“我為書狂”。在國內,最“狂”者當數成都女作家楊紅櫻,她的《淘氣包馬小跳系列》《笑貓日記系列》等的發(fā)行量已超過2000萬冊,而且還被西方出版業(yè)買走了全球全語種版權,楊紅櫻已成為中國當代作家版權出口第一人。中國人從來只知道世界兒童文學大師安徒生、格林兄弟,甚至誤認為中國兒童文學的“起源”是從西方引進的。如今楊紅櫻筆下的“馬小跳”“笑貓”已大舉挺進歐美主流社會,這實在是大長了中國文學的志氣,大大地為中國文學爭了光。
但是,且慢,那些瞧不起“未成年人文學”的理論家卻在那里嘀咕:《哈利?波特》《淘氣包馬小跳系列》,還有什么郭敬明之類寫的東西,那也是文學嗎?怎么會不是文學呢!據報導,2007年7月下旬,來自世界各地的1500余位專家教授,齊聚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喜來登中心,舉行了為期4天的全球《哈利?波特》學術研討會,對《哈利?波特》這部新世紀幻想小說進行了多角度的研討。遺憾的是,中國文論界對《哈利?波特》一直三緘其口,甚至還在懷疑是不是“文學”!因而無人參加。至于楊紅櫻的作品,在國內已獲得多種文學獎項,包括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海峽兩岸共同舉辦的文學獎等,因而早已驗證楊紅櫻的作品屬于文學。郭敬明、韓寒、張悅然等“80后”寫的東西自然也是文學無疑,因為已有不少文論家評論他們的文章了。
既然J?K?羅琳、楊紅櫻、郭敬明等寫的都是文學作品,既然這些作品又是如此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甚至成為超級暢銷書(至于是否成為“經典”,那是另一回事),怎么又會冒出“文學死了”的結論呢?這實在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看來答案只有一個,在那些鼓噪“文學死了”的高深理論家眼里,未成年人文學——兒童文學根本就不是文學!
如何看待未成年人——兒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文學——兒童文學?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周作人就已旗幟鮮明地發(fā)表過見解。魯迅說:“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從而“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魯迅還熱烈地贊譽葉圣陶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chuàng)作的路”。周作人說:“中國向來對于兒童,沒有正當的理解。”“不是將他當做縮小的成人,拿‘圣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么,一筆抹殺,不去理他。”“兒童同成人一樣的需要文藝”,新文學有“供給他們文藝作品的義務”。然而遺憾的是,時代已經進入了21世紀,在某些高深理論家的眼里,兒童依然沒有地位,至于為他們服務的文學自然也就不配稱作文學,于是這才有了“文學已死”的中國版。由此悟出了一個道道:凡是不把兒童當成獨立的人看待的人,就不會把兒童的文學看成是文學;反之,凡是承認兒童有其獨立價值與社會地位的人,自然而然也就會把為兒童的文學看做是文學。因此,如果要說“文學已死”,那最多只是文學的一部分——“成人文學”已死而已。兒童文學不但未死,而且還活蹦亂跳。兒童文學從來不害怕死亡,如同兒童從不畏懼死神一樣,因為兒童的生命距死亡最遙遠。兒童是生長的、發(fā)展的,世界的希望、人類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希望,全在于兒童,文學的希望也一樣。因此,只要兒童不亡,希望就不亡;只要兒童文學不亡,文學就不亡;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兒童,就會有兒童文學,就會有文學,“文學已死”的高論,可以休矣。
兒童永生,文學不死!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