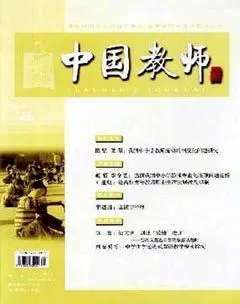孔子如何對學生進行知恥教育
中華傳統恥感文化源遠流長。孔子的思想和學說,沿承夏商周的文化大流,繼往開來,成為恥感文化的源頭活水。
在較早的經典古籍《詩》《書》《易》的一些文字中,已經體現出恥感意識。《書·說命下》把人內心對羞恥的體會與感覺形象地表達出來:“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意思是內心慚愧和羞恥,就像在街市上當眾挨鞭子一樣。《詩·蓼莪》以酒器中沒有酒為酒器之恥,比喻不能奉養父母的羞愧:“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書·說命中》把過失當作恥辱:“無恥過作非。”意思是不要覺得有錯可恥而文過飾非。而在《易·恒卦》中,已將蒙受羞恥同不能很好地保持美德聯系起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盡管在這些經典古籍中已經反映出了恥感意識,但直到孔子,對恥的認識和理解才更加自覺,使恥感文化初步形成體系。孔子特別重視對學生進行知恥教育。他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禮記·中庸》)孔子把知恥和好學、力行并列在一起,體現出知恥在修身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論語》中多次出現孔子對知恥重要性的強調以及師生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應答,這么薄薄的一本小書,“恥”字竟然出現了十六次。這足以讓我們從中領略孔子知恥教育的內容、重點和教育方法。
一、要求學生從知恥開始確立人的尊嚴和價值
孔子教育學生把知恥看成修身的起點。因為儒家認為,人類文明皆從知恥開始。人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羞恥,與禽獸有何區別?《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正如孟子解釋的,人無“羞惡之心”,就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人。知恥是人性的標志,因此,可以說知恥是一種底線倫理。不知恥就是不要臉,不要臉的人什么壞事、丑事、見不得人的事都干得出來,所以知恥十分重要。與別人相比,如能醒悟自身修養的差距,道德的缺失,并引以為恥,于是便會奮起、勵志、進取;人若喪失羞恥之心,則會陷于麻木、墮落、茍且、萎靡。既然知恥對人生十分重要,確立人的尊嚴與價值,必須從知恥開始,進而提升精神境界,追求理想人格。
為了保持人格尊嚴,孔子要求竭力避免恥辱。如何避免恥辱呢?他教給學生的辦法是:“恭近于禮,遠恥辱也。”(《論語·學而》)恭敬待人,可以遠離恥辱。遭遇恥辱,損害人格尊嚴,可謂人生之不幸,特別是奇恥大辱更令人難以忍受。孔子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禮記·儒行》)寧可被殺頭,也不蒙受恥辱,實現這種道德踐履,需要極大的勇氣,所以知恥為勇。孔子樹立的這種道德人格,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
學生們完成學業后都是要做事的,孔子又教育學生,無論做什么事,特別是那些需要承擔重任的,要時刻對自己的不當行為保持羞恥之心。子貢問老師:“怎樣做才可以稱得上士?”因為子貢口才好,能言善辯,長于辭令,是搞外交的好材料,老師就以出使外國為喻來回答這個問題:“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意思是維護國家尊嚴,光靠能說會道不行,首先要有廉恥之心,用堅定的操守約束自己的行為,才有可能不使君命受辱。士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其角色是大道的承擔者。孔子是這一傳統認識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他在這里強調的是,承擔天下重任的人,必須做到“行己有恥”。
二、教化民眾知恥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的思想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以仁為實質內容、以禮為制約形式的德治社會。這種理想社會的建立和維持,主要依靠的是賢德之人和道德榜樣,而不是靠刑律和嚴苛的處罰進行統治。所以,孔子向學生灌輸這樣的思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思是用行政命令來統治民眾,用刑法約束他們,這樣民眾雖然能暫時避免犯罪,但并不知道犯罪是可恥的;如果用德引領民眾,用禮來約束他們,這樣,民眾就會知道羞恥,心悅誠服,并進一步革除自身可恥可羞的行為。
孔子理想中的社會是一種和諧社會。建設這樣的社會,依靠政令和刑律雖然有成效,但其作用是有局限的,因為這種治理方法不過是用外在的強制力量,起到震懾作用,老百姓害怕了,收斂一下,暫時不去犯罪罷了。社會的這種和諧是表面的、不穩固的,建設和諧和穩固的社會單靠強制是難以實現的。只有對民眾進行教化,使他們知道什么叫羞恥,一心想著趨榮避恥,去惡為善,從而自覺地遵從道德原則和社會規范,才能使社會實現穩固的和諧。
孔子向學生灌輸這種思想,目的是為他們日后出仕從政,建設儒家理想的社會,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子游在武城做官,就是按老師的教誨,著重對民眾進行禮樂教化。有一次孔子來到武城,聽見弦歌之聲,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莞爾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論語·陽貨》)孔子詼諧幽默,和學生開了一個玩笑,這正是對學生學以致用而發自內心的表揚和肯定。
三、對學生強調知恥才能勇于承擔社會責任
孔子對“義”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義者,宜也。”(《禮記·中庸》)“宜”即應該做的、符合道義的事。通過“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而“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孔子要求士人勇于承擔起社會責任。那么,見義勇為的初始動力由何而來?孟子的解釋是:“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人之所以勇于行義,由羞惡之心而來。
孔子要求學生勤奮好學,堅定信念,矢志于道:“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在國家和社會迫切需要有為之士施展才能,做出貢獻的時候,卻以種種借口放棄這種責任,見義不為,就是莫大的恥辱。孔子要求學生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是否知恥不僅關系到個人品行和人格,而且關系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興衰。龔自珍說過一句很有影響的話,那就是:“士皆知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明良論》)
另一方面,政治黑暗,難以施展抱負的時候,孔子教育學生應做出不與世沉浮、同流合污的選擇,避免蒙受恥辱。學生原憲向老師請教關于恥辱的問題,孔子回答:“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孔子的意思是:“國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拿俸祿;相反,國家政治黑暗,俸祿照拿不誤,這就是恥辱。”孔子的話對原憲形成了烙印性的影響,原憲對于孔子的教誨終生恪守。孔子去世以后,他感到天下無道,便隱退山野,過著清貧的日子,堅守節操,不與當政者為伍。孟子繼承和發揮了孔子這一道德思想,概括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這一仕進原則,一直被后世知識分子奉為圭臬。
四、在知恥教育中對學生進行的具體行為指導
孔子對學生的知恥教育,不停留在空洞的說教上,而是輔以具體的行為指導。他首先要求學生善于區分什么恥、什么不恥。人都是要臉面的,但看你要什么樣的臉面。比如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求教不算恥,像孔文子那樣“不恥下問”反倒值得贊揚。孔子認為,不同的人,恥感的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平常人更多地在細節上考慮榮恥,而對志士仁人的要求則不然,不誠實守信才是士的最大恥辱。在《論語》中,孔子多次強調了這個問題。如:“君子恥其言過其行。”(《論語·憲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意思是古人不輕易把話說出口,因為他們以說到做不到為可恥。又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這說的是:“花言巧語,偽裝和顏悅色,低三下四過分謙恭的人以及表面上裝出友好的樣子,卻把怨恨藏在心里的人,左丘明以為可恥,我孔丘也以為可恥。”
孔子又對學生強調對恥的自我體驗,從而發揮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學生中有人因貧窮而自卑,以穿粗衣、吃糙食為恥,于是孔子提醒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孔子特別觀察了子路的行為,表揚他說:“衣敝缊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論語·子罕》)意思是“穿著破舊的棉袍和穿著華貴皮袍的人站在一起高談闊論,并不覺得羞恥,大概只有子路吧?這就是《詩經》上說的‘不嫉妒不貪求,有什么不好呢?’”子路受到表揚,有些得意,時不時地把這兩句詩掛在嘴上,念誦個沒完。孔子聽說了,又批評說:“是道也,何足以臧?”意思是僅僅是這樣,怎么能算最好呢!可以看出,在倫理教育中,師生展現了思想認識上的真情互動,細致入微。孔子對子路的表揚和批評,抓住了青年人的心理特點,至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人生際遇不同,貧賤困厄不足為恥,人與人相比較的應是道德境界的高低。道德自信,不隨流俗,不慕虛榮,也是一種勇氣。孔子對學生知恥教育的細節,弟子們日久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可見影響之深。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