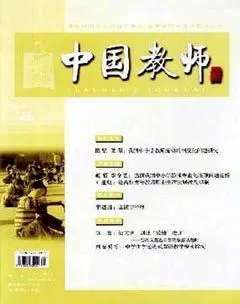重讀李澤厚
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以其《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美的歷程》等充滿智慧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說,征服了中國思想界。那個時候,處于文化與知識雙重饑渴之中的青年學子們,對于中華文化的再度輝煌心向往之卻又將信將疑,對于借國門初開(其實是半掩半開式的)一股腦涌入中國的西洋學說深信不疑卻又不知所云。李澤厚先生的學說恰如甘甜的乳汁,點燃了人們對于傳統(tǒng)文化和現代文明的想象性期待。
在那個劃時代的事件之后,年愈花甲的李先生,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那塊原來的地界兒。這一次,他走得很遠,不僅從廟堂步入田野,而且遠涉重洋,落戶于異國他鄉(xiāng)。此后,他也曾多次往來于陸、港等地,但來去匆忙,家已變成了客舍,客舍反更像是家了。此舉的象征意義耐人尋味。或許,這是默然的言說;或許,這是在距離中略帶寂寞的遠眺;又或許,這是老先生的率性而行,寧愿在漂泊中回歸永恒寧靜的家;或許有太多的或許,連老先生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
終于,《論語今讀》問世了,在兩岸三地相繼發(fā)表。這使人們眼前一亮,盡管遠不如80年代的文字效應來得光芒四射。據老先生自己說:“我之選擇做這項工作,著手于1989年秋冬,時斷時續(xù),于1994年春完成。這倒并非一時興起,偶然為之;也非客觀原因,借此躲避。實際恰恰相反。盡管我遠非鐘愛此書,但它偏偏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某種‘心魂’所在。”90年代以來的年輕的批評者們,往往以“知識者”的銳利目光自居,對老先生的“半宗教半哲學”論、“情感本體”論、“文化積淀”說、“樂感文化”說等大加撻伐。但在我看來,應該關注的恰恰是“心魂”—— 一種把個體精神安頓于中華文化大化流行之中的歲暮心境。
這種安頓,是通過與孔夫子的對話完成的。李先生著述等身,晚年卻執(zhí)意述而不作。在前言中,他這樣說:“《今讀》之所以注明為‘初稿’,并非故作謙虛,而且是我確實很想以后再多幾番修改,包括這個寫得很不順暢的‘前言’。這方面,我倒佩服古人。像朱熹,他不著意寫自己的文章、大著,卻以注好‘四書’為一生的任務,至死方休。這頗有些不現代化,但我現在寧肯更保守些……如果能使這些中華傳統(tǒng)典籍真正成為今天和今后好讀、好用的書,那比寫我自己的文章、專著,便更有價值和意義。”我敢說,老先生這里的所謂“順暢”,不只是知識的,更是精神的,是情理合一的情當理當;不只是一己的精神,也是文化的精神,是通過今日之我的注和疏,打通重重阻隔,把一己的生命融入中華文化之中,又讓文化之流浸入現代中國人的心田。這種疏通性的事業(yè)之所以比橫空出世、徒增紛擾的“個人專著”等更有價值,原因即在于此。其實,真正的“述”確比急功近利的“作”更難:它需要述之者調動自己的全部人生經驗,用整個生命去感受古人;又需要述之者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在連續(xù)不斷的對話中開啟現代中國人的文化生命之旅。
那對話,又時時充滿了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悟。我注意到,《論語》首篇的“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傳不習乎?’”中的兩個“習”字,先生皆以“實踐”釋之。論及前者,先生說:“學習‘為人’以及學習知識技能而且實踐之,當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悅之,一種有所收獲的成長快樂。”論及后者,先生說:“自己所講授所寫作的東西,認真思索過、研究過或實踐過嗎?很好的自警語,今日之‘謬種流傳,誤人子弟’,特別是言行不一,品學分離,蓋亦多矣。”重視踐履并將其納入自我成長之中,體現的也是一種“順暢”,一種打通知與行的阻隔而來的生命舒展。記得曾有論者指出:80年代的李澤厚有著一種“欲為帝王師”的心態(tài)。這話雖有些過分,但若放到時代的大氛圍(李先生就是開那時代風氣的主要學者之一)之中加以檢視,也不無幾分道理。那個時候,在“回歸五四”和“現代化”的宏大敘事籠罩之下,知識人大都關注大問題、喜用大字眼,自覺不自覺地會站在國家主體的立場上,欲熔古今中外為一爐,進而指點江山,開出一副副國家現代化的妙計良方。那方“希望的田野”,讓人們壯懷激烈,而自我卻被卷入到了集群的、有些迷狂的未來希望,自我的精神安頓似乎已被淡忘。進入90年代,本欲把追求主義落實到具體問題研究中的學術化趨勢,在學院中卻漸漸演變成又一次的乾嘉考據之風。不僅淡忘了“主義”,也疏離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