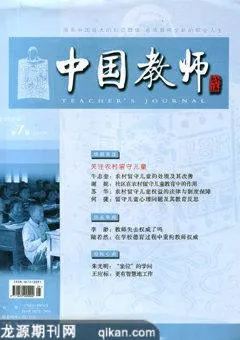寫作,行走于言語與思維之間
不可否認,當前作文教學處于一個“無序”混亂狀態。姑且不說“學生作文煩、提高效率慢”等老大難問題尚未解決,就是現在教師作文課上“教什么(內容)”都成了問題。
其實,回顧一下當前寫作教學內容的發展歷程,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寫作教學“教什么(內容)”正行走于兩個極端:由過去特別強調“怎么寫(表達)”,到現在非常重視“怎么想辦法讓你寫(思維、情感)”。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作文“公開課”(竊以為這是課改的“風向標”),教師一改傳統作文在“如何表達”上的諄諄教導,而是運用各種手段(包括使用音、像、圖、影等),想法設法對學生進行煽情啟發,以求打通學生思脈,使之能落筆成文。據說某些專家認為這是“作文教學的一大進步”。其實也是,既然我們語文教師不能“教會學生怎么寫”(其實不少教師真的不會寫作文),那么“激發學生自己去寫”總該沒問題吧。但是,如此“一大進步”的作文改革卻并沒能根除寫作的沉疴——“學生依舊怕作文”那問題究竟出在哪呢?竊以為,問題就在于我們很多語文教師自己都沒把“寫作是什么”弄明白。
“寫作是什么”,誰人知道?寫作就是“運用語言文字進行表達和交流的方式”,但這樣的表述對于“寫作教學”并無多大意義,因為它并不能幫助我們認清“寫作教學”的本質。因此,筆者倒更認同這樣的解釋——寫作是用筆說話,是和所寫文章的讀者的對話。如果說我們把“寫作”看成是“一種說話”,那么用當前時髦的話說,“寫作”就是寫者自身“言語表達”(外部言語形式)與“表達意向”(其終端即內部言語)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當我們承認“寫作是一種對話”時,其寫作者就一定會考慮與自己進行對話的對象(讀者)的客觀存在并想著如何與之對話。可以說,當我們將“寫作”與“說話”、“對話”聯系起來時,“寫作”的本質才有可能會被透視,“寫作教學”才有可能走上理性的軌道。
其實退一步而言,當前絕大多數學生都還是認可“寫作非常重要的”,但真要他寫又會覺得無“話”可說、興趣頓失。盡管原因很多,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不少教師從來就沒有從“寫作本質”上去理解“寫作教什么(內容)”,或者說,教師素來都是從自己“怎樣教”著眼,而不會想到“什么東西”才能喚起學生共鳴,使之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寫作欲望。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曾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學生既然言不由衷、無話可說,教師還要強迫寫,學生作文自然是真情缺失、沒有靈性了!鑒于此,當前教師的責任就應該是如何為學生營造一個興致勃發、情感萌動的寫作氛圍,從而將自己的思想情感暢快地表達出來,用葉圣陶先生的話說,“為學生著想,鉆進學生的心里去考慮,務必使他們有話可說”。或曰:“鼓勵學生將自己的心里話,用自己的語言一股腦地表達出來!”
好了,圈在學生腦中的“思維、情感的枷鎖”終于有望被打破——“學生有話可說了!”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有話可說”就一定能“說得出、說得好”?學生就真的能寫出文章來?實踐證明:不一定!盡管教育家贊可夫說“放手讓學生去寫,喜歡寫什么就寫什么,能寫幾句就寫幾句”的“自由創作”是何等的愜意,但是,中學語文教育下的“學生寫作”絕不等于“文學創作”,再說也不可能將學生個個培養成為“作家”,也沒那必要。可以說,那種想當然地認為學生“有話想說”就一定能寫的理想境界畢竟只是少數,否則中學語文也就沒有開設“作文課”的必要了。下面,筆者就結合一些學生日常“作品”作進一步的闡述。
1.意不稱物,辭不達意:“心有余而力不足”
毋庸置疑,這些學生都想把自己內心“想法”明白曉暢地表述出來,但事實卻不盡如人意,作者“內心意向”在轉換為“外部言語”時出現了問題:
小時摔倒留下的傷疤,但這不是我的缺憾,而是母親的音符。(將傷疤比作母親的音符,如何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意圖可能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
解放初期,就有死人愿意把眼組織捐給醫院。(人死了,還會有意愿?作者把“死人”表達成了“人死后”,其“思維意向”與“語言表達”存在落差。)
殘疾人運動會,美麗的汗水從最可愛的人身上掉下來,這是缺憾美。(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句,姑且先補出這個學生省略的內容:殘疾人在運動會的流下的汗水是美麗的,他們是最可愛的人,殘疾人是有缺憾的人,但是他們創造了佳績,創造了美。其實,這位學生如果理清思路,他可以這樣連貫地表達:殘疾人的人生是有缺憾的,但他們并沒有怨天尤人,讓遺憾伴隨終身,他們用自己的汗水揮灑征途,在殘疾人運動會上創出輝煌的成績,這樣的人不是很可愛嗎?你不覺得在他們身上散發出一種異樣的美嗎?)
2.時尚前衛,泡沫橫流:“水中之月鏡中花”
某年高考作文(話題:“感情親疏與理性判斷”)中有一篇滿分作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讓讀者捉摸不透的“語言”:“感情如水,理性如冰,八分之一的冰塊浮動在水上呈現著莊重和威嚴,一任冰下藍色的水飄蕩,不減半點高雅,這是理性的美。”說心里話,面對如此“色彩斑斕”的語言,我們讀者的思維能跟得上作者大腦“快速運轉”的思維嗎?如此漂亮時尚的“語言”怎么就成了不可逾越的交流“障礙”?再有就是當前時尚文化(例如“網絡”)盛行,學生作文語言相當“前衛”,如“霸王騎著烏騅化為鬼雄,虞姬將生命之花化作了矛尖的湛藍,于是心被感動了,”“沒有劉邦,哪來的張騫扶著駝鈴走向天山的雪蓮?沒有劉邦,哪來的衛青舞著旌旗奔向大漠的飛沙?”“給所有的事物一個旁觀的眼神,讓歷史的車輪碾過額頭,留下贊許的痕跡……”
文章乃表情達意之物,用如此語言如此敘事,看似新奇且能洋洋灑灑說開去,但筆落千言卻晦澀難懂,讓讀者有不知所云之感。難怪有人說,當前“泡沫語言”橫流于中學生作文筆端,情況相當嚴重。
3.荒誕無據,價值缺失:“誰能明白你的心”
江蘇的金光老師曾在《對另類作文應另眼相看》中記錄了這樣兩個作文語言片段。
——幾百年過去了,人民不再懷疑亞里士多德,直到20世紀中葉,英國科學家伽利略做了個震驚世界的實驗,他在幾千米的英國斜塔上,把一團紙和一團泥從同一高度同一時間放下……(啼笑皆非、滿是錯誤的文字,我們不知道是作者的確不知原委,還是他故意寫之以顯“另類”。試問,即便此例能夠恰到好處地論說作者觀點,但其荒誕過火的表述也會讓讀者覺得是在“笑話”。)
——當我被抱出產房門時,看到的是爸爸、媽媽的喜極而泣,媽媽的淚滴到我的小臉上是熱熱的……”(寫作過程中學生想象力被激發,神思飛動,縱橫馳騁,無疑是好事!但“神思”不等于“胡思”,某些無視客觀事理、人理常情的想象是令人不可思議的。)
通過以上事例及闡述,我們發現,學生在作文過程中,詞匯積累貧乏、語言運用笨拙或表達技巧不高等,往往會造成“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尷尬局面。陸機在《文賦》中也曾說:“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的確,激發學生寫作動力,使其有“噴薄欲發”的寫作沖動很重要,但這僅是寫作的“第一步”(有話可說),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作者如何將內心的“欲望、意圖”表述出來(如何說),并且還要考慮你的讀者能否讀得懂,是否覺得與你對話快樂,有意義。如此看來,作文教學僅僅觸發學生寫作沖動還是不夠的,教師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即引導學生與自己寫成的文字進行“對話”(“內部言語”與“外部言語”的對話),讓學生在“對話”中努力實現用最理想的“語言”來做最成功的最準確的表達。作家孫犁曾說:“從事寫作的人,應當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語言,應當把語言大量貯積起來,應當經常把你的語言放在你的心里,用紙的砧,心的錘來錘煉它們。”作家福樓拜也說:“無論你所要講的是什么,真正能夠表達它的句子,真正適應它的動詞和形容詞也只有一個,就是那準確的一句、最準確的一個動詞和形容詞。”其實,古人在這方面已留下太多佳話,賈島“推敲”之故事,王安石吟“春風又綠江南岸”,等等,這里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當前作文教學的確要注重學生寫作思維、寫作情感的培育,因為學生在作文中普遍存在著情感缺失、思路狹隘等問題。但是,作文教學又不單單是思維啟發、情感培育的問題,這就如同不能單純訓練語言表達一樣。我們說,寫作過程中“思維情感”與“語言表達”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一塊硬幣的兩面,存乎一體,不可分割。作文教學的思維引導、情感激發絕不可脫離語言表達,而應寄托于“語言”這一美麗載體,有血有肉有靈有性地進行。同理,語言是思維與情感的語言,語言表達也要符合學生思維情感發展的需要,任何脫離或超越思維情感的語言都只能是虛情假意、矯揉造作了。
(作者單位:浙江省溫州二中黃龍校區)
(責任編輯:洪明)